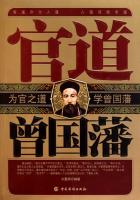2006年12月27日,上午进行队列训练,下午进行擒敌训练。好不容易挨过了3000米的轻装跑,晚饭刚吃饱,又要开始体能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我们一组一组的做,汗水一把一把的流。声音越喊越低,地面越来越湿。当洗漱哨声响起的时候,我们全部瘫软在地上。向没有骨头的软体动物,拼尽最后一点力气往外爬。如果说白天的训练对我们来说,算是苦的,那晚上的体能训练,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就是折磨的。就这样在班长的目送下,我们走出了屋子。满身是汗水的我们,被走廊里灌进寒风一吹,额头上干的就只剩下盐巴了。等去过了厕所,在回来拿洗漱用具,去往洗漱间,就寝的哨声就该响了。有些人总是牙刷了一半,有些人总是脚洗了一半,有些人脸上香皂泡沫还没有洗掉,就匆匆往回跑。有些人甚至还没有走出班级,就已经熄了灯。做完体能训练,我躺在床上蒙头昏睡,呼吸着满屋子的汗臭味,脚臭味,眼皮子一沉,老子睡的天昏地暗。
新训大楼后是一大片开阔地,隔着跑道建造了一个地窖。里面多数装的是土豆,白菜,大白菜,小土豆,还有糠萝卜。一年四季里面黑不隆咚,潮湿滴水。地窖的旁边是一处沙场,用厚厚沙子铺垫成一块摔擒场地。雪平整的覆盖在沙场上,风过鸟无痕没有一处脚印。大雪覆盖在部队大院里,风却在夜里悲嚎,夜晚显得那么孤独。
窗外的白雪趁着月光,照亮了去时的路。吴宇熄灯后就陷入了假睡,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直到午夜寂静了下来,走廊里除了风声什么也听不到。借着走廊里渗进来的灯光,他抬起手,看了一眼手表针指向一点。他故意翻了一个身子,铁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静默了一会,确定下面没有动静。他才掀开被子爬下梯子,轻手轻脚的跳到了地上。穿上鞋子提起衣服,小心的拉开门蹿出了班级。
风顺着窗户,拼命的往厕所里灌,吹的吴宇浑身瑟瑟发抖。他心里七上八下,越是害怕,手抖的越是厉害。好不容易把衣服穿戴整齐,一屁股就坐到了小便池的边沿上。厕所里窗户是他打开的,地面也是他用抹布一块块擦出来的。蹲便池子他用刷子一遍遍刷过,在用手扭干了抹布,擦掉一处处水痕。瓷砖与灯光交相辉映,他满脸是泪的脸庞折射在地砖上。看着眼前的自己,他几乎要哭出声来。他双手用力捂住了嘴,脸涨的通红,眼泪如豆粒般大小,疯狂的从眼睛里涌出来,掉到了地上,模糊了他的脸。
直到哭的全身没有了力气,吴宇用双手擦去眼角的泪水。哭红的眼睛,如死灰一般暗淡。他站起身来,走到卫生间的门口,放轻了脚步,连大气都不敢踹一声。感应灯霎时间,也安静了下来。走廊里面漆黑一片,他顺着右侧的楼梯,走到了二楼。二楼的楼梯口就是队长闫兵的办公室,他未打算做停留,瞄了一眼,头也没敢回的往下走,等到了一楼的楼梯口处,他站定了身子。他身体贴着墙,弹出脑袋看着远处走廊的中间位置。一位新兵正坐在那里,只见他瞪大了眼睛,观察着周身的动静,没敢有丝毫的松懈。吴宇在最后一节台阶上坐下,心跳到了嗓子眼。
guang-dang一声干脆的闷响,回荡在走廊的另一头。新兵站起身来提起手电筒,嘴里嘀咕着,“大半夜的,马德什么情况?”步子越来越远,渐渐的消失在走廊的尽头。吴宇深吸了一口气,快速闪出身来,摸着墙边走到值夜新兵,刚刚坐着的位置,而后顺着正门,跑出了门外。
风透着彻骨的凉,渗进了毛孔。顺着袖口,裤腿往身体里面钻。它们也想试图用寒冷,去拥抱温暖。
吴宇顺着楼檐下,转了半圈到了楼后。眼前一片白茫茫,远处天与地连成了一线。他望向远处明明一片黑洞,却又仿佛看见了自由。
自由在远处挥着手,张开了怀抱。留着眼泪,等待着他的拥抱。于是他热泪盈眶,发疯般的向前跑去。脚步深一脚,浅一脚的在雪地上留下一排脚印。他跌倒了爬起,爬起来在摔倒,他是多么想拥抱那份自由,那份能给他带来温暖的怀抱。他心中的太多委屈,无人倾述,无人在意。他越跑越快,越跑越远,毫不犹豫的跳过了最后一道防线。越过了用铁丝网编织的护栏,就已经出了营区。他停下脚步,回头望了一眼。远处的新训楼,安静的睡着。肉眼所见的地方,到处一片漆黑。摸的到的地方,尽是寒冷。他心中那股子劲头,慢慢松懈了下来。他大口的呼吸着,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冷风不停的吹着,他回过头看着满目荒凉,映入眼帘的尽是白雪。远处的村庄,早已经陷入沉睡。就这样他深吸了一口冷气,给自己壮了壮胆子。顶着寒风,踏着皑皑白雪,一个人行走在冬夜的冷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