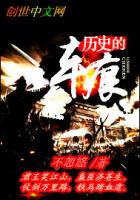江州大牢,一场生死较量正在上演。仅仅三米宽的监牢里,横七竖八地躺了几十具热气腾腾,新鲜出炉的死尸。从他们统一的着装,凄惨的死状上来看,是被一位体壮如牛,气势如云的壮士所杀。
汗在滴,血在流,刀光剑影之间,张必先的意识渐渐模糊,游魂散的毒性随着血液迅速布满全身,最后占据人的意识,让中毒之人如坠梦幻的深渊。
噗,噗,噗,沐英一刀又一刀地调戏着乌云大汉,刀刀见血,刀刀不伤要害,慢慢地释放着自己心中与生俱来的戏谑之火。
不知不觉间,两人已经战了五十几个回合,内心恐惧的士兵全都知趣地躲在一边。可悲的是,他们不是让乌云大汉吓破了胆,而是被锦衣卫这位少年千户统领的笑声吓得不敢向前一步。
“哈哈,哈哈,张必先,你也有今天。为了追杀你们兄弟俩,我沐英挨了多少骂,受了多少委屈,你,你知道吗?呜呜呜。”
士兵们都要疯了,这战斗正在激烈上演的时刻,沐大人居然还能抽出空来哭上一鼻子,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此时张必先的心里已经麻不不仁,他根本没有听见对面那个疯子的谶语。本能地挥舞着手中的钢刀,机械般地格挡着敌人的招式。
“二哥!你怎么了?快振作起来,孟娘等着你!”
一声柔弱的提醒突然在脑中响起,张必先一瞬间恢复了些许清醒。既然是计,就说明孟娘和少主可能没事,他们还平安。
“哈哈,哈哈,哈哈!”
一想到此,张必先突然释怀了,天不亡我大汉,只要少主平安无事,自己死又何妨,脑袋没了碗大的疤,十八年后又是一条浑然正气的好汉。
张必先怒目圆睁,钢牙咬破舌尖,意识瞬间恢复了清醒。他狂笑不止,抡起胳膊做最后的搏命,能杀一个赚一个。
钢刀手中握,雷霆万钧开。跳梁闻破胆,唯有英雄汉。张必先手中的钢刀突然变成一阵索命的狂风,所到之处肢体纷飞,鲜血横流,惨叫漫山遍野,恐惧达到了顶点。
沐英正玩得春风得意,突然感觉张必先的眼神恢复了一丝清明。他是个比鹰还精的主,接着罡风一闪,就退到了漩涡外面。一旁的士兵可就遭了秧,瞬间被卷进了绝望的激流,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一首歌再好听,也有曲终人散的时刻。一幅画再美丽,也有尘封灰暗的那一天。当一出戏到了令人激情澎湃的最高潮,那山呼海啸般的掌声过后,等待它的就是最终落幕的萧瑟。当一个人走到了生命中最后的那一刻,拨开乌云却见不到明月晚晴天,唯有一颗赤诚的心在朗朗乾坤之间,永恒地跳动着。
张必先用尽最后的力气带走了一片尸山血海,那勇武的拳头,威猛的钢刀吓得士兵抱头鼠窜,搅得江州大牢天昏地暗,气得锦衣卫千户统领沐英暴跳如雷。因为,鸡飞狗跳之间,他那一身心爱的白色锦绣战袍,被不知哪个无名鼠辈弄上了一滴红点。
“啊呀呀!混蛋,这是我新换的战袍,混蛋,混蛋。”
沐英把心底的愤怒全都发泄在了强弩之末的张必先身上,他丢掉钢刀,亮出恶拳,一拳,二拳,三拳。十拳,百拳,千百拳。拳拳到肉,冷酷无情又毫不浪费地招呼在了张必先强壮的身体上。
这不是在打人,这像是在打一个没有知觉,感受不到疼痛的沙包,木桩和玄铁。呼吸间,张必先就从一个高大威猛的乌云汉子,变成了支离破碎的模糊血肉。
“孟娘,孟娘,孟娘。”
在意识消散的一瞬间,张必先只看见一个面色清秀的女子,在遥远的云端,微笑着注视着他,似乎在向他招手,又似乎是在向他道别。
“我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新衣服就这么被你毁了。老子刚换的新衣服。”
沐英上一件衣服因为杀人杀得兴起,被死人的鲜血染红了。他嫌弃地丢弃了沾满无辜鲜血的袍子,换上了一身白色的锦缎。可只是一滴血,就是那么小小的一滴血,在他的眼里就是罪不可恕,就是该千刀万剐。
“哎呀,天呐。沐大人,快别打了,再打人就死了,你不说过还有一出好戏要看吗?”
知府李肃不知何时悄悄地凑了过来,高声提醒着歇斯底里的千户大人。怕他一时糊涂犯了大错,圣上可是亲传谕旨,要捉活口。
“呸!倒霉催的!李大人,找一辆加固的囚车来,套上枷锁,本官要把这倒霉玩儿的游街示众。”
沐英打也打累了,骂也骂爽了,鄙夷地唾了一口黄痰,撸胳膊挽袖子地出去了。
“乖儿子,上天给我盯着,把他同伙揪出来,我要再打一百遍!”
孟娘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出了房间,下得楼去,僵硬地走在大街上,跟着热闹的人群一步一步的向江边走去。
“客官,起来了?昨夜休息得可好?”
伙计殷勤的巴结被孟娘焦急的心无视了。她迈着沉重的步子,漫无目的的走出迎风客栈,全然忘了房间里还有个嗷嗷待哺的少主,在忍受着碱毒的折磨。
“不,这不是真的。二哥,你那么勇武的一个人,怎么会落到这群鹰犬的手里,怎么会被关在那个冰冷的囚车里,我不相信,不相信这是真的。”
吵杂的人群中,孟娘只敢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呐喊,她不敢出声,不敢做任何动作,只有脸上那默默流淌的热泪在挂念着囚车里那个心爱的男人。
“怎么办?怎么办?二哥,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痒死了,好痛,这还有没有天理啊,怎么可以放着一个孩子不管啊,我还没吃饱那!”
房间里,陈永乐渐渐从瘙痒剧痛的折磨中恢复了出来。环顾四周,空空荡荡,美女不见了。
“毛主席从小教导我们说,凡是遇到困难,要自己动手,才能丰衣足食。我前世好歹也是个全运会亚军,怎么会被这小小的折磨击垮?再痒再疼我也忍着,可就是饿我忍不了啦!我要吃饭!”
苦苦挣扎后,一个三岁大的孩子在陈永乐坚定不移的努力下坐了起来。窗外刺眼的阳光照射进来,让小家伙不禁低了低头。
“嗯?这不是美女吗?这是要去哪?真是的,太不负责任了。丢下我一个人不管,难道是自己吃好吃的去了?”
也不知陈永乐哪里来的勇气,居然有如此荒唐的想法,自己苏醒之后,这是第一次真真切切感受着这个陌生世界的一切。
房间里的陈列朴素整洁,家具桌椅看上去古朴沉重,卧榻上的被褥像是电视上演得宫廷剧中才会有的样子。永乐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穿着也像个古代人一样。
“原来地狱就是这个样子啊,这根本就是中国的古代嘛!”
咕噜,永乐正感受着自己小小的身体。陌生,新鲜和好奇压制了她背上的奇痒和剧痛,却没能压制饥饿的侵袭。肚子没羞没臊地突然响了一声,吓了永乐一跳。
“哎呀,先不管了,填饱肚子是正经事。”
小家伙费劲地从床榻上下来,穿好了布鞋,在饥饿的驱使下一步一坎儿地走下楼去。
“耶?这娃娃是谁家的?这么小一个人有没有人管?”
“三儿,别在那大呼小叫的,这不是刚才那位客官的孩子嘛。小娃娃,几岁了?你娘亲出去了,你在这儿等她一会好不好?”
掌柜的人不高,可永乐的高度也才到他腰以下。陈永乐心中有千言万语就是说不出来,虚弱的身子让她摇摇晃晃。可外人看来这孩子可能腿有点残疾。
很快,客人络绎不绝,掌柜和伙计忙活开了,没人在意客栈门口一角还杵着个小不点。
“饿死我了,上哪去弄些吃的呢?刚才美女是往那个方向走了,我还是去找她吧。”
陈永乐在一片热闹声中迈出了门槛,向孟娘的方向寻了过去。此时,陵江边的坊市里,一片空旷的场地挤得人山人海。好奇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这种天性可以让人寻找未知,突破自我。可有时,这种天性也会让人显得冷血无情。
“这囚车里是逆贼?谁啊?”
“听说是陈汉军的一位将军呐!”
“净瞎说,你见过将军啥样吗?你看那蔫吧样,哪里像个将军。”
人们交头接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有孟娘的泪,在这群闲杂人等中间显得那么珍贵,重情。
“二哥,在忍耐一会儿,孟娘马上想办法救你出去。”
人群之中,孟娘怀握匕首,焦急地想着救人的办法。全不觉得周围这些闲言碎语有多可恶,可气,可恨。
“沐大人,这人越聚越多,人一多就容易旁生事端,我看我们还是尽早回吧。”
“哈哈,李大人。敢不敢再和我打一个赌啊?”
“得了吧!沐大人,你饶了我吧,我。”
沐英和李肃正站在江边看着,聊着,等待着,等待逆贼的同伙出现。突然,远处江水之上传来了打斗的金铁声音,好像这逆贼的同伙真的来了。
声音越来越近,卷着层层江水向岸边的坊市空场袭来。惊得看热闹的人群四散飞逃,惊得孟娘的心瞬间停止了。
因为她听见一声再熟悉不过的呐喊,“孟娘,保重!”
“不好!逆贼要咬舌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