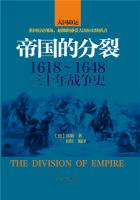何奇江听他说话不清不楚,正要发作,可顺着他的手势方向一看,不由大吃一惊:“这……这……”他自己也“这”了半天,没“这”出个所以然来。其时,场外走来了三个被五花大绑的人,他们正是张玉环三兄妹。大概是因为这件事实在透着稀奇,那些原本胆小怕事不敢来看热闹的父老乡亲,现在都跟在三人后面来到了现场。见到眼前这一幕,何奇江及其传令官当然不得不张口结舌了。
“玉环,你,你这是何苦呢?”何奇江迎着三人走去,想要为其松绑。
“等一下,”张玉环并没领他的情,领着梅花二人,直接向跪于坟前的乡亲们走去。何奇江只好尴尬地立于一边。
“乡亲们,我曾经对大家说过,如果你们出现了麻烦,我定会为大家说话。现在,我正是为大家说话来了。”张玉环三人面对乡亲而站,那些原来垂头丧气的人,这时全都直起了腰,以一种无所谓的不无讥讽的神态看着她,等待着这场闹剧的结局。
“何叔遇害,这全是我爹一手造成的,其他人只不过是受了他的蒙骗。”听了这话,众人脸上讥讽的神色去掉了不少。“常理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爹指使人干了这件伤天害理的事,他是该替何叔偿命的。可是,平日好好良良的他,却在去年提前走了,这也可说是遭了报应。如果有人对这种自然解决的方式不满意,非得用枪杀人才解恨,那就让他来杀我好了。我爹已走了,有道是‘父债子还’,我是他的女儿,理当替他来还这个债。在他临终之时,我就答应了他的,如果仇家来复仇,由我替他偿命。”众人听到这里,都不免佩服地点起头来。
“假如杀我一个还不满意,非得大家都去死的话,那就让我先乡亲们一步走。第一,我是罪魁祸首的女儿,又应承替他偿命,当然该归我先挨枪子。第二,我也曾应承了乡亲们,到时为乡亲们说话。现在话是说了,却没能解脱乡亲们的危难,害得乡亲们没有及早远走高飞,到如今来遭此大劫,这是我该死于乡亲们之前的第二个原因。第三……”说到这里,张玉环不由自主地抛下两行泪水来,复又接着说,“第三,当初我同梅花妹子救下了一个濒近死亡的人,而这人后来却成了个杀人恶魔,要乡亲们一百多口人来偿他爹一个人的命,看来,我们先前是救了一个不该救的人,这就是该让我先乡亲们一步走的第三个原因。并且,因为这个原因,就算让我死上十回八回也不能免去我这时心头的悔恨。乡亲们,就让我先走一步,看看我张玉环是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说到这里,她突地转过身来,面朝着站于一边让她尽情演说的何奇江道,“来吧,姓何的,有本事就先朝我开枪!”虽然她脸上满是泪痕,却仍不能抹灭她那决断和刚毅的神情。
何奇江站立原地,久久地、正儿八经地瞧着她,就像是瞧着一架刚从国外进口来的西洋镜。他实在想不透她,这几年怎会变得如此倔强,如此不顾一切。他记得,过去她可不是这样的,过去不论遇到什么事情,哪怕只是针尖大点的小事,她都总是大呼小叫地让他来替她处理,不管这些事自己做得是否正确,她也总是无所谓的。如今可不一样了,哪怕是面对屠戮,她也要坚持她那个理。
场中跪着的人,瞪眼看着这对冤家的对峙,长时间没人发出声音,空气又像是突然要爆炸似的。场外人虽要好过得多,但也不时有人擦着额头上突然冒出来的汗水。
终于,何奇江的嘴角突又现出了平时他那特殊的微笑——既表现出狡黠,又显示出猾稽。他拍了拍巴掌,旋即哈哈一笑说:“看我这老婆,真是会演戏。”说时,他就走上前,又想为她解开绳结。
“谁是你老婆?谁给你演戏?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张玉环还是不依不饶。
“好好好!算你狠,我叫一声姑奶奶行了吧?”他走上前,又面对着仍跪在地上的人们高扬起双手说,“乡亲们,误会,误会,这完全是场误会。”说着,他扭头对身边的副官狠声道,“还不快把那些机枪给我撤下去!”接着又转过头来,“啊,乡亲们啦,我叫他们把武器带来,只是想让大家开开眼界,并不是叫他们用它来对付乡亲们的。不知是哪个混蛋,误传了我的命令,回头一定追查此事。乡亲们啦,有人说我是杀人恶魔,我杀了谁了?我又说过要杀谁了?都没有,是不是?”说到这里,他双手叉腰,俯着身子对石老二说道,“石老二,你说说,我说过要杀你们兄弟俩了吗?”
“哼,你不是说要替你爹报仇吗?”对何奇江的故意做作,人们既是觉得可笑,却又不敢笑出声来,还是用那鄙夷的目光看着他,只有石老二再顶了他一句。
“报仇?是呀,是呀,杀父之仇,岂能不报?可我说过要用杀人的方式来报仇了吗?”
“你若是无心杀我们,干吗把我们捆来跪在这里?”开始有人厌恶的嘟嚷着说。
“啊,是的,你们都还被捆着。来人啦——啊,慢着,乡亲们啦,先听我说几句……”何奇江又叫住了正准备去为人们松绑的士兵。士兵们被他的行为弄得啼笑皆非;而仍被捆着的人又不知他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没办法,也只好耐着性子看他继续表演下去。
“说我想以杀人的方式来为父报仇,那是没有根据的。当初,杀害我爹的凶手除石维义而外,还有我内兄一个,如若我要杀人,岂会放过内兄,可我并没把他押来,是他自己主动来的,大家讲是不是?我何某可不是那些心胸狭窄之人,可是现在要为大家松绑,也总该先从我内兄开始,我想大家是不会有意见的,对吧?!”说到这儿,何奇江便走到张治业身边,为他解起绳索来。
张治业从打与妹子一道自缚来坟地救人的那一刻起,就心如止水,什么事也不愿去考虑。反正这条命如今是掌握在别人手中,只把自家当成个死人,任他们怎么办都行,听天由命算了。现在见到何奇江这种态度,并没如妹子说的那样可怕,自己脑中反倒是一头雾水,不知他夫妻二人究竟玩的是什么把戏。而今见何奇江先要来为自己松绑,也就不言不语,任其而为,只是希望这场闹剧早些结束。
直到何奇江把张治业的绳子解开抛在了一边,张玉环心理的疑团仍是没解开:“难道自己的判断错了,这家伙思想已经开通,并不准备再杀人?不不不,如果不准备再杀人,那他押这些人来干什么!可是……”她的脸色虽是稍霁,但也就不再做声,静观事态的变化。
“来人,现在去给乡亲们松绑!”当士兵们脸含笑意去给众人松绑时,何奇江回头看了张玉环一眼,并对之嬉笑了一下,见她把头转向一边,让兄长为之松绑,就又面对或站或坐的众人说,“乡亲们这下放心了吧,我们卫乡团的刀枪,怎么会向着乡亲们开呢?如果是那样,那还叫什么‘卫乡团’?不过杀父之仇,不能不报!”说到这里,他扫了一眼众人那又为之变色的脸,再看了看那虽被松了绑却仍然跪在地上的石维义,转身走到供桌边拿起原来石维义交出的枪支和银元,然后扬起它们说,“害死我爹的杂合子,就是这两样东西,不是它们,我爹不会死。今天,我就拿它们开刀。来人,把门板竖起来。”
两个马弁听到吩咐,在距何奇江三十步开外的地方,竖起了一块门板。副官从何奇江手中接过两块银元,把它们并排嵌在了门板上。何奇江把三发子弹全部装进这支驳壳枪,然后翻转枪身左右瞧了瞧,突然举枪指向两枚银元,只听‘叭叭’两响,两枚银元虽然仍纹丝不动地嵌在门板上,可各自中心全都留下了一个空洞。
“好枪法!”人们禁不住齐声喝起彩来。
“果然是支好枪!”何奇江吹了吹枪口上的热气,“石维义,你怎么还在那儿跪着?如今那两块大洋,已为我爹身上中的两枪付了债,从此以后,我们之间的怨仇一笔勾销。这支枪,本是我岳父送给你的,现在仍然还给你。里面还有一发子弹,请你以后在开枪之前,先想想清楚,这枪到底开得开不得。”说着,他把枪递给副官,示意把它交给石维义。
石维义微颤着双手接过枪,然后才慢慢站立起来,他双目凝视着仍是那么油光铮亮的它,泪水泉涌,点点滴滴掉在了枪身上。
“乡亲们!”何奇江又开了口,“这些天,我的手下弟兄,不明究里,对大家多有得罪。现在,何奇江令人煮了这几锅大菜,以示道歉!”说到这里,他又环视了一下场外越来越多的看客,向他们抱了抱拳道,“还欢迎前来参加我们这‘冤家会’的场外父老兄弟,大家都来喝上一杯‘释仇酒’,望我们大家今后团结一致,再也不在家乡做出什么让人痛心疾首的事来。好了,如今我父仇已报,在没喝这‘释仇酒’之前,我还得把‘恩’也报了,真正做到恩怨一笔勾销,然后才好与大家一道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