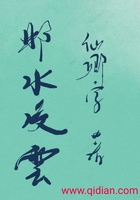1947年8月,中华大地的国内战争,又进行到了如火如荼的历史阶段,而这远离战场的茶洞边城,却正是玉米秆儿翻黄的季节.。这天傍晚,为了传达上峰派丁派款的紧急命令,以及进行必要的工作安排,汪子俊又一次在擦黑天从新街过河来。这次擦黑天过河,他已有了往常的经验,除了左右有王七贵和刘二两人相伴外,身后又加了两个镇丁跟着。.
五人刚在新街码头上方一现面,河这边的越素贞就出了码头坎上摆设摊点的小屋,径直来到坎下河边,上了杨全癫子的小游船。一俟越素贞在船舱内坐好,杨全便唱着山歌,慢慢悠悠地将小船划向上游的老马路。这老马路处于大桥和渡口之间的地段。当初公路桥还没建成时,汽车是从此路经渡口用船装载过河;大桥建成后,此段公路就自然废弃了,所以称之为老马路。
汪子俊一行过了河。表面看来,大家都轻轻松松,有说有笑,但一进西门面向余家院坝之时,大家的神情就马上紧张起来了。
“上去看看!”未成进入余家院坝,汪子俊就在余家右侧厢房屋侧,吩咐刘二带上两个镇公丁,先行进入城楼巡察一遍。
刘二带着两个镇丁登上城楼,四下张望了一时,并没发现周围有什么异常情况。其时,原来城楼前左侧的莫家小店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覃家新建的四层木楼。清政府既是已成为历史,那在城墙边新修房屋就没有了过去的旧规矩。覃家旅店新修的这木楼正是如此,他不但没留阳沟而紧靠城墙重建,并且那屋脊还高过城墙四五米,甚至还把房屋靠城墙这一侧的壁头,将就着砌在了城墙上,使得这段原来比较敞亮的路道,如今变成了一个小巷子。又因为覃家这壁墙的尾部延伸过长,影响了余家院坝的志向,杨有元就与覃老板吵了一场,既而闹到了天王庙衙门。然而,余、汪有嫌,覃氏有钱,一场官司下来,谁胜谁负也就不言自明了。如今这儿既是变成了一个小巷道,且一眼就能把前后看穿,那要想在这儿藏什么人,也就变得不可能了。若是真的有人想朝巷中开枪,那他就必须是到城楼上。
“楼上没人!”刘二与两个镇丁下了城楼向汪子俊报告。
没听说有异常情况,汪子俊点了点头。五人就又照先前的队形,王七贵居左,汪子俊居中,刘二居右,三人走前面;两个镇丁并排跟在他们的后面,五人一起经过余家院坝走向了登山的路道。当然,走在前面的三个人并不担心身后有什么响动,而走在后面的两个镇丁就不同了,他们二人时不时地返身向后张望,生怕一不小心,自己就变成了短命鬼。
五人上到了绿阴阁,就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汪子俊回身望了望山下民宅,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道:“从前那一枪,莫非是那婆娘在她家里放的?”
“那怎么可能!”王七贵像是知道他说的“那婆娘”指的是谁,就提出了质疑,“那时,她那房子的屋脊,还高不过城墙两尺,在她家里开枪,角度根本就够不上!”
“如果她躲在她家的天花板上,先揭开几张瓦,然后把枪口对准我们,那又怎么样呢?”汪子俊又反问对方。
“啊,那倒极有可能!”王七贵也真是如梦初醒,“可那时,镇长怎会没想到这一点呢?”
“我也是刚刚才想通的。”汪子俊轻笑了笑,“你们看,现在覃家饭店的三楼,楼层下面刚刚同城墙持平,如果有人要从那吊楼上向我们开枪,那我们五人不论哪一个,都会暴露在他的枪口之下。而当时莫家那房子的天花板的位置,同这三楼的位置是一致的。那时我们之所以没想到这一点,就是被瓦面的因素蒙住了,以为如要从那儿开枪,非得站在瓦面上才行,没去想瓦是可以揭开的。”
“嗯,那是那是!”王七贵也若有所思地接了话,“几时我们去她家搜一搜,看看她把枪藏在哪儿!”
“暂时不要去惊动她,”汪子俊转过身,又边走边说起来,“她刚与蒋跛子成亲,一时半会还不可能有什么动作,我们不如暂且让他们快活几天。不然,事情隔了这么久,现在单凭一点猜测去找他们麻烦,又会惹得街上人议论。”
“镇长真是说得对,”刘二讨好似的跟上一步,又补在了汪子俊的右手位置,“只是越素贞那婆娘,一朵鲜花插在了蒋跛子这堆牛粪上,也实在是可惜!”
“什么脔鲜花,只不过是烂货一个!”汪子俊驻足说道,“没听人说吗?那狗日姓黄的团长,临走之前同她裹了好几夜!”
“事情确是这样的。只是我实在不明白,当初龙文池那骚公子,一门心思放在她身上,可她却死活不顺从,现在倒要嫁给这蒋跛子,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你老弟懂个屁,”走在汪子俊左面的王七贵也禁不住开了腔,“她一直以为是龙文池那小子害的蒋奉楠,怎么还会委身给他?”
“嘿!七贵看事情就是实在,”听了王七贵的话后,汪子俊也不由地赞赏起来,“正因为这样,她才心甘情愿地让那狗日的黄团长上她的身,之后就靠这姓黄的取了龙文池的……”说到这里,汪子俊突然觉察到此话不妥,也就急忙转换了话题,“不过,这话你们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说,不然事情就闹大了。”
“这事镇长大可放心,”刘二见汪子俊如此谨小慎微,就又讨好地接上了话,“我兄弟几个,也没有哪个是不懂事的。那次让他蒋奉楠吞了鸦片,事到今日,也没见一个兄弟露了口风去。”
“嘿嘿,你老弟今日不是露了口风吗?”听了刘二如是说,王七贵禁不住冷笑着又刺了他一句。
“这,这是我们自家兄弟在说话。”刘二不由地胀红了脸。
“记住,以后不许谁再提起这话,不管是不是自家兄弟,”汪子俊也觉着刘二说话有些荒唐,于是出言给于警告,“谁要是再提起这事,出了事由他一个人捡梗。”
“好,以后谁都不许再提起!”刘二也觉着话不投机,下了保证后,就不再出声了。
五人上了大山门前那石板铺砌的坝子后,全都轻松自在地准备走进大山门。突然,天王庙与城墙之间的巷道里,陡地闪出了一个黑衣蒙面人,还不等五人惊啊出声,蒙面人右手上的短枪便指向了前面的人,随着砰砰两声枪响,汪子俊和刘二就同时倒了地。其他三人见势不妙,也迅速卧倒,出枪,对着巷道一阵猛射。
当三人抢到巷道口时,只见巷道的另一头,那黑影已闪身上了城墙,再一闪身便消失了踪影。王七贵带着两个镇丁,追到了黑影闪身不见的城墙地段,只见城墙脚下,土中的玉米杆在晚风中株株颤动,叶叶作响。他们实在不敢就这么跳下城墙再行追凶,向玉米地胡乱放了一阵枪后,又不得不垂头丧气地撤回了庙内。
这天晚上,越素贞偎在蒋老成怀中兴奋无比。她不断地重复着这么一句话:“我已报了仇了,以后可以自自在在地过日子了。”
第二天,他们起床特别早,目的是想听听路人是怎么对昨晚的事件进行评说的。可直到早饭时分,他们才从知情人口中听到确实情况:汪子俊真命大,刺客明明是要杀他,他却让刘二给他挡了枪子,自己安然无事,可怜刘二就命丧当场了。
“难道真有老天保佑他?”坐在饭桌旁的越素贞,半天不曾动筷子,就这么端着碗,长时间地愣着。
“不要性急,这次不成,还有下次。”蒋老成又不得不出言对妻子进行安慰。
可是,从此以后,不管是黑夜还是白天,汪子俊出入天王庙就再也不从大山门走了,全都改由小山门出入。大山门就此长期关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