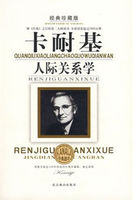我注意到猴哥进来时候拎着个大皮包,瞄了一眼之后就开始盯着猴哥布满褶子的有趣的脸,努力的把它幻想成为一朵花,最后竟然有点恶心了,也不明白这是一种怎样的恶趣味。
我轻咳了一下,然后看着他一沓一沓的从他的黑皮包里往出掏钱,不久在远处服务员的目光,由不屑变成了吃惊再变成恭敬之后,我面前的桌上整整摆了五十沓钱。猴哥的黑皮包转瞬就瘪了下去,被他拍了拍丢在一边。
金钱总是给人很强烈的说不出是什么样的感觉,尤其是整整齐齐的这么多。“你平时上街也都带这么多钱?”我弹弹裤子上散落的烟灰随口问他。
猴哥此刻坐在我对面像极了一个财神爷,他抬手拿起面前的高脚杯,那是鱼先生刚刚走的时候留下的,杯里的冰块早已化成了水,混合着红酒残存的味道。猴哥咂咂嘴说:“果然是酒吧的水,多少还是有些酒味的。”我没说话看着他品味的神情,听他继续说了下去
“反正都是你的钱,我就算整了一运钞车丢了也是你的,我又不心疼。他斜眼看看我,见我没什么反应,他识趣的换了个坐姿又张口压低声音说:“人家委托人拿给我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收到消息时委托人叫我去城郊的一所旧房子里去取的,目标信息和要求都在那里,我想附近也一定是有人看着的,因为离你这太远所以来的迟了些。”
我吸了口烟然后问他:“那我要是不接的话岂不是很麻烦。”
“你麻不麻烦我不知道反正我会很麻烦,一来钱很重,二来送完之后我可能也会回不来。”说完他从怀里拿出一张纸递给我。
我伸手接过来摁灭烟头,边看边说:“你又把麻烦分给了我一份,也为委托人添了不少麻烦。。。。不过,”我眉头皱了一下,“我接了。”
“目标确实棘手,可是尾款还有三个这么多,那就辛苦辛苦。”
我没说话,有的时候我在想送信人原来也一定是个杀手,就连我之前死掉的那个生活也及其自律,从不冒险,所以从他们手里接过的委托通常不至于太离谱。
因为只有杀手本身才能准确的意识到是否真的可以。我想他在接单回来的路上有没有设想一下如果是他该怎么做呢。那是他的故事,我其实挺好奇的,不过懒得去问他而已。
“选人杀”从来就不是我的风格,所以这么久合作以来他送来的单我通常是来者不拒,我在想是不是他对我开始有了些盲目的自信。当这单摆在我的面前的时候,这次确实有些离谱了。
目标是一个黑帮老大,很纯的那种。很黑,而且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帮。同行里有些人的枪都是从他那里购买,也有很多人接了他的单再也没有收到尾款。散播的谣言里多少还是有几分是真的。
尽管委托人给的信息真的是很充分,足足十几张a4纸,在有些时间上甚至精确到了秒。然而除了能表达出委托人真的很想让目标立马死掉之外,对于我来说毫无意义。就像考试时候自己做的小抄,大家都是极尽详细,用来应付考试的时候种种变化。
没错就是变化,对于目标这种人来说,固定到可以让人觉察的东西一定是万无一失的,那么剩下来的就是无尽的变数,每个变数都会使杀他这件事情的难度成几何次方增长。任何失误就会意味着死亡,我敢拿脑袋担保他一定不会让你有第二次出手的机会,关键词是你,而不是第二次。
猴哥看我不说话就开始收拾桌子上的钱,又装上了满满一兜。然后安安分分的拿着我的钱去买了单。然后他把皮包递给了我,起身就走。在快出门的时候他突然回头说:“下次一定我请你。”
我没来由地笑了笑,冲他扬了扬手。远处的服务员还在好奇的打量,最后终于缩回了脖子。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旦你发现你所好奇的是你所无法承受的,拜托就请识趣些,还是过好自己的日子很靠谱。
我拎着皮包出了酒吧,喜欢的夜色,又降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