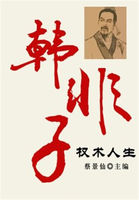第二天我起床,穿着拖鞋下楼买早餐的时候,报摊上头版头条大大得写着,大学教授与爱徒分遭割喉爆头。附着三张照片有两个死者打着马赛克的脑袋,还有天台上一支漂亮的高脚杯。
这是鱼先生的风格,一枪爆头,然后在狙击点留一支酒杯。真是够麻烦。如果有一天出门做事忘记带杯子了那岂不是很尴尬,难道还要回去取?鱼先生说他从不忘记。倒是我有些多虑了。我也曾问过他为什么叫鱼先生,而不是叫什么猫先生,鸟先生的。他就用他惯用的理所当然的表情对着我说:鱼只有七秒的记忆。
“那你为什么不在酒杯里放一条鱼,那岂不是更有风格。”我有些不甘心的问道。
“那太麻烦,而且,太傻了”他满脸讽刺的味道。
我发誓再也不会和他讨论任何关于他的问题,似乎只要我问的都会显的我很蠢,那样可真是太无趣了。不懂幽默的人类,除了喝酒他的生活还有什么乐趣。
我与他的相识是他的第一单,目标也就是他那个倒霉师傅,更倒霉的是我就这样和这个鱼先生撞单了。这样的几率事实上并不大,只是看起来得手的把握会更大些。有钱的人似乎总是很小心,而我就是他的第二重保险。
这世上的事大多都像是一场戏,人们都把自己当成是导演,事实上谁又不是被命运肆意安排的演员呢。
鱼先生的师傅是一个老手,像我们这行似乎都有好运被用完的预感,于是在我准备下手的头几天,他就整天猫在家里拉紧窗帘,晚上甚至连灯都不开。
作为一个总在狙击镜里杀人的杀手,他比谁都害怕出现在别人的狙击镜下。我在他的房子附近转悠了好几天,他确实比我们会享受生活也富裕的多,三层的小洋房露天的大泳池,还带了个小花园。
我不是很喜欢这种潜入杀人的方式,很麻烦,很有难度,尤其是再面对这样的同行,被反杀就悲催了。我注意到每天都有一个年轻人会在这栋房子里待上三个小时,我猜这个时候该是最难干掉目标的时候,因为要面对的是两个人,但同时也是目标最放松警惕的时候。
我抽了抽鼻子,这需要个差不多的计划,还要选一个最稳妥的方式。年轻人一般是上午九点准时出现在这家门口,用钥匙打开大门,再仔细锁好,再去敲响房门,大概在十一点左右会从房里出来然后离开,为了稳妥些,我把时间选在了那个年轻人出来的时候,而我就等在门口,为自己借了一辆邮局的送信车,电动的,很轻巧,作为道具在我看来也算正式了。
十一点过五分在年轻人推开房门的同时我敲响了那个大铁门,高声问道“请问这里是,xx路,xx号么,这里有封你的包裹。”
那年轻人走出来,目标并没有跟出来,只是半开着屋门连头都没露,真是够小心的。年青人朝我走过来,我突然觉得那个年轻人表情有些怪异,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这次可能要无功而返。
正想着年轻人来到大门口,我正视他,他只是看了我一眼,小声说道,“你是谁,不可能有信件会送到这里,”我心里一紧,难道被识破了么,我正要张嘴解释,只见那个年轻人又笑着接过信件,突然咦了一声,然后回头冲房子的方向喊到,“师傅”。
我心里一紧,我去还是师徒,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还不想放我走么。屋里传来回应“怎么了?”“这信很奇怪,上面画着一只眼睛。”
我突然很疑惑的看着这个年轻人,信封上其实并没有什么眼睛,后来我猜一定是他师傅有了一个了不得愿望,愿望这种东西就很容易变成毒药。
“什么?”屋里的人似乎很惊奇,然后门呼啦一下就打开了,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快步的朝大门走过来,似乎很急切的一把抢过信封,反正面一看自然是什么都没有的。
他疑惑的抬头,迎接他的却是我从门上铁栅栏里探进的匕首,他的瞳孔立刻收缩,紧着抽身想要后退,突然他身边的年轻人用左手捂住他的嘴,右手用力向前一推,噗,目标的喉咙直直的迎上了匕首。
目标眼睛睁得大大的,原来一个人在生命的最后一瞬目光中回流露出那么多情绪,疑惑,惊恐,不甘,绝望,血溅了我一脸,我有些意外,一时还没回过神,那年轻人松开手,甩了甩手上的鲜血,冲我微微一笑说道:“没想到这么轻松,呵,这算你的还是算我的?”
我也收回了匕首,抹了把脸“妈的,真晦气,如果是同行的话处理了尸体这单算你的。”
“可以,在对面胡同里的酒吧等我,半个小时后见。我送他一程”他没抬头看着地上翻了白眼的目标。
我努努嘴,“这车也送你吧,这下亏本了”,我转身点了支烟,一股子腥味,我快步走向路边的公厕,还好这地方人不多,我打开水龙头洗干净脸上手上的血迹,这是什么情况,我深吸口气,终究好奇心还是战胜了我,我决定去那个酒吧等他。
如约,在侍者第三次提醒我这里不允许吸烟时他出现了,他竟然还抽空换了件衣服。“不好意思,迟到了点”他俯身坐下微笑着对我说道。
“反正我对时间也没概念。”我用手指敲着桌子。“彩头给你,不过我想听故事。”
“还真是个好奇的人。准则第二条。”他微笑的说道。并且从侍者那要了瓶红酒。
“这顿得你请,我可没过过有钱人的日子,我只对你的故事感兴趣,别拿准则说事。”我没看他摆弄着打火机说道。
“他是我的师傅,也是我的第一单。事实上接单的时候我还不是个杀手,可能雇主等的太久才又找的你吧。幸好雇主厚道,没想我是在骗他的钱,让你连我一起干掉。这单我收获颇丰,这顿我请了。”他带着笑似乎真是开心的得很。三言两语,他停下来不打算说下去的样子。玩味的透过酒杯看着我。
“就这样?”我挠挠头。
“要不然?”他还是在笑。
“你是真的很开心,还是有点什么病?”我是真有些无奈。
“别的不说就说老头留下一把L115A3狙击步枪,Y国制,最远射程2475米,可是有钱都买不到的好家伙。你说我开不开心。”他说着嘴角不自觉的翘起。
“你也不嫌晦气,不怕我后悔。”我往沙发的靠背靠了靠,翘起了二郎腿。
“可是我请你喝酒了。”他放下酒杯双眼盯着我。
“哈哈。”我也说不上怎么突然就觉得很开心。他见我笑了,也和我一起大笑起来。我的规则从来就只是看心情,就像我喜欢自由,不受约束。
过分欢快的节奏,总是让人容易忽视最重要的音符,比如他的故事,比如信封上并没有的眼睛为何就会那么容易就让一个谨慎的老手连最基本的警觉都丧失掉,很明显的杀手行当里迷一般的盒子,怎么会就这样由一个普通的邮寄员送达嘛。
一直到夜里我没收到包裹,也没收到尾款,所以我开始躺在床上,假想怎样的愿望会让人不顾一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