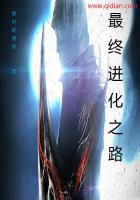听见喊声,我脚步一顿,随即转过头抹了一把熏黑的脸对来人说到:“还用我进去么,我这真是强出来。”
来的是目标的一个手下。他马上说:“不不不,这已经非常感谢了,我过来主要是想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我们老板。另外,你这真的没事么。”
我摇摇头一脸认真的说:“就这一个老太太,别人没看到,这么大火怕是不好说了。我这没什么,你们赶紧救火吧我回去洗洗。”那个手下应了一声就向火场跑去,我也转身晃晃悠悠的离开。
当我开着这台破车回到家里,已是凌晨两点半的光景。我一身焦糊味的倚在车边抽着烟,裸露在衣服外的皮肤开始有些隐隐作痛,我摸着被烧没的眉毛,不禁苦笑。
这里的夜晚很静,年久失修的路灯颤抖着昏黄的灯光被喜欢光的飞虫们簇拥着。在许久以前人们都在说飞蛾扑火,那是一种奔赴死亡的决绝,或许我也只是想要那种一瞬间的灿烂,子弹命中,或是生命凋零,电光火石间立见分晓。
我将烟头踩灭在黑暗,夜还长,别浪费了。我摇晃着上了楼,我脱掉上衣打开了淋浴喷头,温水落在身上我疼的一皱眉,周身传来的灼热,以及浴室起的热气又让我有了一种窒息感,我靠墙坐下,突然有些疲惫就这样睡了过去。我又梦到了那个大雨倾盆的夜晚,一切都很模糊,然后一片血光。
当我被冷水打醒,起身关了水,我晃了晃发沉的脑袋,擦干了身体。我望了一眼镜子,脸上有几处熏黑怕是洗不下去了,眉毛也牺牲了,头发都卷曲着贴在头皮上,我苦笑,黑人你好。
出了浴室,我从焦糊的上衣里拿出手机,尾款入账,猴哥的恭喜短信,慕斯的催款短信,还有台风警报。台风,来了。
我换了套衣服,把钱给慕斯打了过去,然后给猴哥打了个电话约了在那个酒吧见面。简单收拾一下后我拉开门,果然包裹就躺在了门边,黑色的一只眼望着我,我把包裹扔回屋里,转身出门。
天气阴沉的厉害,一路顶着街上打量的目光,我来到了那个酒吧。猴哥已经在那里等我了,看到我时他几乎差点笑了出来,又马上收了回去,表情十分怪异,我没理他转身要了杯酒。然后开口说:“很开心,我有机会喝到你请的酒,”
“我也很开心再次见到这样的你。”靠,又是那副很想笑的表情。
“最近听说流行切除笑神经的手术,蔷薇有提过,不过还没找到人练手,要不你去试试。”我喝了口酒,靠在椅背上对他说。
猴哥尴尬的咳嗽了两声:“咳咳,我们换个话题吧,今天早上的报纸你应该还没看到吧。老大死了,老二上了台,顺理成章的接过产业。”说着把今早的报纸放在了桌上。标题很醒目:“黑老大遭火灾惨死家中引暗流涌动,二当家出面调和各方势力还社会安定”
“委托人是二把手?”
“应该是,获利最大的就是他了吧。”
我摇了摇头未置可否然后讲了一下昨晚的经过。
“这有什么不对么?”猴哥听我讲完问。
“我是觉得太容易了,而且像他这样的人不该喝酒喝成那样。事实上我并不觉得这是我的运气。”
“关于他的故事多少我还知道一些,要听听?”
“反正下雨了就说说吧。”我望了望窗外,点了支烟。
“你觉得什么样的人会成为黑帮老大?”猴哥突然问我
心狠手辣,工于心计,讲义气……我头脑中闪过很多词语但这都是可以后天可以养成的,然后开口说:“应该是见识过绝望的人吧。”
“还是你见识深,你知道早些年在城乡结合部那原先有一个社团么。”
“听说过,报纸上说过不是被警方围剿了么。”
“是的,目标龙哥小时候家就在那里,因为那个社团的出现,整日游荡在那里的二流子似乎都找到了归宿。崇尚暴力,信奉不劳而获的他们很快成为了那里的大祸害,这样的趋势像病毒,很快吞并了这个区域,进而成为好不了的绝症。
善良的人被感染侵害,恶毒的人越发嚣张,你可能不会理解那个时候的水深火热,和那种暴戾的疯狂。而那时候他还小也不过十四五岁的模样,父亲姓穆,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人。因为勤劳家里的日子要比附近的邻居好一点。
他是个很聪明的孩子,父母很疼爱他给他取名穆龙,也是望子成龙吧,虽然家里并不富裕,但还是坚持送他去读书。
似乎故事最悲情的转折都会用上好景不长这个词吧,没错的就是好景不长。他家的邻居说是是个小偷,平日里偷鸡摸狗惯了,之前人们淳朴也都不怎么计较,再说大家日子都穷也没什么可偷的。
然而社团的存在,让很多人开始自以为可以主宰一切。小偷在行窃的时候,被一个社团的小头目发现了,被打了个半死爬回了家里。龙哥的爸爸老穆得知后就去隔壁看望他家的这个可怜的邻居小偷,并宰了一只鸡顿好了送去给小偷让他好好养伤。
小偷是个孤儿,一直以来困苦与屈辱让他的心理扭曲的不成样子。他怨恨,怨恨高高在上的富人,怨恨将他打的半死的恶人,更怨恨这个送给他鸡吃的善人。小偷一想到每天傍晚隔壁人家传来地欢声笑语就越怨恨,还要假装善良的来看他,真是该死。
于是他在心里萌生了一个念头,如果不能得到,那不如就毁掉吧……”猴哥讲到这里停了一下,喝了口水,给自己点了一支烟,抬头看了看我,我没说话也点了支烟,示意他继续说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