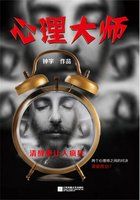雁荡谷位于西南边境。奇峰危石、千姿百态、狭长如巷,更有着‘一线天’的说法,前有东越文士大家赋诗云‘何人仰见通宵路,一尺青天万丈长。’,说的便是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地。
此些内容在《各州地理志》都有记载,慕怀风三岁时便已熟记了下来;可以说,雁荡谷乃偌大个锦州仅次于天堑崖的险地,同时亦是兵家必争之地。
云阳皇室自然知晓雁荡谷的重要性,每年都会派遣重骑把守,毕竟行军打仗的必经之所,万万马虎不得;据说当初云阳王朝平天下、定帝都的时候,雁荡谷是极其重要的关键手。
可就是这样铁骑重重的险地,早些年却出现了一伙名为‘夜枭’的山贼。据传当家的姓郭,使一柄重达六十四斤的宣花斧,江湖人称郭胖子,修为不俗,恐是那玄灵境的高手。
不知为何,郭胖子在雁荡谷谋得一席之地,召集了百来号流氓草寇,干起了杀人越货、强抢良家的勾当。对此,官府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个中猫腻可见一斑。
介于上头有人,姓郭的胆子越来越肥,有一次手持宣花斧,前往一名为‘封门’的偏远山村,全村上下一百四十五口老弱妇孺,全被这占山为王的马贼屠了个干净。
一夜间,封门村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自此,夜枭之名震动八荒六合,郭胖子更是恶名昭彰,甚至有了个‘雁荡小魔王’的称号。
当年‘封门事件’爆出,身处金陵深处的林文清勃然大怒,遂颁布了一道‘剿尽天下千万匪,自此世间得安宁。’的加急秘旨。
当时的无殇皇子还是七珠亲王,为建立功勋,义不容辞领命而去;以南北俩朝分界线--汜水为起始点,一张针对各山头匪首的大网铺陈开来。可以说,永乐三年的剿匪,除了蒸蒸子民的讼状哭诉,更多则是郭胖子鼓捣出来的‘封门事件’。
那一次,锦州境内的许多山头都被云阳铁蹄无情践踏,就连距金陵千里之外的龙虎山都未能幸免,军方扫匪打盗的手段,可谓前有未有的铁血,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喝彩与叫好。
就当云阳铁骑兵围雁荡谷,准备一鼓作气,啃下最后一块硬骨头之时,无殇亲王竟大失所望的下令撤兵;自此,这场雷声大雨点也大的剿匪扫盗落了个‘虎头蛇尾’的结局。
经过朝廷的敲打,夜枭也不像以往那般横行无忌,郭胖子也敛了性子,再没有那‘手持宣花斧,屠尽尔满门’的骇人听闻传出,不过背地里强抢良家、鸡鸣狗盗之事,这位雁荡小魔王定没少干。
无殇皇子因剿匪有功,回到金陵帝都便被授予九珠亲王,更打破林氏宗法制度,加爵大良造,掌管云阳军政大权,入驻华阳宫,权利直逼常年不在南方的挂名东宫太子--林无痕。
此等庙堂之事,以慕怀风的身份自然心知肚明。鞠梦能从雁荡小魔王手中逃脱,自然从侧面表明了八方影刹的不俗实力,至于对方提到的死亡蠕虫,武典阁内的《环境毒理学》有过记载。
此种蠕虫长年居住于戈壁滩中,通体猩红,身体有二到三寸长;俩端有时会探出犄角,长得像牛肠一般,其**有剧毒,又可顺着人的眼耳口鼻,钻入内脏肺腑,若一旬内未得解药,必定全身溃烂而死。
要想控制死亡蠕虫,也并非无计可施,《环境毒理学》清楚记载南疆湘西地区有巫族精通蛊术,其中有一类挑生蛊便可以很好的控制此类蠕虫;可慕怀风翻遍了整座武典阁一层,都未找到关于挑生蛊的记载,年幼的他也只得放弃,可就算找到了制蛊之法,慕怀风也未必能学会,更不用说控制死亡蠕虫了。
今夜听到鞠梦被死亡蠕虫蛰了却能安然活下来,岂不是说判出魔教的女子有死亡蠕虫的解药,甚至有制挑生蛊的偏门之道?
夜渐深,明月高悬,少年想着方才二人的交谈、或说想着那柄大狗腿,没有说话;席萝看着空荡荡的巷子尽头,同样没有说什么。
“鞠梦此时叛教,或说离教……真傻。”良久以后,小姑娘收回视线,声音有些惆怅。
“离教很傻吗?”慕怀风觉着能离开是无上幸事,没想到自己上司竟认为那很傻。
“为了一个文士,就赌上余生,难道你觉着不傻?”席萝脸色不大好看,蓦地转身道。
“她说过值得,还说过不后悔。”已然知道离去女子的结局,可还是想找个好受些的理由,慕怀风视线低敛,小声辩驳道。
“值得?”
席萝嘴角冷笑,“百无一用是书生,一个连来接她的勇气都没有的羸弱文士,值得什么?”
“不后悔?”
她似在回答慕怀风,又似在自言自语,最后看了一眼巷子口,低声道:“你说能和他在一刻就已足够,望你至死那一瞬,都能够无悔。”
慕怀风很想告诉她,你口中的文士真的是个经不起长途跋涉的少年,他是云阳荆家的二公子、是个很爱吃肉夹馍的家伙;还有,鞠梦叛出魔教不一定会死,那个喜好收藏名刀的书生定会想尽办法找到浑厄丹的解药。
可少年还未开口,小姑娘就当先一步走进了驿站;此时,一场小雨同样无声而落,击碎了所有的梦。
-----
夜幕降临,五凤溪街尾的萧记早就打了烊,独留后院还有几缕细碎灯光;一入后院,靠墙种植着一丛芭蕉,高不过墙垛,病恹恹的。大多数芭蕉都喜半荫温暖气候,好比豫州、扬州。院中这一丛红焰蕉耐寒,是少数能在锦州生长的蕉类,不过后院水土不好,长势稀松,这也多亏了中年老板娘的悉心照料。
芭蕉丛旁是一荒弃多年的四方天井,天井早已没了井水,其上覆着一布满青苔的木板井盖;说来古怪,天空飘着蒙蒙细雨,却没有一滴落在井盖上。
有时候声音的产生,却能显得越发宁静,好比此时后院的雨打芭蕉声、屋檐落水声,一家子的交谈声。
离芭蕉丛不远的屋檐下有一简单四方木桌,其上摆着零零散散的瓜果花生;旁边是一质量上佳的太师椅,此时上面躺着一身形臃肿的中年汉子,其身后是一中年妇女,正是萧记老板娘,一旁是个明眸皓齿的麻衣少女。
此时风韵犹存的老板娘正轻柔的为男子捏着肩,少女搬了条小板凳,端坐在四方桌旁,乖巧的为男子捶着腿,“爹爹,此次出行,可还顺利?”
在少女记忆中,眼前身形臃肿、算不得英俊的男子便是爹爹。爹爹是茶商,长年行走于荒漠中的茶马古道,用生命赚些血汗钱,很长时间都不能见上一面,最快乐的莫过于这般,一家三口欢坐在一起,磕着瓜子聊些稀松家常。
“一切都好。”
臃肿男子轻轻捏了捏少女的脸,柔声夸道:“好久没见我家丫丫了,真是越长越水灵了。”
站在他身后的中年妇人柔柔一笑,眼中尽是爱意,男子拍了拍妻子的手,打趣道:“也亏得我们家丫丫长得像你,要是随我,可就嫁不出去咯。”
被长年不见的父亲调笑,小名丫丫的少女俏脸一红,下意识的想到了一月前在店里吃面的清秀少年,起身努嘴道:“爹爹就会取笑丫丫,我去睡了,不理您了。”
说完后小妮子抓了一把花生,迈动脚丫子朝着里屋走去,左脚刚跨进门槛,似想到了什么,扭过头期盼道:“爹爹,今夜能不走吗?”
“丫丫,夜深了,去睡吧。”
看着自家女儿接近祈求的眼神,男子心头一软,轻声道:“爹爹答应你,今夜肯定不走。再说,下雨天的夜晚燥热,我还得为我家宝贝女儿摇扇子哩。”
得到父亲的保证,少女心情大好,笑道:“爹爹,你不用为我摇扇子的,多陪陪阿娘吧;您不在的时候,她可是天天念叨您哩。”
说完后,少女将一颗剥好的花生丢进嘴里,看着屋檐下的二人俏皮一笑,蹦蹦跳跳的进了里屋。
屋檐下的二人都没有说话,静静听着远处雨打芭蕉的声音,很久后男子无奈道:“知道你会怪我,可在其位、谋其事,我别无选择。”
身形肥硕的男子紧紧握着那双因长年劳作而显得粗糙不堪的手,想当年这是一双何等滑腻的柔荑啊!
跟了自己这些年,怎让她受了这么多的苦,如今更是连她的亲弟弟都守不住,这位历经人世沉浮的男子眼中溢满泪水,依偎在女子怀中,哽咽道:“是我没用,没能保住沙瓦里。”
身后妇人曲臂搂住面前自己深爱一生的男子,声音如院中雾气般轻柔,“没有什么是无可饶恕的,不是你的错,我不怪你。”
“沙瓦里呐,自小便有野心。还记得小时候与邻村群童打闹,一天便要当那山大王,其余人不服气,他便想方设法让对方臣服。”
妇人将男子搂在怀里,就像讲故事哄孩子一般,怀念道:“有一次啊,邻村有一性格特倔的孩子,硬是不服他当那山大王,没想到沙瓦里那愣子竟逼着对方喝尿,要不是我及时赶到,可真得出了大事。”
妇人讲着讲着便落下了泪,哽咽道:“你说嘛,那山大王有何好当的?”
依偎在她怀里的男子小声呜咽着,他没有说一句话,只是任泪水肆意的流淌,淌花了那张做工精良的面皮,男子正是唐不拉国主帕特里克。
小雨渐停歇,只闻屋檐边缘嗒嗒的滴水声,这位唐不拉国主起身,脸上早已恢复了平静,对着妇人道:“天冷了,多穿些衣裳。”
说完后不作停留,一步踏出了院子。
妇人看着自家男人的背影,露出一抹凄然的笑,捧起桌上的一把花生,连忙追了上去,柔声道:“带些花生,路上吃吧。”
帕特里克止步,肥嘟嘟的大手颤巍巍接过那把花生,将那数十颗女子亲手炒的花生放在了上衣口袋里,轻声道:“没有我的日子里,你要爱惜自己。”
他走到那滴水未沾的四方井盖旁,看了一眼犹有水珠的芭蕉丛,将脸上的面皮撕下,感慨道:“今后都不需要这面皮了。”
将面皮随手一扔,帕特里克纵身跃进了早已荒弃多年的四方天井内,下一刻便出现在了白月宫后方的寝宫里,炉中的梨碳仍熊熊燃烧着。
妇人双眼空洞,一下子跌坐在雨水中,愣愣看着布满青苔的四方井盖。
你曾说待你得一天下,必许我一份安稳,怎能亲手杀了我之弟弟?你曾说要与我开一间杂烩面的铺子,怎能是我一人独守?你曾说你最爱听雨打芭蕉声,今夜又为何走得这般决绝?
天亮了,妇人跌坐一夜,泪水早已流尽,憔悴的脸上看不出悲喜,只是一直在重复一句话,“丫丫,爹爹永远都不会来看你了。”
不知何时,一直躲在门背后的麻衣少女出现在屋檐下,看着跌坐在院中的妇人背影,小声道:“阿娘,你曾说过:时间会治愈这世间所有的伤。可他带给你的伤,何日会痊愈?”
“我想那伤口,此生都无法愈合了吧。”少女看了一眼墙角的芭蕉丛,泪水无声滑落。
-----
自今夜起,身形肥硕的帕特里克再没有踏进过此间后院;而唐不拉也流传出,位居白月宫的国主不知从何时开始,总喜欢对着十数颗花生发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