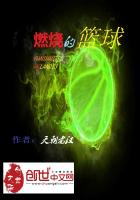他关上出租屋的窗,把喧响隔绝在外,躺到床上培养睡眠。最近他清醒很多,睡眠很少,睡眠不易豢养,像只老想往外飞的雀鸟,捞不住,就只好用幻想兜紧它。
这个扮演菩萨的夜晚如此奇妙,他身体里沉睡的东西被激活了。扮演菩萨之前,他是一个沉默的影子,贴在城市的边缘,黑夜罩下来,它就隐没了;而在扮演菩萨之后,他身上发生了变化,具体是什么他说不上来,然而确切无疑,他和先前不同了。身体里有个声音告诉他:你不一样了,你现在是“扮演菩萨的男人”,你头顶打了灯光,你在众人目光的聚焦下,是一具发光体,周遭的黑暗,戏中人生杀予夺的权力,都在你手上。
耳边响起落幕时剧场回荡的掌声,有人站起来吹口哨,有人呐喊。那一刻,他皮肤一阵痉挛,泛起了小点,密密麻麻的小点在蔓延,这是人们所说的“起鸡皮疙瘩”,可他觉得不是,这是空气中的粒子在震荡,就像水面漾起了细细的波纹,一圈一圈往外推,推到他身上,就变成了这些密匝匝的小点。这种感觉,只有看《恋爱的犀牛》或者《暗恋桃花源》时才能体会到。然而,台上终究不是台下,台上台下,是两个世界。舞台会将许多原本稀松平常的东西放大,包括感知,也包括幻觉。
那一刻他一定被幻觉包围了。现在想来,恍如大梦一场,庄子梦见蝴蝶,或者南柯梦见自己并不存在的人生,大概就是这样。
还有一部叫《如梦之梦》的戏,比这两部“混搭”得更驳杂。梦里有梦,叙述套着叙述,讲梦的人带领听者(也包括观众)穿越时空。不同维度的故事同时上演,这样的并置,不是电影也不是文字能做到的。在剧场里,观众也参与了演出。这是一个四维(零维/一维/二维/三维/四维)的世界(点/线/面/空间/时间),也许还要加上一个心理空间?如此一来,不同观众有不同观感,无数的排列组合,就有了无穷无尽的空间。因为有呼吸,有掌声,有停顿和开始,剧中人和剧外人,共同存在一个宇宙中。
上下两场,七个半小时的戏,他看得几乎沸腾起来。“在一个故事里,有人做了一个梦;在那个梦里,有人说了一个故事。”一切变成一个自证的命题:既能证实,也能证伪。他想起小学课本里写爱迪生用几面镜子和蜡烛解决一台手术的照明问题,他学着爱迪生,用两面镜子(家里只有两面镜子)互照,一下子就看到无穷的影像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产生我的同时被我所产生。
他捏自己脸,发现会痛,所以镜子中的所有影像都是假的。
那次看完《如梦之梦》,已是凌晨时分,外面下雨了,城市灰蒙蒙一片。他独自寥落地走出剧场,望见身后巨型鹅卵石一般的剧院,突然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夜并不黑,他的心却是空的。出租车被截走了一辆又一辆。他将套头衫的帽子掀起,盖住,细雨如丝。他想起戏中的“五号病人”,和自己那么像,也许所有人都是“五号病人”——
“五号病人”出来买一只煮玉米,妻子就消失在人群中了,然后他开始了无穷无尽的寻找,从上海,到巴黎,从现实到梦境。他想起母亲的早逝,也许母亲只是累了,不想走下去,所以她暂停了属于她的那部分时间,就像圣经中罗得之妻,在逃出索多玛城的那一刻忘了不该回头,于是变作盐柱。是的,他始终这样认为,母亲的去世,只是停留在时间中不肯走,而他连同这个世界还在大踏步朝前走,他走,所以时间流动,也就回不到往昔。
——“死亡就是世界加上我,再减去我。”他无端端想起这句话,忽然明白,人生无常,人来到这个世界,有开始,就必定有结束,所以,他也释然了:终有一天,他也会停在时间上的某一个点。时间是三维的,三维的时间是静止的,只有在时间轴的节点上晃动,四维的空间才会产生。可当他死亡时,属于他的时间也会停止,怎么可能还存在于四维的空间里呢?他忘了一个问题,广义上的时间并不属于他,时间没有主体,也没有客体,人寄居其中,终究要离它而去。在四维的世界里,时间依然呈线性流动,源头只有一个,将来也只有一个,未来不可预测,但不管下一秒发生什么,即将发生的事情也只有一个。
想到这里,他才明白,为什么他的第三句台词会是“爱是唯一救赎的法宝”。
《如梦之梦》中的“五号病人”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寻找他消失的妻子呢?
——因为爱。爱是多么虚无又多么强大的字眼啊!爱并不存在,是人的存在印证了它的存在——就像阳光制造了阴影,温暖驱逐了寒冷——所以,人才要互相寻找,互相慰藉,互相仇恨,互相拥抱。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爱是线性流动的时间,它穿透你我,穿透这个虚无世界的假象。
五
母亲生前最大的愿望是看他娶妻生子。她不止一次说,找个合适的,就结婚吧。他骨子里抗拒,就像他抗拒自己出生的地方。在他长大离家求学的日子,他羞于向别人提起自己老家,别人一问,他就以更高一级的行政区域来指代那个地方,仿佛圈定了一个大的范围,就能掩盖他出身的卑微。
对他而言,老家就像一样粗鄙的伴手礼,不值得拿出手,也不值得向别人炫耀。
女朋友要和他回家,他思考良久,最后以“不方便”为由婉拒了她。说实在,他并没有理由不带女朋友回家,这个家,不是他们两人一起租的房子,而是另一个他离开了又回不得的家。女朋友质问,为什么?他答,没为什么,就是不方便。女朋友不同意,揪着不放,带我回去很丢脸?他皱眉,摇头,喉咙深处咕咚一声,不是这个,你不懂。那你说呀,你不说怎么知道我不懂?你就是不懂,你别逼我!她气得直咬牙,跺着脚问,你当我什么?性伴侣?炮友?玩爽了就甩?他重复,你别逼我。我逼你?你会不会说话啊你?我搬来和你住,伺候你吃伺候你喝,你当我免费劳动力啊?!
他从未见过她发这么大的脾气,一时惊慌,心里堵着,一步步往后退。她逼近他,鼻子里喷出“哼”的一声,怎么?不说话了?默认?他抬起头,躲避着她的目光,发现她哭了,没声没息地哭了。她眼角挂着泪,忽而又笑起来,笑得断断续续,喘气,任凭眼泪滴落下来。稍后,她仰起头,深深地吸了口气说,我明白了,你从来就不爱我,你只爱你自己。
他没回应,心被捅出一个洞,风吹过,呼呼作响。
直到现在他也不明白,女朋友(应该是“前女友”)为什么要跟他回家,仿佛那个家是她的;在女朋友的观念里,她想和他在一起,在一起就意味着,要组建一个家。女朋友要跟他回去,就好像街头的流浪猫流浪狗要回家。他并不喜欢自己的家,母亲去世之后,父亲没有逼他结婚,他早就对这个儿子失望透顶了。办完母亲的丧礼离家时,他心里庆幸,母亲走了也好。有一天他想到这件事,被突然萌生的念头吓了一跳,为什么我会这么想?难道我潜意识里并不喜欢母亲?家里除了兄弟姐妹和父亲,只有母亲对他最好。他是小儿子,怎么说都有先天的优势,然而,哥哥姐姐依次成了家,只剩下他单身。如此一来,优势就变劣势,他就更不敢回家了。
他不是不想结婚,而是根本不知道,婚姻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人要结婚?结了婚,还要生儿育女。他不想进入这个集体的循环,也找不到其他抵抗的方法,这个集体的循环有着强大的向心力,就像旋涡,人靠得越近,就越容易被卷进去。
和前女友同居的日子,有一次,他们去观音山玩,车拐过一段盘山公路,远远就看见一尊金色的观音像,立在云雾中央。他印象中,观音是不会笑的,她永远低眉顺目。“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电视剧里都是这么说的,但是电视剧从来不会告诉你,观音菩萨长了一双男人的大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