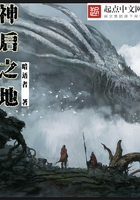第十九章当黑白遇到无常
陈国,午门斩首的菜市口
上天似乎也为这些无辜的生命而感到悲悯,在四王妃和小世子,同时被人拖到绞刑架上面的一刻,人群中的众人,指着那些刽子手,愤怒地说:“女人和孩子都不放过,你们太可恶了。”
空中的乌云,黑压压地遮住了阳光,放佛压着整个地面,似乎也在诉说着对当局者的不满。执行官看到众人悲愤的情绪,再看到上天似乎想劈下一个惊雷,将那些罪恶滔天的凶手,雷个外焦里嫩,为了赶快完成人物,监斩官的一枚令箭,“啪啦”地落在绞刑架的前面。
四王妃的头硬是被人按着套入了一个环,她抬头望着王宫的方向,最后的一点点希望也不复存在了。“也许这就是命,命中注定,我们就这样含冤而死。”
空中吹来阵阵冷风,诡异的让人起鸡皮疙瘩,一些迷信的人,合着双手道:“阿弥陀佛,您大鬼不记小鬼过,不要让小鬼缠着我。”世人以为到这种地方惨败鬼神,可以躲过黑白无常的索命,兴许可以多活几年,可是在这个乱世,谁又能保证你下一刻会不会受到牵连。
阴风里面站着的黑白无常显然已经在等待着绞刑架上面的灵魂,黑白说了:“这个女子不是还有三十年的寿命么?”无常也道:“那个即将受刑的小世子,讲来可是要统霸天下的,我们是不是接错了人。“
两人这么犹豫之间,一阵阵带着沙土的阴风,迷了众位看客的眼,监斩官用自己的袖子,挡住了阴风,对带着面罩的刽子手说:”行刑,快行刑。“
”哗啦“四王妃和小世子脚下的木板被抽掉了,两个的头就这样被吊到了绞架上,黑白和无偿这下愣住了:”他们两人是真的要死掉了么?“
无常打开记事本问:”难道他们是阎王安排的死后穿越,魂穿身不穿,谁会穿来帮助这位小世子成为,天下霸主?“
黑白拍了一下无偿的脑袋:”你一天到晚,就知道看小说,整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你看,那边,赶来营救他们的人已经到了。“
只见弥漫的风沙之中,有一个小黑点,小黑点发出了一片带着银光的飞刀,削铁如泥的刀刃,轻而易举地割断了绞刑架的绳索,四王妃和小世子的身体做自由落体,小黑点凌空将二人抱起,光速一般,飞入了附近安排好的马车。
监斩官看到犯人逃跑,急忙呼叫道:”竟然劫法场,给我杀了他。“监斩官的杀还没有落音,飞刀已经插入了喉咙,黑白看着咽气的监斩官道:”这个魂魄是我的,“
无常问道:”那么还有一个呢?“
正是那位双手合十,念叨着:”大鬼不计较小鬼过的路人。“被刽子手误认为是劫法场的,猛地将站在马车边的他,扑倒在地。路人怒道:”我只是个看热闹的。“
”你分明就是那个劫法场的人的马夫,你手里还有鞭子。“
无常无奈地摇着头说:”刽子手,你今日真是要倒霉,他那鞭子有毒,你一碰那鞭子,必死无疑。“
刚说完,那个刽子手的魂魄已经出现在无偿的面前,狠狠地说:”“该死的,不应该是那个路人么?”
黑白无常道:“此人极为虔诚,每次都让我们放过他,所以我们阎王手下留情,决定再让他多活一阵子。”
黑白无常谈笑着已经进入了十八层地狱,而路过他们的身边,赶着马车的黑衣人,带着马车里面的四王妃和小世子,八百里加急,快速地跑入了一片白桦林。在林子的最深处,马车停到了小茅屋的前方。
“我们到了。二位请下车。”若寄将自己的面罩摘掉,露出英俊的笑颜。
四王妃打开车帘,跳下车子,将小世子抱下马车,两人走到若寄面前道谢:“多谢英雄救命之恩。”
若寄一指茅屋:“这里是缯姑娘安排你们住的地方,你们就暂且在这里休息吧。”
四王妃对小世子说:“快跪下,给恩公磕头。”
若寄道:“您这是要做什么?”急忙拉住跪下的小世子。
王妃道:“请恩公收这孩子为徒弟,教他武艺,他长大之后方可防身。”
若寄面露为难之色。就听到茅屋内有人走出,说:“这孩子根骨奇佳,做你的徒弟,我觉得不错,你就收了吧。”
说话的人,正是一身青衣的缯三妹,若寄这才笑笑:“有你做保,我怎能推辞。”
就这样,四王妃以茶代酒,让小世子给师傅若寄磕了三个响头,递上一碗茶水,若寄便收了徒弟。等待四王妃和小世子在房间收拾衣物。
缯三妹和若寄在林子里面慢慢地散步,缯三妹捡了两片树叶,拿着树叶的根部道:“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玩树叶比赛,将树叶的根部和另一片树叶绕着,然后用力一拉,那片树叶断了,那片就输了,你每次总是拿到最强的一片,我总是输的。”
若寄笑:“你不喜欢认输,每次都找到一大堆的树叶和我比,其实你不知道,我当时是用了内力,将你的树叶震碎的。”
“啊,不会吧,你居然在很小的时候就玩阴的。”缯三妹拍着他的胳膊说:“我们还能不能愉快地玩耍了。”
若寄握着缯三妹的手,一本正经地说:“我来之前,和你的父母提了亲,我对他们二老说我想娶你为妻,终身伴你左右。”
缯三妹脸部一红,害羞地问道:“那么,他们同意么?”
若寄看着落叶和树上的树叶,红着脸说“他们让我亲自问你,看你个人的意思。”
白桦林的叶子,随着一阵秋风吹来,树叶欶欶地落在地面,落在在空中飞舞,缯三妹童心未泯,拉起裙子,在落叶中跳起了舞,同样的舞姿,仿若十年前,二人在大周的那片落魄的校园中一样,天上下着雪,而那时十岁的缯春秋,在雪中起舞。
弹指一挥间,已经十年,又是一个十年,今年二十岁的缯姑娘,已经是一位老姑娘,她看到若寄红着像是苹果的脸庞,宛如刚刚接触爱情的楞头小子,缯姑娘笑了:“我的想法,我想,”正要回答,“啾-”天边飞来的海东青打断了她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