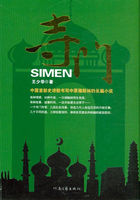十一月十一日。
我去找沈姑娘了。
不是突然地兴起,本来上周就想去了。
只是沈姑娘说她需要冷静。
于是推迟了一个礼拜,整整七天。
这是我二十年来过得最漫长的七天了。
坐立不安,漫无目的……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沈姑娘早就不属于我了,扭头走时坚定地让我害怕。
难道就靠一纸车票和几滴眼泪就能拉回来的吗?
这天早上醒来很早,五点多,和近些天一样,睡不着。
打开手机看到沈姑娘的动态,她和别人在一起了。
是一个等了她很久的人。
我从床上蹦起来,对床的学长被我惊醒,抬头看我。
平日起床我总会很轻,学长总是没有课,我怕吵到他睡觉。
今天我像造反了一样,跳下床,乒乒乓乓鼓捣一通,几分钟之后就出现在门外了。
原定九点的列车,改签到了八点。
没有等出租车,就抓起书包拼命跑。
我知道打车更快,但是我不想停下来。
嫌电梯太慢,就三两步地跨楼梯,嫌地铁太慢,就在早高峰的人群中往前部车厢一点点挤去。
我知道都是徒劳啊,往前走,地铁就会变快吗?
可是我停不下来,不想停下来。
我知道都是徒劳啊,就算此时此刻出现在沈姑娘身边,又能怎样。
我知道都是徒劳啊,可我就是不敢停下来。
飞奔,饥饿,筋疲力尽。
沈姑娘总说我行事不懂安排,因此在行程中总会有颇多的意外,让她觉得不喜。
哪是不懂安排,只是那时觉得有沈姑娘在,需要什么安排,哪里都是终点啊。
所以这次去我安排了好久,几点出发,几点到地铁站,几点到动车站,又几点到沈姑娘的楼下。
沈姑娘肯见我,我要与她说这些话,每一句都在脑中过了千万遍。
若是沈姑娘还肯陪我久些,就和她聊得多些,多的话题,也都记好了。
沈姑娘说在一起那么久,我都不很了解你。
所以啊,如果有机会,我还会跟你讲讲,我到底是怎样的人。
倘若沈姑娘不肯见我,我要给她写点什么吧,然后托谁转交……
都计划好了,可还是有意外不是吗?
谁曾想到一周之后,沈姑娘就变成了别人的沈姑娘了呢。
可还是有意外不是吗,定好七点的闹钟,为什么六点就冲出了寝室呢。
就像沈姑娘说先前在一起,是因为她觉得我成熟,可后来发现,我的成熟仅限于此。
我忘记和她说了。
那是我妈说过的一句话,她说,家里一个老公一个儿子,像养了两个儿子。
我听到那句话时抬头看看我爸,他正在开车,笑了一笑。想到他在外面工作时候的严肃认真,指挥下属时的不怒自威,还有咬着牙揍我时候的样子,冷不丁地哆嗦了一下。
后来我明白了,我的成熟,是因为那时候的沈姑娘于我而言只是朋友,我冷静地与她交谈,时不时点头表示赞同,我想起来的时候问句寒暖,不苟言笑像是看起来的成熟。
可后来的不成熟,是对着自己女朋友的撒娇,仗着喜欢,可以表现得不那么正气凛然。
而后来每天的嘘寒问暖,也变得不那么新鲜不那么珍贵。
现在一路狂奔却不明白为什么要奔走的我,还会成熟吗?
那时候的我,连近在眼前的公车都懒得跑两步,不紧不慢,赶不上就等下一辆。
一路狂乱却一片空白的奔袭,连自己都想不到可以那么快就到学校,刚好是沈姑娘中午的下课时间。
我站在下课的人流中拨通沈姑娘的电话。
原定的画面,时间比之更晚一些,场景应该在沈姑娘的楼下。
还是和计划的有些不一样。
拨通沈姑娘电话的那一刹那,我终于停下来了,像是松了一口气,但却更加地揪心。
见到了沈姑娘,可是所有的想说的要说的该说的话都变成了泡影。
一边走,一边聊,却都不是我计划中要说的。
也没有再送沈姑娘到楼下,沈姑娘说:就到这里吧。
我说:嗯。
接下来去哪。
去走走那些和沈姑娘一起走过的地方吧。
这次就我一个人。
我花了两天,整整两天,走了所有所有和沈姑娘一起走过的地方。
可是那么多的地方,我该从哪里开始走起呢。
随心吧。
走到校门口,有两班公交车。
哪辆先来,就上哪辆。
哪一站开始有回忆,就抛个硬币,正面向上,就下车,反面向上,继续坐。
十字路口,正面向左,反面向右,如果不想抛,就往前。
反正大街小巷,全是沈姑娘的脚印。
一个人坐“太空漫步”,一个人吃披萨,原来那个位置。
一个人吃牛排,单独开的包厢,也是上次的那个。
一个人对着雕像摆沈姑娘曾经摆过的pose。
蹲在我们蹲过的地方发呆,躺在我们躺过的草地睡觉。
看电影,因为沈姑娘今天也在看电影,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场。
然后是另一个校区,图书馆一起坐过的位置,另一个楼道关着门的一楼楼梯,废弃的体育场的看台……
抓娃娃机,没有沈姑娘在,我好像就一定能抓到。
直到天都黑了,我还到不了。
继续一个人去游戏厅,沈姑娘开过的赛车,沈姑娘唱过的歌房,沈姑娘吃过的烤肉。
一个人在喝咖啡玩手游,坐在湖边看瓢虫和蘑菇……
两天,逛不完。
两天,回忆不完。
我还要走啊,要回到原来的地方。
曾经昂首挺胸啊,从自己的学校去到另一个学校交换。
沈姑娘不让走。
我说我们该经历啊。
我们那么疯狂,谈了一场那么完美的恋爱。
不是说爱情的本身完美,而是它该有的好与坏,我们都有。
我们不远万里地去追星,我们在周末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的旋转木马,我们的云霄飞车。
沈姑娘让我做了太多我从未尝试过的东西。
我有两个兄弟,子郁会在我难过的时候跟我说:哥,没事的,会过去的。
而九天是这样的:他娘的像什么样子,给老子振作。
但是他们都会陪我疯,子郁在暴雨中把伞扔掉陪我淋雨,九天在最穷的时候,坐六个小时的车来找我。
但是昨天九天问我:你讨厌她吗?
我说怎么讨厌呢,那么喜欢。
九天说:我懂的,经历过。
和往常不一样的对白,差点以为他被子郁附了身。
九天说,经历过了,哪怕最后很难过,但是她让我懂得了很多很多东西,看到了自己的缺点,这样的难过,值了。
我点头,我说这样的疯狂,以后再不会有了。
是啊,我可能还会再陪哪个女孩去游乐场,但肯定不是在逃课和仅有一点生活费的情况下。我可能还会陪别的女孩逛公园,打电动,但说过的话肯定不会再有第二遍。
我不会再打一个暑假的工,然后陪一个女孩坐十几个小时的动车去一千七百公里外的城市了。
我不会再只要没课,就坐上无力吐槽的33路,去完成一场见面了。
我不会再看《陪安东尼度过的漫长岁月》了,本来我下在pad里,还想和你一起看一遍的。
九天说我去洗内裤了,洗完再聊。
然后就死在了洗内裤上,杳无音信。
我同沈姑娘说,我对你,挺拼的。
沈姑娘说,嗯,你对我是挺好的。
我说不是,是拼。
我去和沈姑娘告别,我知道沈姑娘周日有一节课,我就在她的宿舍楼下等着,怕错过,就早了一个小时去等。
沈姑娘的宿舍楼有两个口。
第一次等她的时候,我在A口,沈姑娘从B口下来,她说那边比较近。
后来我去B口等她,她从A口下来,她说这样方便。
上一回我也在B口等她,她从A口下来,她说我在给你洗提子呀。
这一次我还给她装提子的碗,这一次我等在A口,她从A口下来。
终于没有再等错了,可是还有什么用呢。
我说我要走了。
沈姑娘没有回应。
她说我要去上课。
我说我知道。
你的课表,我背的比自己的还熟。
我把沈姑娘从亲情网中删除,从此以后662这个号码就再也打不通。
前些日子有人看到沈姑娘在我空间的留言,跑来跟我说,你他妈到底是找了个什么样的女朋友。
我说:啥?
她说:我给你翻译翻译这些话的意思,然后噼里啪啦。
我说你别说了啊,我心里难受,也别说她啦,她不是那个意思。
还有一句话没说出口。
我找了个什么样的女朋友?
我只是找了一个并不爱我的女朋友而已啊。
空间的留言,往前翻也是沈姑娘的。
那时候的沈姑娘说:以前谈恋爱就是在谈恋爱,但是和你在一起就想要一起生活,面对今后的各种道路。
那时候的沈姑娘说:我以后会乖乖地,不随便使小性子,忙的时候也会回你,想为你变得优秀,变得贤惠,变得懂事,成为可以陪你一直走下去的人。
那时候的沈姑娘说:这条路你再也不能丢下我。
我那么好的沈姑娘,怎许你们说她半句不好。
只是后来沈姑娘说,其实不是那么爱你啊,只是恰好在我需要怀抱的时候,你给了我肩膀而已。
我该走了啊,这是最后一面。
大巴驶着,我面无表情地望向窗外。
好久好久……
突然天空变暗,四面狭促。
我知道那是车子驶入了隧道。
这个隧道……是进入宁波南站的隧道。
上一次驶入,是和沈姑娘来罗蒙环球乐园玩,那时候的自由如风,那时候的开心放纵,那时候我的眼里,都是沈姑娘。
那时候沈姑娘还不嫌我没有安排,让她走许多的路。那时候的沈姑娘会抓住天南地北的所有东西当话题,不会和我讲,我们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说的话了。
那时候的沈姑娘……我宁愿相信她真的爱过我,而不只是因为我恰好地出现,恰好地暧昧,捕获了恰好孤独的她。
我一下子哭了出来。
终于哭了出来。
为什么要说终于呢。
自我们分开,我没有哭过啊。
不管是难受得死去活来,还是彻夜难眠地翻着沈姑娘的记录。
别人跟我说你哭啊,哭一场就好受些。
我哭不出来。
一个人在寝室的时候,经常手足无措坐立不安,我也很想哭,我蹲下来抱着自己大嚎,但就是挤不出眼泪来。
像是溢满了泡沫的高压锅,却忘了装排气的孔。
终于哭了,逛了那么多曾经走过的地方,最触动的,原来在这里。
沈姑娘已经炸裂开心了,她说现在和她在一起的人才是她真正喜欢的。
她是有一首歌的歌词最能表达她现在的感受。
“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等我勇敢,你还是我的我的我的,你看。”
她说这样真好,她说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
还有一首歌,唱我的现在吧。
“相逢太短不等茶水凉,你扔下的习惯还顽强活在我身上,若我站在朝阳上,能否脱去昨日的惆怅,单薄语言能否传达我所有的牵挂,若有天我不服勇往,能否坚持走完这一场。”
我说就这样吧,我该走了。
室友问我,你抽烟吗?
我说来一支吧,消消愁。
他递给我,我说他娘的这打火机怎么那么眼熟。
他说找了好久才从你抽屉里找到的。
两支烟一瓶可乐,四张车票,换了一场还算可以的青春,换了一句你好,一句再见。
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