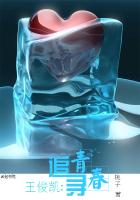淡淡的黑气笼罩着一望无际的大海,原本湛蓝的海水现在已经变得灰白而死气沉沉,偶尔有浪潮将变异的海洋生物冲上沙滩,僵硬的躯体在海滩上显示出扭曲的样子。
似乎是已经习惯这种氛围,禾轶沉默着抱着小鲛人的躯体穿过寂静的海域,目光却始终未曾触及海滩上可怖的尸体,像是不在意,又像是恐惧着某种未知的生命轨迹。
禾桑静静地跟着他,偶尔停下来,俯身用苍白的手指点上地面已经冰冷的生物的面庞,低低吟诵出一段安魂的咒语:“你们不过是人族和鲛人战争的牺牲品,被无谓的争斗所波及,如果可以,愿神庇佑你们来世再也不受这样的苦楚。”
不远处,禾轶对着海边的一个小小的山洞停下来,猛一看,这个地方平淡无奇,不过几尺见方,诡异的是洞最深处的墙角下生着几颗瘦骨嶙峋的小草。幸运的是,山洞口突出的石头几乎将光线遮了大半,极好地增强了这个山洞的隐蔽性,不过细细观察之下还是隐约感受到运转在这个山洞之间微弱的灵力流动。
从怀中掏出一把用坚硬的珊瑚礁制成的尖刀,禾轶习惯性的将自己的手指划破,殷红的鲜血在空中顿了一瞬,便自动地向那几颗小草飞去,那小草无风自动,竟将鲜血缓缓吸收,原本枯黄的叶子在鲜血的滋润下显得鲜活了许多,接着,洞口处传来禾轶短短的念咒声,伴随着声音在洞内的回响,黑暗处豁然裂开了一个大大的空隙。
“桑,走了。”像是知道禾桑已经来到了自己的背后,禾轶没有回头。用力将怀中平静的面庞压入自己的胸膛,犹豫良久,这位年轻的王却始终没有踏入黑暗裂缝的勇气,抱着小鲛人的手一直在微微颤抖,黑沉沉的眸子里满是茫然和无措。
里面,是他的族人,也是他的责任。
神印的庇护甚至已经无法笼罩这片海域,他们该怎么办?
躲藏在这个扭曲的空间苟且偷生已经数十年,他们要怎样过下去?
数十年没有诞生新生命的种族,数百年不断被捕杀的苦难,作为他们的王,我又该怎么做?
心里仿佛有一个声音一直在问,他却像是掉入了无底的深渊,只能不断地挣扎,无力的下沉,胸口却像是压了千斤巨石,坠得他的心生疼,搅得他的思想一团糟,根本无法给出答案。
“王,先知,您回来了?”突然,黑暗的缝隙后透出一双闪着机警的眸子,凭着禾轶良好的夜视能力,他轻松地辨认出,这双眼睛属于鲛人族最骁勇善战的士兵。
在看清楚撕裂空间的人是自己的王和先知后,这位士兵的神色顿时一松,挂上了浓浓的欣喜:“您还好吗?有没有受伤”
“王……”
“王回来了!”
更多带着轻松和信赖的声音在黑暗之后响起,仿佛给了禾轶无限的勇气,深吸一口气,他平复了自己的心情,缓步走向黑暗。
黑暗之后,还是一片没有生机的荒蛮地,发黑的天空中酝酿着雷霆的闪电,不时劈下来,震得蜷曲在一角的鲛人们瑟瑟发抖;没有几株植被的黄土地上缓缓涌动着冒着酸气的河水。
这里本来就不是生物能够留存的地方,甚至连鲛人宫殿的牢房都不如。然而可笑的是,现在的他却要带领着自己的族人在这一片小小的空间里艰难求生,就是这边人迹罕至的荒蛮地,还是鲛人族举全族之力,用亡去鲛人战士的魂灵换来的!
踏进珊瑚礁的禾桑还未开口便被族人此起彼伏的声音包围,周围都是激动的、疲惫的、年轻的脸庞,凄惨地聚集在一边的老鲛人也犹犹豫豫地看过来,皱纹纵横的脸上显示出几分几乎难以辨别出来的欢喜颜色,看着这些年轻人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向他们的王汇报,然而突然间,这些熙熙攘攘的声音在接触到禾轶怀里那个小小的尸体的一瞬便突然停止,像是被掐断了声线,几乎所有围绕在禾轶身边的鲛人都将目光集中在了那个仿佛在安睡的孩子的身上。
幼崽对于自从进入大海便没有后裔降生的鲛人族来说意义太过重大,而这个孩子凄惨的死状更是点燃了这些鲛人们心中愤怒的火焰,低低的叱骂不断地响起。
“******,又是那些该死的人族!非得将我们赶尽杀绝吗?”
“干脆杀到东边去,弄死那些道貌岸然的人类!”
“这都多少次了,真当我们好欺负吗?”
沉默地将孩子小小的身体放上祭台,禾轶的脸色在族人低声的咒骂和隐隐的啜泣声中渐渐变得苍白起来。
“孩子,我的孩子……”啜泣声终于转变为尖锐的哭泣,一位面色苍白的女鲛人从蜷曲的人群中立起,瘦弱的身子用尽全力跌跌撞撞地奔过来,扑倒祭台宛然在安睡的孩子身上,用颤抖的手不断抚摸着小鲛人已经冰冷的面庞,成串的珍珠从她莹白的脸颊两侧滚落下来。
“我,很抱歉……”看着眼前这个好像世界已经崩塌的母亲,禾轶不知道该说什么,湛蓝的眼神里满是愧疚和忧伤。
伏在孩子僵硬的身体上,悲痛的母亲抬起头来,直直盯着自己的王,她问道:“王,孩子不过是跑到海陆相交的地方,原来神印能够庇护到的这片相交之地,现在也成了我们无法涉足的危险区域了吗?”
这句话像是传染性极强的瘟疫,令嘈杂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下来,将略带惊恐的目光投向自己的王和先知,鲛人们就像是惊弓之鸟一般惊慌无措。
禾轶顿了顿,动了动自己的嘴唇却说不出任何话来。
然而他的沉默也坐实了某种猜测,一种绝望的情绪渐渐弥漫在寂静的空气中。
“嘶!”
突然伸出手撕开胸前深蓝色带有隐隐星光的衣袍,露出心口自继承神印就从未凝固的伤疤,一缕微弱的光芒从禾轶胸口鲜红的伤疤后透出。
“神印的光芒未曾消散。”用温柔的眸子凝视着胸膛前柔和的光,禾轶低低地说道:“神从来都不曾抛弃我们。”
齐齐向着禾轶跪拜,沉浸在绝望的人们像是终于找到了寄托:“神佑,鲛人!”神带领着他们走过崎岖的岁月,神赐予他们食物,神给予他们安居之所,所以,所以神不会抛弃他们的!
不敢想,不敢想如何被神抛弃之后他们会怎样。
一直沉默着的禾桑走上前,用一把银白的刀子熟练的挑开手腕,对准禾轶胸口的伤疤注入汩汩的鲜血。在鲜血连续不断地浇灌下,那光芒渐渐变得耀眼,衬得禾桑素净的脸庞格外苍白。
“不会。”像是对那个悲伤的母亲的回应,又像是对整个族人坚定地宣告,禾轶坚定地说道:“只要我在,只要有神印在,鲛人族绝不会消失。”
祭台下的鲛人狂热地注视着那道光芒,目光里重新染上了希望,再次向着禾轶俯身跪拜——鲛人王的胸口,那里,是神印被封存的地方。
神器有灵,卑微的生灵无法能够驾驭,然而剖出心脏的鲛人王却是放置神印最好的容器。以鲛人王的身体为媒介,用鲛人族最纯正的鲜血浇灌,就算是神器也会染上俗世的气息,赋予在一定范围内人族攻击对鲛人无效的能力。
就像是用鲛人战士的亡魂为代价来祈求这片庇护之所,只要代价足够,只要足够信仰,没有什么是神做不到的。
然而,一颗小小的怀疑的种子却不断地在禾轶的心里发芽,作为神印的保存者,他能最直观的感受神印的作用,每时每刻,神印的守护范围都在不断地缩小,鲛人族莫测的命运黑洞却越来越大。
站在祭台明与暗的光线交错处,禾轶静静地看着台下自己的族人。良久之后,他打破了沉寂地跪拜:“我有事宣布。”
众多目光聚集在了他的身上,带着绝对的追随与信任,像是给他,又像是在他的身上看到了神的身影。
“我决定,去和人族谈判。”
“王,您怎么能,怎么能去和人族谈判??!”最先反映过来的是脸上还挂着泪珠的失去孩子的母亲,陡然尖利的声音划破寂静的珊瑚礁,她苍白的面庞上有被背叛的不能置信和被抛弃的悲伤:“我们那么多被屠杀的同族,我们那些还在被奴役的同族,我们被迫藏身这片荒凉海域的苦楚,难道您都忘了吗?”
“我从未忘记过。”转过身缓缓扶起那个歇斯底里的母亲,禾轶的眼里满是隐忍的痛苦。
“正是因为记得,我才做出这个决定。”
“一时的妥协绝不是退让,而是为了积蓄力量。”
“人族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卑微的族群了,他们甚至将强悍的龙族都逼入了大陆东南角的深湖,我们必须做出改变。”
台下的鲛人们微微有些骚动,但很快平静下来。一些头发灰白的鲛人怔怔地看着自己的王,表情恍惚又可怜,仿佛还沉浸在过去的旧梦里。
“目前陆地大旱,淡水资源极其匮乏,而我们,拥有得天独厚的控水能力,这是神赋予我们的优势。”
“神印的威力越来越弱,族人的数量越来越少,凭借着这笔暂时的交易,我们能够争取更多的不被人族追杀的时间。”
“这段时间,将会成为我们重新崛起的契机。”
用手捧起地上流光溢彩的珍珠转向跪拜的鲛人,禾轶温和地注视着自己的族人,低低的声音回响在每个鲛人的耳边:“鲛人不需要眼泪,上天赋予鲛人更长的寿命不是用来流泪的,你的泪水只会让他们更加猖獗。”
渐渐有珠子坠地的声音响起,一些弱小的鲛人甚至小声啜泣起来,然而这啜泣声在禾轶巡视一圈的目光下渐渐平复了下来。
“我支持您的决定。”久不做声的禾桑眼里闪过一丝挣扎,然而最后还是平静下来,翻转受伤的手腕搭在胸口,她向着禾轶俯身跪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