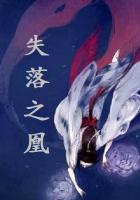老妖人劫持李先道一口气就在迷宫似的山涧与密林叠嶂之间跑出有十几里之遥。可是老妖人一头跌倒,再也无论如何也立不起来了,就是一头濒临死亡的驴子,没有一点兽性可发。李先道一看这茫茫大山云蒸雾绕,鸦悲猿号凄惨至极。可是,他懵懂着竟无法辨别方向,心想是一定要陪定要死的驴子于深山。
“李医生,你不会撇下我不管吧?你看,我实在是不行了,挽留不得你,要溜请尽快。”
“我是想过,可是我迷失方向了。”
李先道坦言相告。
“我告诉你,记好了——从这里出发,沿着山涧到底,翻过一道小梁,再顺着大的河谷走到两个绿滢滢的水潭。要记住,往右上方走是斡尔塔人的地盘,往左上方是去往安河你家的方向。”
“你为何告诉我这些?”
“也许是人之将死其心也善吧。况且,我们并不冤仇,我死,没有理由也要你陪葬。”
“我不能走。告诉我该怎样帮你?”
“我就知道,你不会扔下我不管的。”
“是你的诚实使我改变了注意。”
“我浑身无力,比灌满铅还沉重。我知道你医术无边,定会有办法的。我中他的毒又因运功打斗,已经散布至全身。眼看就要分出胜负,不较量我真是咽不下这口气。”
“我也不敢保能有十全的把握让你脱险,不过我尽力而为,不要说话,我开始了。”
李医生早在心里盘算好——荆棘刺迅速刺进十宣血,并释放出晦暗的血液。理应是用银毫针,那不过是书本传授的技法,可是适逢这特殊的环境,就只能活学活用了。此血督领任督、奇经八脉,谓之穴位之统督。它不但能回阳救逆,拯救生命于危机之时;不为人参透玄机的更是针刺放血使血气不回归心筋,气血外流必然导致淫毒外走,这才是施治的关键所在。
老妖人面露欣慰的笑容。
这还不够,旋即针刺人中、百汇和合谷,相辅相成,如同君臣佐使主次分明,共奏其效。
“最后一项是把你的舌头尽量探出来,能伸多长就可能地神多长。别怪我非常时候非常治疗。”
这也是他的收宫之作——,此乃心经之脉,名为金淋腺,开窍于口。一针下去,嫩滑的舌头顿时鲜血盈口,比搏斗中五脏六腑具裂时的样子还要惨烈。
“你的血液太多,我要给你多放一些。”
妖人居然还能顺利地把李先道引领回山寨。
李先道从老妖人的女人口中知晓他的名字叫巴彦陀,族谱上不曾有过的民族——翰伦卑族。他是部落四大护卫之一,生性好斗。他的妻子为人谦和,说话透着女人温婉的灵光。而且她相貌并不丑,还可以说是一个曾经十分风华的美女。只是她好像碍着某种难言之隐,闪烁其词;想说出来,又有顾虑,还是没能说出来。围坐在火炉旁还有两位把自己很不见外的翰伦卑部落的医生。他们一致的目标都是围绕巴彦陀的病情展开——
“巴彦吉庆老弟,你平日里倒是颇有建树,今日为何不开口说话拿个主意?”
“你何从不知,我平日里主要搞些个日常杂病兼些金创外伤,对这路却是不甚熟悉,巴彦胡特兄弟。”
“一点不假,我们翰伦卑人向来光明磊落,药草是用来救人治病而不是用来做伤天害理的事的。”
“我建议还是尽快请我们这位汉族兄弟吧,既然巴彦陀能安然返回,他的能力是不容怀疑的。对不起,李先生,请恕我直言,主人把你带回来就事先考虑过我们这点能耐,必然是有他的用意的。事不宜迟,我们莫要磨嘴皮子,巴彦陀还躺在床上等待急需治疗呢。”
在说话的时候,李先道的心就很纠结,并不是两个男人的说话让他不好下台,而是他纳闷,以旁观者的身份从一个医务工作者惯有的眼光去看待某件事就大不一样了。按人情常理夫君突遭不测其女人自然而然会忧心忡忡,面容、神情、举止,焉能有无动于衷,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
“我看这样吧,”李先道不慌不忙地温和的口吻说,“谁来挑这大梁,征求一下巴彦夫人的意见如何?”李先道貌似城府空洞的样子,眼巴巴瞅着大家。
“这……,”巴彦胡特的汉子陡然语塞,老鼠样环视的眼睛充满警觉。最后一眼是从巴彦夫人身上划过去的,像贼人的眼睛一样飞快。
巴彦吉庆倒是不露声色,一脸茫然无邪的样子。“这——未尝也不是不可。”
“各位叔叔们好。”进来并且很有礼貌地说话的小伙子,走路带着风就到了近前。后面跟着的这位要腼腆得多,或许是不喜欢讲话的缘故,所以一直没吱声。
“来得好,巴彦特,巴彦陀的大儿子——你们看如何,他毕竟是家里的大男人了,有处理家事的能力了。”
李先道明白巴彦吉庆的意图,但自己现在好像只热衷于第六感觉的探究。不过,有一点他不能说也不敢说,只有在心里对着自己说:“蹊跷,太离谱了。怎么就好像一个人呢,对,就像我记忆深刻的老毒物,简直就是他的翻版。看,他的深陷的眼窝而浑圆的眼睛,他的山根浅挺又略带鹰钩的鼻子,还有他的方蒲团脸型,无一不像;他的体型,甚至他的头发都无一不像。巧合,真的就有这般天巧之合?为什么两兄弟无论从哪里比较都没有一点相像之处呢?”
“我们需要你拿个主意,看用哪位先生合适,我们你是知道的那点本事有限。事不宜迟,你老子还在床上哩!”
“我当然依从二位本族的先生的意见。我知道我们的劲儿是往一个地方使的,作为长辈你们比我更有权决定。”他注视着李医生,眼睛里似乎有话要说。
“那我们就一致恳请李医生受累吧。李医生,你不会推辞吧?我们都谢谢您。”
“是啊,两位叔叔都代表我的意见。我本人也是满心希望、并真诚地恳请李医生救我父亲的命。”
“实不相瞒,我要让大家失望了。”
一语使得众人惊,都不知所措。
“是这样,我切过他的脉——颇使我力量有限,恕我直言不能拯救他的性命。”李先道蹙眉很是为难的样子,语调也有些忧郁。
“这都是债呀,做的孽!”巴彦陀的夫人突然说道:“把我抢上山寨以后就信誓旦旦地对我说,‘绝对改邪归正’,可是话都说到扭屁股上了,成天惹是生非、打打杀杀,这不现世了吧!‘’
李先道心里一阵紧怵,没想到缘由竟是这样。难怪夫妻同床而心在北,强扭的瓜儿真不甜。
“还是请李医生救下他这条命吧,看在孩子的面上。”
大伙都齐刷刷地盯着李先道,像是这句话说出了他们的心声;可是更多地李先道觉得他们的眼神流露出的是怀疑、惶惑、不信任以及不甘心。
李先道除了会看病外,还会看相以及心声。
“我说过,我无能为力。不过,有人能救,解铃还须系铃人。”
“那能行得通吗?一辈子的冤家对头了。”巴彦吉庆忐忑地说,“这不是自找没趣受吗?”
“我去嘛,我是老大,有责任和义务。”巴彦特的话很果断,“就算龙潭虎穴我也要去试一下,实在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大家都望着他,没有说话,可是都心照不宣,只有他自己一人还蒙在鼓里呢。
“不准你去,”他的母亲厉声说道,“偏不让你去。这事没得商量。”
众人哑然无声。火盆里青冈栎炭上虽然蒙上了一层灰蒙蒙的灰,可是里面散发的热能仍然十分烫人,虽然围坐在了它的跟前,真要是以身试火恐怕稍懂一点人情世故的人都不会冒犯不必要的虎威,做事就是这个理儿。
“我不希望和斡尔塔家族有任何瓜葛,明白吗,孩子?实情告诉你吧,我是二十年前巴彦陀从斡尔塔部落抢回来的,今天你再去央求人家会有好结果吗?”
“这……,”巴彦特自觉尴尬,再往下说也无必要,结果已经很显然。他默然了。
“不过,还是求求李大夫吧,他已经救过你父亲一条命,要不然他早就……,快,孩子们,给你们的恩人跪下叩头……”
…………。
李先道被人供着下不来台,只好把自己那点手艺再奉献出来。而两个族医则像两个跟屁虫,缠着硬要目睹神医的妙手回春。而这期间,李先道只是勉为其难地给做了些不让毒物扩散的基本疗法,使病不至于加重,但也不能除却病源。他似乎有意拖延时间,心里另有盘算。到底他是为了什么?没人知道,他想知道的事情恐怕不是外人能够轻易发现得了的。
傍晚,两个终于无可学习的、耐着不肯离开的部落医生最终还是怏怏地离去了。天际有乌云密布,暴风雨很快就会笼罩翰伦卑部落,涤净人们蒙尘的、被尘埃伤害过的以及正在和正准备受伤害的心灵——在快乐的人看来是一场逢时的及时雨。
这个时候巴彦陀夫人终于有了时间倾述,不,应该是方便了一述内心的惆怅——而李医生有可能是她一生中遇到的最愿意聆听她的观众,还有,她还从没有把心扉向儿子打开。她愿意和盘托出,因为珍藏了几十年受了几十年内心的煎熬,她感觉沉重得再也无法忍受了……更害怕某一日铸成大错将后悔莫及——
“先生,我是个可怜的妇道人。”她有些激动。“我本姓薛,单字一个婷,汉族人。家住开县双庙,薛云泉商行老板的幺女儿。”提及薛云泉脸上明媚的荣光顿时消逝,阴郁、哀愁凝聚拢来,只差没垂下泪来。我原本也是个富家女儿,那时候日子过得多体面。十七岁那年,我父亲,也就是薛云泉商行老板,被一个无理取闹的和尚装束的凶恶人打伤。在场的一干众人没有一个敢挺身而出的,是怕事,还是怕担事,总之是躲着事。哎……,那年月的人心呀也糟蝗虫吃了。”
“妈妈,那后来外公咋样了?”二儿子追问。
“你只管听着就知道了!”哥哥反驳他。
“你们的外公后来留下了残疾。……我还是接茬说吧——,关键时候出现了一个英雄,他的心是美好的。他的武功虽然不是很好,但我看来比起那些所谓的高手要强得多,至少他够男人、够勇敢。前提是怎么打他或打得怎么样,只要他满意,痛快离开就行。精爽的一个小伙子被打得一团烂泥,怎么着坚强立起来都不成,就算双肘支撑着趴着硬是不肯躺地,这就叫骨气。……伤小伙在我家养伤一月有余,不知不觉中我们变得很熟悉——没有栅栏的世界才变得最纯洁、善意、美丽和富饶。我们的眼睛里都是蓝天、白云、湛海和百灵鸟动人的歌喉。世界多美啊!美丽的世界里所以没有痛苦,只有憧憬,只有兴奋和追逐梦想的冲动。我们那个时代还懵懂着啥子是爱情,真是愚蠢得可笑。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玩笑说‘是受地球引力所致’。后来,我做错了一件事,跟着这个男人跑了,不,有人说是私奔了也正确。”
“你不是私奔了吗?怎么又出来抢劫一事呢?”大儿子问,他觉得母亲是一个有许多传奇故事的女人。
“那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别打岔。”
“你的命也够苦的了!”李先道说。“我想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全部故事。对一个在追求幸福的路上磕得遍体鳞伤的女人我深感同情,真是真心离伤心最近。”
“叔叔,你怎么就知道我妈妈的全故事,我们咋就不知道呢?”二儿子不解地问。
“叔叔是何等高的智商,而你还抵不过蚯蚓的智商,能相提并论吗?”老大揶揄老二,不过,他们平日里斗嘴已习惯,谁也不计较谁。
“李医生说得极是,料想你已经猜想到了结果。我这愚笨的儿子,我看还是告诉他们为好。”她顿了顿,眼角的余光扫视了一下孩子的父亲方向的屋子。“此人斡尔塔族,李医生已经见识过了——现在的法老先生,他的名字叫斡立月。”
“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是啊,怎么会这样.“二儿子巴彦昭也附和,“怎么会这样呢?“
“一切都有可能,而且是你父亲所为.“李先道说.“你父亲看来不是一个常人,最起码不是一个按常规思路出牌的人.这已经够了,几十年的抑郁今天终于吐露出来了,让孩子们知道不一定就是坏事,只不过我是个外人,我会守口如瓶的,请放心.“
“你我倒是十分放心.不过,我不想我们本族的人知道得太多,不是怕我脸上蒙羞,我一个糟践够了的女人还有啥面子可谈,而是怕影响到孩子们的声誉,他们是最无辜的.“
“衣服脏了可以洗,面子仍然干净,可要是心脏了就真是无药可救了.我们这代人追求的可以不看结果,但可以享受过程就足够了.看来,你已经有主意了?“李先道望着她,真诚地问.
“你指什么?“
“在巴彦陀病情方面.''
“我想还不够火候,“她打量着孩子,目光是深邃的,遂又慢慢移开,对着李先道的目光,四目交谈.“卤水点豆腐,真是一点就开。
“是,我看快了.我来帮你施加点外力.“
“那甚好.我谢谢你.“
着力点在大儿子巴彦特身上,李先道就是杠杆,给他传力.一切都正如他想象的那样,进行得十分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