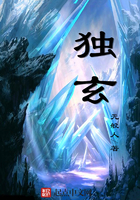第四十章何谓,无谓
天空破晓,金乌破空而上,光芒照耀大地。
华美的紫色光芒,华美的白色光芒,交织在一起,编制成为一个破碎的梦。
骨鸣崖,是净化之舟附近的一座高山,只不过这座山虽然称之为高山,但是其实并不高。
约莫五十米的高度,只能算群山之中的小众。
不过,当你登顶之后会发现,入眼而去,一片平整。
是那么的荒凉,那么的寂寥,五十米高,方圆百里,皆是如此。
相传,在上古世纪之时,神魔大战,有人一剑直接斩动天地,从而造成现在的情景。
又传,在上古世纪之前,这座山,本是世界之树的生长之地,是通往上界的通道,不过后来被人毁去。
总而言之,这种已然随着长久的时间逝去的存在,自然而言的就有很多版本的流传。
在骨鸣崖朝北的方向,是净化之舟前方的大片大海。
两地相距不过十里,说远不远,说近不近。
清晨的阳光,斜斜的照耀着,那漆黑的岩石,发出黑晶的亮光。
她转过头,看着半蹲着的他:“正因为是在这种地方,所以我也想弄清楚一件事。”
他抬起了头,看着她。
她弯下腰,三千青丝侧于耳畔。
他瞳孔一缩,那一年,那一日。
书桌后,一男人正在笔墨浓砚的书写着。
男子的脖颈处一把短剑,裹着黑衣的手,环抱着他的肩。
划过的脖颈,流下的鲜血,是恶。
无力的身子,倒下的轨迹,是罪。
她后退了一步,她看着他。
看着他眼眸之中的慌乱,看着他瞳孔缩如猫眼的惊恐。
“大约三年前的事,是你吧。”
声音平静,却不平淡。
他缓缓的点了点头,很诚实,很坦率。
她站了起来,身后是遥遥无际的天空。
淡紫色的光芒,将她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
她苦笑了一声,面容略带伤感:“谢谢,心里清爽了很多。”
他只是静静的半蹲着在那,接受着阳光的洗礼,他也许应该百分之八十,懂得秋湘玉所想表达的意思。
“那个人,对她应该很重要吧。”
他无神的呢喃道,他看着自己的双手。
在净化之舟听到的话,他还历历在目。
他的双手,沾满了鲜血,杀人就是杀人,不管用多么冠冕堂皇的语言去修饰,杀人就是杀人。
他愣在了那里,破晓的黎明之光,映射在他的身上,照亮起一片白光。
此时的他,有点像-秦义绝。
像那个白色的秦义绝。
镜头一转,浑身浊气蔓延的秦义绝,紧闭着双眼。
睁开冷酷无情的眼眸,淡淡的看着前方。
紧紧握住的双拳,黑色的浊气在弥漫着。
随着手心伤痕鲜血的落下,周围陷入一片白色。
白茫茫的空间,鲜血在落下,一滴又一滴。
……
竹篓编制成圆壶,高高的斜挂在高台上,一个又一个,整整齐齐的摆放着。
一滴清水,那是露水。
巧妙的结构将其引渡在此。
晶莹的露水划着一个美丽波纹,在干净的水平面荡起涟漪。
干净的灰白陶瓷碗,安静的躺在木桌上。
“这就是现在的你。”
溟老语重心长的说着。
在一旁是少年时期的魂,此时他才约莫十一二岁。
陶瓷的壶,装着清冽的水,随着水的滴落,涟漪一圈一圈的向四周排开而去。
云雾缭绕的高山之上,一间陋室在其安然的竖立着。
天空白茫茫的一片,一颗青树高松的立在一旁,宛若仙境。
“无法被任何事物扰乱的虚无,但是这么一来。”
苍老的手,皱褶的皮,握住水壶。
清冽在水在碗中打一个回旋,那么的自由。
满满的,在碗中叠起,那么的圆弧,那么的满,却不满溢而出。
他站在一旁,静静的看着这一切。
白色的胡须,随着话语而轻轻略动:“但是……。”
轻巧的手指,轻轻的触碰碗的边缘,涟漪层层排开,却依旧不满溢而出。
“会被轻易扰乱。”
溟老抬起头,额头上的十字伤痕虽然依旧淡化,但是依旧让人在意。
一滴晶莹的露水再一次的落水,时间轮转不休,万物皆轮回。
虚无如道,本是无迹可寻,却可被扰乱。
看起来有些逻辑不通,其中的玄奥又有几人可懂。
“用人情充实自身后,还要保持不被扰乱,难如登天。”
“但要朝拜努力。”
魂静静的看着溟老:“为何?”
云雾缭绕的天空,快速的行迹的云层,在风的追赶下,变幻莫测。
山林,被盖上一层朦胧的袈裟,在高耸入云的高山之中,你无法看清被环绕的群山,你只能看到朦胧的天空,朦胧的世界。
“为何不可是虚无?”
“因为我希望,因为我希望你如此。”
溟老眯着眼,慈祥的看着魂,皱起了白眉,希翼的看着他。
眼中的关爱,不言而喻。
涟漪扩散,一层又一层,一圈又一圈,再一次,再一次的轮回不朽,循规蹈矩的凝结滴落。
“虽然虚无的你不会被扰乱,但亦不能充实自身和他人。即使能,也无意义。”
溟老向前走了两步,继续说道:“这与死同义,或者说…咳咳。”
溟老睁开了双眼,忧愁的看着魂:“今天到此为止。”
伸出双手,掰开一个豆沙包,分其两半,递其一于魂。
“吃吧。”慈爱的目光,关爱的语言,在他心中感受不到任何暖意。
毕竟,他虚无。
微风轻动,摇曳的竖起,在和滴落的露珠无声的演唱着虚无。
“有何意义?”
“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