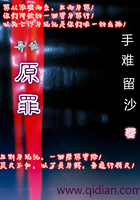我站了起来,像一尊2米的雕像。(你的身高不是173cm吗?——是的,你的记性真好。但你忘了,我现在是雕像,而雕像一般都是有底盘的)
我的头微微低着,腰没有挺直,手臂自然下垂。如果创造我的工匠是一个痴迷于肌肉线条的怪咖,那我的腹部会被勾勒出立体的线条,我的背部会完美地显现出铁一样的三角肌,我的两条手臂则会在由石灰组成的皮肤表面上冒出几根勃勃的筋脉来。
我希望创造我的工匠是一个中国人,因为他如果是一个外国人,我可能会没穿衣服。
我会被各种博物馆收藏,然后站在断臂的维纳斯身旁.....
“你站起来干嘛?怎么,垃圾捡完了?——那这边的几个烟头算怎么一回事?刚才说你眼睛不好使吧,你还不乐意。这回无话可说了吧。”
语言,本来是一种和蔼可亲的东西。因为它可以交流,可以换取说话双方的想法。但此时我却察觉,它是女人嘴里的炮火、AK47,瞬间把男人的遐想炸成一片烟雾。
“不好意思,房间的灯光有些暗,我没有看到。”我把垃圾桶放下,看着她。我的声音听起来带着一种反抗的味道。
“是吗?那为什么我可以看到,而且看的一清二楚。这怎么解释?”
说话的时候,那个女人把手里的筷子一松,手臂交叉地抱在胸口,然后身体靠着椅背。我读过心理学,她的这种坐姿,是警戒的意思。
由于她是坐着的,所以看我的时候她是抬着头的。于是,我们就这样四目相对了。
包厢的上方,有一盏6头的欧式吊灯,复古的暗金色灯光营造着一种奢华与尊贵的氛围。
我看着她,我的第一感觉是,她好漂亮~
我的第二个感觉是——被这么漂亮的女人骂几句,那又怎样?!
我的第三个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感觉,真剑!
.....
那是一张精致的脸:眉骨很高,眼睛很深邃,鼻梁很挺,嘴唇很性感,看起来不像是东方人的面孔,倒像是一个外国人的。那种五官,一点都不柔和,像是用刀刻出来的,有一种直刺视觉与心灵的美丽,让人看过一眼,便再难忘记。
“不好意思,我,我——”
我说不出完整的话来。理由,我想不用细说了吧。
她咧嘴笑了笑,带着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自信,那是一种只属于女人的由内而外的自信。
“既然知道了垃圾在哪儿,那就做你该做的事吧。”
我不知道她说这话的意思,算不算挑豆我。因为烟头的位置在她脚下附近,很明显,她抽完烟之后,把烟头扔在地上,然后用自己的高跟鞋踩灭了,而且还转了两下。
“这恐怕....不大合适吧?!”
我虽然明白男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冲动的,但我没有那个胆量。十几年的教育,加起来比我都高的书,此刻正束缚着我的思想。可我的内心深处却很想臣服在女人的脚下,借着捡垃圾的名义,满足自己对女人的精神占有欲,近距离地观看那双让我身体发烫的长腿。
——不,这是偷窥!
为什么不,你个心口不一的男人,你真虚伪!
我变得撕裂起来,道德的名义此刻在我的身上极度脆弱,我甚至抵触脑海里的说教,开始有了一种冲动,一种不计后果的冲动。
九月份的夏天深夜,是比较凉的。
她却穿着一件单薄的白色七分袖衬衣,一件职业的黑色半身裙。空气里弥漫着厚重的酒味,还有挥散不去的女人香水。
如果现在是在拍电影或者电视剧,那么此刻的我,正是荧幕里的那个无知少年,承受着灵与肉的对抗,正一步步迈向漩涡,一个灰色的边缘地带。特效师会把我头顶上的光,变成极具冲击力的红色,镜头会重点拍摄那个女人完美的身材,以及裸露出的肌肤,音效师则会穿插一系列悲壮的混合交响乐,侧面说明我即将崩塌的精神世界。
“有什么不合适的。难道我会喝你的血吗?”
女人的话,像一个巴掌,啪的一声,让我从我的世界里清醒过来。
“嗯。?”
我有点懵,不明白她会举出这么另类的例子。
喝我的血?——你又不是吸血鬼.....
我突然很想笑她,因为她看起来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没想到竟然会说出这么摸不着边际的玩笑话。
我正莫名地笑出声来,谁知,“刷”的一下,那个女人就这样从我的对面像一阵青烟一样从座椅上凭空不见。
这怎么可能?
除了魔术/哈利·波特/张震讲鬼故事,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诡异的画面。
下一秒,我还没缓过神来,女人那张精致的脸便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她的眼睛是那般的鲜红。
一道亮光闪现之后,我的脖子便传来一阵刺痛,像是被什么锋利的金属给拉了一下。
我因为疼痛正要喊出一个啊声来,女人的一只手便牢牢地捂住了我的口鼻,然后我因恐惧、疼痛、缺氧,脸上的表情开始剧烈扭曲,眼睛也瞪的老大,整个人有一种快要被憋死的模样。
这究竟是怎么了?
我怎么会遇到这么不科学的事。说好的建国后动物不许成精的,一切牛鬼蛇神不是在文革时期,都被铲除了吗?
弥留之际,我感觉我的脖子被一个小小的吸盘一样的东西,紧紧粘住。
我不能说话,周围的一切都好安静,只能听见咕咚咕咚的声音。
我知道,那是一种饥渴到一定程度,疯狂吮吸清水的声音。只不过,那清水,换成了我的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