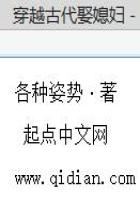庙堂与江湖,总是难以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江湖难以左右庙堂的长远,却是可以影响天下的天平盛世。
九国之时文治天下,各朝才俊皆是手捧四书五经念叨着之乎者也,一众舞刀弄枪的侠客有如过街老鼠,暗无天日。
可如若不是娄烽漫从冷平川的铸剑坊借得十万兵甲,秦越便不是这个秦越,庙堂也不是这个庙堂,江湖,自然也不会是这个江湖。
直到此时,天下人才幡然醒悟,文可治国,武未尝不可。
即便京城里头的那位天子掌着天下生杀大权,他也不得不信奉民心。位高者,怕的便是民间的流言蜚语。当年白凤城冷家之功高不可没,所以造就了今天的白凤城成了与京城并驾齐驱的武城,天下也成了文武并重的天下。
渐渐的,那些政客名流士子也摘了腰间的上等玉佩,悬上了打着冷家铸剑坊烙印的刀剑。由此一般,冷家铸剑坊成为万众敬仰之地,门庭若市,千金难求一器。
本是归隐山林博个淡泊名利之说的赵家剑冢,在这文武并重的世道,终于再也耐不住那份清寒寂寞。
红尘琉璃权势在前,终究少有人能真正的淡泊名利直指佛心。
冷风杨所谓的盛事,不过是赵家剑冢不甘落了下乘的私心,想与冷家铸剑坊在这江湖之地平分天下。
虽然各自皆是名声在外,却应征着傲者不为伍之说,娄烽漫与赵家剑冢几人打个照面,便是寒暄的念头也没有。娄烽漫身为庙堂阵营的拔尖者,对于江湖上的恩怨情仇不敢有太多的情感,无论天下人是青睐冷家铸剑坊还是买赵家剑冢的账,总之,这天下也不需要他娄烽漫再作出一人借兵甲十万那般青史留名的丰功伟绩了。
家大业大的冷家铸剑坊,一辆马车自然入不得账本,所以怀揣着马车还是白送的坐的舒服,银子还是握在手里的踏实的想法,娄福跟车行老板苦口婆心才杀价买来的马车,只是在这白凤城游览一番便再次被换成了白花花的银子。
不知为何,老娄执意要带着赫连寂禅和他的那个小不点一道进京。
当年冷平川借出十万兵甲便外出游历,五年后归来,身边就多了个怀抱木剑手牵乌龟的小娃娃。
不到一年,冷平川撒手人寰之际,不是交代着如何振兴祖庭,而是交代儿子冷传扬要对赫连寂禅百般照顾。父命难违的冷传扬将赫连寂禅视如己出,虽然冷平川未曾说出小娃娃的身世,但是冷传扬却渐渐发现,这小娃娃古灵精怪聪明通灵,身后必有一番天地。
冷府之前,马车金贵了几分,便是那些细软也是上等。冷传扬百般不舍,可赫连寂禅自己却毫不在意,牵着他的小不点跟着娄烽漫上了马车,不哭不闹。
秦思省躺在宽敞的马车上,头枕着金丝绒,嘴里叼着根野草,侧眼看着眼睛出神的娄烽漫,道:“老娄,不说说?”
娄烽漫回神,神色回味。
“说什么?”
“得!装糊涂!”
秦思省瞪了眼娄烽漫,起了身子看着躺在娄烽漫怀里,正自顾自的逗弄着小不点的赫连寂禅,方才还龇牙咧嘴立马就换了个自认人畜无害的笑脸,道:“赫连小娃娃,你家人呢?”
赫连寂禅头也没抬,“我没有家人。”
“没有家人?”秦思省轻声一笑,冲着赫连寂禅挤了挤眉毛,道:“那你是石头里蹦出来的?”
赫连寂禅轻灵的扬起脑袋,耸着鼻子冲秦思省一阵欢笑,手舞足蹈好不欢快。
“石头里怎么能蹦出人来呢!你个大笨蛋!”
听着赫连寂禅实实在在的嘲笑,秦思省砸吧着嘴一阵无奈。在东阳村不算是舌战群儒那也是一人骂一村不带卡壳的,没想到一个小娃娃却愣是让他断了弦。秦思省硬生生的落了面子,心想着怎么也得好好教育教育这猖狂的小娃娃,不然日后这一身威风还能耍给谁看。
“赫连小娃娃,你那木剑是谁给你的?”
“我爷爷。”
“来,给我看看。”
赫连寂禅猛然侧身,拧着眉头,瞪着大眼睛,撅着嘴,满脸尽是提防。
“不行!”
秦思省龇牙咧嘴,口吸凉气。
“哎呦!你这小气鬼!我用我的刀跟你换!”
“不换!”
“得!”
没有占到丝毫便宜的秦思省不甘心的躺下身子扭过脑袋,心里盘算着计策,可是一行半月,直至那京城门楼出现,秦思省也未曾能染指赫连寂禅的那柄木剑。
左手握刀右手作帘,远远的眺望着那京城城门,秦思省眨了眨眼,道:“老娄,那就是京城?”
娄烽漫一如秦思省般眯眼远眺,万般慨叹皆藏心中。自京城崛起,又陨落于此,如今老死的骨头拉马折道,不知是否能辉煌如初?
“这就是京城。”
京城,亦称文城。作为皇城,就自身地位而言,秦越二十三州无一可出其左右。
城门的巍峨是非肃州那般寻常州府城门可比肩,便是那四列三十二名身着盔甲手执长枪的守城士兵的威严阵仗,也不是肃州府衙能够到达的规格。
所谓皇城,便是皇家的颜面,马虎不得。
入得城门,宽阔的通天道直延向北,似是没有尽头。道旁商铺林立摊位众多,车水马龙比肩接踵。
比肃州府高大的城门,比肃州府宽敞的街道,比肃州府人多的街市,比肃州府风韵的可人儿......
这等繁华,让以为肃州府就是顶天的繁华的秦思省有着一种陌生却梦寐以求的向往。
秦思省从不曾想过,有朝一日踏在京城的道上是何等的心境。当梦境般的迫切归于现实,欣喜已然难以描述。
难以抗拒的魅力,油然而生的豪情壮志。人言京城之地多富贵,嗅着这充满权利的空气,秦思省不愿去想那些权利之下的血流成河。
他只知道,想了二十年的京城就在脚下,刀在手,不富贵不还乡。
侧眼看着闭眼驻足的娄烽漫,秦思省感受不到娄烽漫的情怀,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交替。
“老娄,这京城没个人情味儿啊!”
娄烽漫看着有意言之的秦思省,笑着说道:“瞧这么些个人,这般的烟火气,秦爷何出此言?”
秦思省双手撑在袖子里,佝偻着腰,摆着冬雪,咧嘴不屑。
“你这么个朝前大官,如今重返京师,那些个达官士子真就没个风声?不说殷切如何,起码也得移步到这城门相迎吧?瞧你这孤零零的一老头,莫非是世态炎凉?”
老娄笑着说道:“正如你说,我这是朝前官,如今为民。这皇城里面,虽有一抓便是大有来头,我一个老头子,如何当得起百官相迎。”
秦思省听了老娄的话一阵咧嘴。
想着萧浅在那东阳村也算是大有来头,如今不过是换了地方。虽然皇城猛人多,但是随手一抓都是大有来头,那十足的水分不浅。想那皇亲国戚轮个数也就那么些个,即便是大有来头,无非是沾亲带故的裙带关系罢了。
娄烽漫前来京城是得了皇帝的密诏,没有期限,所以此刻神不知鬼不觉的贸然抵达,对于府邸之说自然略显妄言。穿过半天通天道,便是京城驿站。娄福上前一番商讨,没多久却是被两个身着无品官服腰悬下等佩刀的衙役给轰了出来。
娄烽漫满脸委屈的说道:“老爷,这两人不让咱们进去!”
“为什么?”
娄福看了眼秦思省,道:“因为......因为咱们没有官碟。”
“官碟是什么?”
“官碟就是朝廷颁发的通用文书。”
那瘦弱衙役斜着眼对着秦思省一番打量,语气满是嘲讽的说道:“每天到驿站骗吃骗喝声称自己是朝廷命官的人没有一百也有八十,瞧你们这几位的寒酸像,估计这辈子是没那做官的命了。”
秦思省双手撑在袖子里,弯着腰咧着嘴。
“怎么着,狗眼看人低?”秦思省拧着眉头说道:“还不怕告诉你,你眼前这位爷,那可是皇上眼巴巴请来的!这年头啊!扮猪吃老虎的主儿贼多!”
“皇上请来的?”
那衙役左看右看,却怎么也看不出一脚进棺材的娄烽漫身上有哪怕丁点的富贵气。
“您这主儿是哪路神仙?”
“娄烽漫娄爷!”
“没听过。”
秦思省黑下脸来。
“新来的?”
“这京城,就是翻个地儿也找不出娄姓的爷!”
秦思省握着冬雪,嘴角贼笑。
“赫连小娃娃,那白胡子老头儿姓什么来着?”
赫连寂禅操着稚嫩的嗓音,却一脸鄙视的看着秦思省。
“爷爷姓娄!笨蛋!”
秦思省哦了一声,抬手摸着下巴满是无奈。
“纵是当年封疆万里封王碑居榜首,也敌不过这京城官爷的慧眼如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