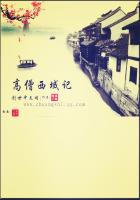翌日,江楼月让复痕带上一个脉枕,往太子殿下的寝宫崇仁殿去。进了殿门,见了赵遣鹿,江楼月道了声早。
赵遣鹿有些奇怪地看了她一眼,“早。”他随即就看见了复痕手上捧着个东西,用细绸包着,“是什么好东西?”他有点好奇地笑问。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先用早膳。”江楼月道,神情柔和,看起来倒不是在卖关子。
两人用过早膳,宫人将桌子收拾了,江楼月道:“都退下吧。”
“是,娘娘。”所有殿中伺候的人都退了下去。
江楼月取过一旁的脉枕,放在赵遣鹿面前,揭开细绸,道:“请。”
赵遣鹿看着面前的脉枕,一时没有说话,也不动作。
江楼月道:“我医术不精,只能是尽我所能罢了。”
他抬眼盯着她,目光并不锐利,却想要将她整个人都看透,看进她的眼底,一无所获。“你要给我诊脉?”赵遣鹿道。
“是,诊脉,治病。”江楼月看着他的眼睛,没有丝毫躲闪。
赵遣鹿微微笑了笑,心里却有一丝冷意浮现,“怎么现在想起来要给我治病了,不相信御医的医术么?”
“难道你不想治么?你的病,怎么可能是御医在治?”江楼月温和地道,并无半分咄咄逼人之意。
“我怎会不想治,这不一直都在治么?”赵遣鹿道。他的手不禁颤了颤,胸腔里气血翻涌,看着她的视线残忍地模糊了些。他压抑着气血的翻涌,握紧了拳头,微笑着道:“我不是不相信你的医术,只是我这病,从根儿上就是要人命的,不是说治就能治好的。”
“你在怕什么,难道人会怕活着么?”江楼月道。
赵遣鹿站了起来,背过身去,“你……不明白么?”
她没想到他竟比自己还顽固。“你让我试试,要怎么治,是我的事,让我见见给你治病的大夫,商量商量,总会有更见效的法子,且不说别的,你的眼睛还能坚持多久,你自己不知道么,到时如何批阅奏折,还如何赏南邦的大好河山?”
赵遣鹿缓缓地转过身来,她在他的眼中已成了一个虚幻的影子,耳畔似听闻了什么东西碎却一半的声音。他坐回凳上,拉了拉袖子,将右手放在了脉枕上。
江楼月沉心静气,伸手诊着他的腕脉,一脸严肃认真。
赵遣鹿目光垂着,看着她纤细白皙的指尖,眼前却禁不住的恍惚,他喜欢看她的手包扎伤口的样子。
她指腹传来似冰非冰的触感,此脉像沉浮不定,他体内气血正翻涌着。他的眼睛,如往常一般沉静有神,但此时这双眼能看清些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
如此把脉便花了一盏茶的工夫,直到他体内的状况稳定下来,手上的皮肤恢复了一惯的冰冷,她才收回了手。她仔细地看了看他的面色,开口道:“以后发病在我面前不必忍耐,反正又不是没见过,别再憋出别的问题来,我是说真的。”你别感情用事。
“好。”赵遣鹿清淡地应了一字。
“你这情形复杂,病根深久,初次病发是被毒素诱引,可惜当时毒素未能尽除,渐渐侵入脏腑。病去如抽丝,我得先好生想想如何开始。给你治病的大夫,可见是回春妙手,一定让我见见。”江楼月道。
“好。”赵遣鹿仍是淡淡地道。
江楼月重新包了桌上的脉枕,拿在手上,“我先回去了。”她开门走出去,将脉枕交给复痕捧着,离了崇仁殿。
好一会儿后,赵遣鹿才转头看着她背影离去的方向,他的眼中,像是下着一场鹅毛大雪,寒风肆虐。
江楼月回到香澈宫,坐于书案后,命复痕研了墨,然后让后者下去。她细细地将赵遣鹿的脉象与症状等写下来,一边看着一边思索,半个时辰后,写了一张方子,左右思量一番,皱了眉头,又提笔改了几处,看着觉得仍是不好,两下把方子揉作一团,扔在案上。
她手里拿着之前写的症候,边踱步边看,然后停于烛案前,又看了一回,脑中的想法似是而非。她把这两页纸点火焚了,扔在盆中。看着纸烧完,她往后园子里走,又给草药浇水去了。
复痕见江楼月去了后园子,便悄悄进了书房,瞥见书案上的纸团子,眼神动了动,上前把那方子打开,看了数遍,不敢再动他物,只得将方子背下,揉了一团放回原处,回到自己在香澈宫的下房,赶紧把方子默了一遍,干了墨迹,折起揣在了怀里,瞅着空就呈给主子。
江楼月给草药和别的花草都仔细浇了水,把水瓢放回桶中,走到檐下,坐倒在躺椅上,挪了个最舒服的姿势,闭目养神,手指时不时地轻叩着。
六月的南邦京城已是炎热,她这一通忙活,身上是一层薄汗,在这风口里歇一歇,很是舒爽。
赵遣鹿沐浴更衣,去斐嘉殿处理完今天的政务,便来了香澈宫。
复痕见了太子,行礼道:“奴婢拜见殿下。”
“起来吧,娘娘呢?”赵遣鹿道。
复痕道:“回殿下的话,娘娘在后园子里。”
赵遣鹿提步欲往,复痕掏出怀里的方子,低声道:“这是娘娘写的,在书案上揉作一团,想是不满意。”
赵遣鹿接了过去,收起并不急着看,“你去吧。”
“是,殿下。”复痕行礼自去。
江楼月睁开眼时,有点迷糊,左右看了看,想起自己是在园子旁的廊檐下,竟就这么睡着了。她低头一看,谁给自己盖的薄毯?以她的警醒,只要有声响,或是有异样的味道过近,她肯定会醒的,难道是园子里各种香气扑鼻,一时疏忽了?
此时复痕绕过殿宇近前来,“娘娘,您醒了,要现在用饭么?”
江楼月这才注意到天色已晚,这一睡怎么把午膳都给睡过去了?
“谁来过园中么?”江楼月问着,起身把毯子递给复痕。
“殿下下午来过,略坐了坐就走了,命我等别扰着娘娘。”
江楼月轻点了点头,没言语。
“娘娘,要不要摆饭?”复痕又问道。
“好,摆饭。”江楼月说着,似有点怔愣。
复痕见了她的神情,只道:“我这就去传膳。”
给赵遣鹿治病的大夫姓陈,虽不是御医,却住在御医院,居着个闲职,领微薄的俸禄,只给太子殿下一人请脉治病。太子还是吴王时,患有顽疾之事就鲜有人不知,当年病情严重,赵遣鹿不得不从大将军的位置上退下来,专心养病养了几年,才好了些,至少是不碍行动,想走便走,武功也没因此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