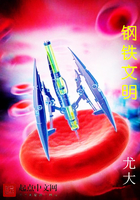兴王府平静下来后,严嵩曾试图求见朱厚熜。门岗问他有什么事,并告诉他,王府的一般事务都由管家骆安处理,不是什么重大事情,朱厚熜通常不见客。严嵩听了,怅然若失,跟管家骆安,他犯得上说吗!
为了在长寿县生存下来,严嵩在店铺给人帮过闲,到地主家打过短工,干的时间最长的是货郎,整天挑着一副货郎担,走乡串街,吆喝叫卖。就这样,时间悄然到了深秋。这时严嵩才意识到兴王府已不像以前那样热闹,他们封闭起来,成了一潭死水,如果自己不主动想办法靠近他们,他们是不会主动来找自己的。
当时的文人,读的基本都是四书五经之类,其中《周易》是学人的必修课。严嵩才高八斗,腹藏珠玑,对《周易》自然颇有究习。他思之再三,决定到兴王府附近摆一个卦摊,表面上给人看相算命,代写书信赚钱度日,实际上是监视兴王府,寻找接近朱厚熜的机会。他在心里说:如果老天爷不给自己机会,那是自己的命。如果老天爷给了自己机会,自己一定不负平生所学,让朱厚熜对自己高度重视,难以弃舍!
也是严嵩劫数未尽,该有一场伤痛之灾。这天,卦摊前来了两个凄凄凉凉的男女,一看就是那种老实巴交的穷苦人。他们来到这里,是求严嵩帮他们写一张状子。通过他们的叙述,严嵩大致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是一对父女,姓邓,家里有几亩稻田。他们生活的村子叫边家村,村里有个恶霸地主,人称边百万。边百万霸占了村里的大部分土地,对邓家的几亩稻田也志在必得。然而,这几亩稻田是邓家赖以为生的命根子,他们说什么也不放手。边百万就霸占了四周所有的土地,把邓家的几亩稻田围在中间,然后邓家人从他们的田埂上走过,边百万就要收取高昂的过路费,这实际上是逼迫邓家放弃那几亩稻田。邓家无处说理,不得已只好出此下策,寄希望官府能还他们一个公道。
严嵩是农民的孩子,对地主恶霸的凶残本性了如指掌,也深恶痛绝。他非常同情邓家父女,就业务为他们写了一张状子,让他们到县衙去告状。
没过几天,几个阴阳怪气的流子斜鼻子歪眼睛,吊儿郎当地向卦摊走来。老于世故的严嵩一看,就知道来者不善。但他自问在这里与人无怨无仇,街上的地痞流氓讹诈也不会讹诈到一个看相算命者的头上来吧!所以,他充满疑惑,强作镇定,问:“几位大哥,是想看相算命,还是想抽签问卦?”
流子头道:“我们想请你算一算,今天是个什么日子?”
严嵩:“今天是个什么日子,那要看你问的是什么事了。”
流子头:“杀人!你帮老子算一算,今天老子杀人,吉不吉利!”
严嵩:“杀人?杀什么人?”
流子头:“杀你,杀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严嵩:“大哥你说笑了,我与你素不相识,你莫名其妙的杀我干什么。”
流子头:“邓大清的状子是你帮他写的吧?”
严嵩如坠云雾:“邓大清?哪个邓大清?什么状子?”
流子头:“你******还跟老子装糊涂!邓大清告边大地主的状子不是你帮他写的?”
严嵩猛然醒悟:“你是说那一对父女呀?那是他们找我写的,我一个卖字混饭吃的,只是帮人代笔,没有跟边大地主过不去的意思。”
流子头:“怎么,害怕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说着,一脚踢翻了卦摊,几个流子一拥而上,把严嵩打的双手抱头,满地乱滚,直到高喊救命,他们才扬长而去。
严嵩的心在流血。这是一个混沌世界,是一个正气萎缩,邪气横行的社会。严嵩被几个流子殴打时,街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站出来制止,没有一个肯为他这个形似乞丐的外乡人,去得罪当地的恶霸地主。问苍天:人性为何物?为什么自己仗义为人写状子,得到的却是这种非人的报复?这世界还有救吗?泯灭的人性,还能复苏吗?
严嵩在自己狗窝似的草棚里结结实实地睡了几天。他流干了眼泪,也流碎了一颗伤残的心。他想起了远在江西老家的妻儿,他们是否安好?自己本打算进了兴王府后再跟他们联系,免得他们时时为自己担心,可这个梦想何时才能实现?他想起了自己半生努力,满腹经伦,到头来却落到了这步田地,连做一件善事都会受到非人的报复,自己对生活还敢抱有希望吗?
时间滑进了正德十六年(1521)的门槛。春节很快过去了。
这是一个倒春寒天气。鹅毛大雪从头天下午一直下到第二天早上才停。皑皑大雪掩盖了一切,层峦叠嶂的群山远远望去,就像波澜壮阔的惊涛骇浪,让世界充满了诗意。严嵩拉开草棚那扇形同虚设的破门,瑟缩着来到街上,在老地方支起了他的卦摊,然后孤独地坐在那里,对着兴王府的大门发呆。突然一声响亮,王府的朱漆大门拉开了,从里面鱼贯而出八九个少男少女,喜鹊一样在雪地里叽叽喳喳。其中有个少年衣着服饰特别华丽显眼,被几个少男少女众星捧月般地簇拥着。他们在那个少年的指挥下分作两班,然后打起了雪仗,五彩缤纷的身影,在雪地里形成了一道别致的风景。被寒冷冻得缩成一团的严嵩,霎时热血沸腾。他料定那个衣着华丽的少年必是兴王世子朱厚璁。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老天爷终于开眼,将机会送到自己的面前来了。
少男少女们玩兴很高,四散开来,雪团在他们的头上流星般地飞来飞去,伴和着他们的欢声笑语,给人很强的感染力。他们离王府大门越来越远,离严嵩越来越近。就在他们激战的不可开交时,一声吆喝很不协调的灌进了他们的耳朵:“算命喽,看相算命喽。几位公子小姐们有愿意看相算命的吗?不要钱的,免费给你们看相算命。从你们的面相上,我就能知道你们的未来前程,吉凶祸福,并能帮你们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少男少女们相继停了下来,朱厚熜惊异的四处张望,寻找这声不协调的吆喝从何而来。一个婢女看见严嵩,对朱厚熜说:“是个看相算命的,没什么稀奇,我们还是接着玩吧。”
朱厚熜不满十五岁,平时深锁王府,有时偶尔出来,也必然有人带着,前呼后拥一大帮,哪里见到过什么算命先生。但他从书上得知,看相算命甚为神奇,现在遇到一个看相算命的,不觉动了好奇之心。他扔下手里的雪团,带头向严嵩走来。
管家骆安生怕几个少男少女玩出事,一直站在大门口盯着他们。见朱厚熜等人停止打雪仗一起向严嵩走去,吓了一跳。因为世道混乱,要是被歹人挟持,那还了得!所以,他一边向前狂奔,一边大喊:“世子,你要干什么去?”
朱厚熜不理骆安,径直走到严嵩的面前,说:“先生,你给我算个命吧。”
严嵩说:“算命暂且推后,还是先看个相吧。”
朱厚熜正欲说什么,骆安赶上前来,一下用身体护住了他,说:“世子,江湖骗子的话听他干什么,我们还是回去吧。”
朱厚熜受一种好奇心地驱使,一推骆安,不高兴地说:“骆安,我要干的事,用得着你管么!”
严嵩煞有介事地端详着朱厚璁,说:“世子天庭饱满,面如满月,前途不可限量……”说到这里,严嵩有意用眼睛环视左右,显得更加神秘:“世子,这里不是说话之处。当众说破,恐泄露天机。”
骆安见严嵩装腔作势,根本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忍无可忍,怒喝道:“大胆狂徒,世子面前竟敢装神弄鬼,当心我砸烂你的狗头……”
朱厚璁被严嵩说得心痒难捺,见骆安一再怒斥严嵩,败坏自己的兴致,也真火了。他冲骆安吼道:“你给我住口,再敢无礼,当心我先砸烂你的狗头。”说完又转向严嵩,诚恳地:“先生,你看哪里是说话之处呢,到我王府怎么样?”
严嵩心里暗喜,脸上却平静如常:“如此最好,到时我一定把世子的命运,好好地解析出来。”
严嵩被朱厚璁带到兴王府,先在客厅呆着,而后又被带到后厅,面见蒋王妃。话不过三句,蒋王妃就直奔主题:“先生,听世子说你是先皇钦定的进士,应天府翰林院侍讲,知天文晓地理,能知人前程,料知未来,可是真的?”在得到了严嵩的肯定答复后,又让严嵩测了几个字,还排了朱厚璁的生辰八字。严嵩有备而来,不管蒋王妃报什么字,他都会说的如何如何高贵,如何如何玄妙,把蒋王妃听的一惊一乍,似乎朱厚璁每走一步都处在十字路口,每走一步,都是刀山火海,如果没有高人指点,稍不慎就会死无葬身之地一样。
蒋王妃是个女人,一个没有男人的女人,在很多时候是没有主见的,这时她在心理上就已经被严嵩降服了,言谈之中就少不得要问他为何落到这个地步。严嵩便从头至尾,把事情的经过声泪俱下地说了一遍,最后道:“草民因久闻兴王爷贤德之名,故弃官挂职千里来投,谁知王爷他……”说到这里,严嵩心酸地擦了一把泪水:“小民也就落到了这种地步。”
蒋王妃不知严嵩说的是真是假,但严嵩那么大一个男人,一把鼻子一把眼泪,倒也让人感动。她说:“王爷生前的确惜才,王府也有许多幕宾,只是今非昔比,先生来的不是时候啊。你千里来投兴王府,这份诚意我替地下的王爷心领了。敢问先生,以后有什么打算?如果准备回去,王府可资助你盘缠,让你一路再不受风霜之苦了。”
严嵩垂头不语。
蒋王妃见严嵩不语,便又说:“先生既然是先皇钦定的进士,应天府翰林院侍讲,腹中必有八斗之才。如果先生不准备回去,愿意留在兴王府的话,我今天就破例把你留在府中,闲时陪世子读书,急时帮王府排忧解难,我们得便再帮你弄个小小的前程,不知你意下如何。”
严嵩盼的就是这一天,听了蒋王妃的话,喜出望外,连忙起身一揖,说:“多谢王妃。严嵩能为王府出力,肝胆涂地,在所不惜。前程之事,愧不敢当。”
蒋王妃一本正经:“王爷生前爱才,也嫉恶如仇,对世子管教极严。你若教导世子学好,使之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王府自然不会亏待你。若怂恿世子声色犬马,我既能留下你,也能赶走你,甚至杀了你!”
严嵩一凛,又作揖:“王妃放心,严嵩若不尽心竭力,天劈五雷轰。”
正德十六年(1521)年3月的一天,弃官挂职的严嵩漂泊在安陆府,饱受了辛酸后终于进了兴王府。在蒋王妃的吩咐下,管家骆安很不情愿地派了两个府兵,将严嵩简单的行李搬进了王府。在离开那个狗窝的草棚时,严嵩心里一酸,忍不住流下了说不清道不明原因的泪水。他更不知道,一场改良社会的序幕,以此为分水线,已经悄悄拉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