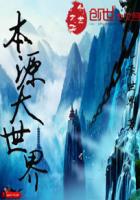这彪凉军头领不是李弘还是谁人!周统知是凉军援兵已至,不再与樊越苦战,要是因为樊越这莽夫而误了大事,那么他周统可是吃罪不起的。
李弘驻马高呼道:“周将军,你们夏军可真够狠心啊!那可是三十万人啊!你们居然如此草菅人命!”
周统恨声道:“李弘,你别给说这些没用的,你们凉国是自作孽,不可活!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来多少人,我们就杀多少人!”
李弘摇头惋叹,大手一挥,数万凉军朝天怒吼,挥舞着兵刃呼啸而来,声势如虹。
周统心知今日难免一战,利刃一挥,数万夏军儿郎纷纷云集景从,矛光剑影,虎扑上前。
双方近十万将士持刃火拼,血光大现,整个一线天要塞充满了呼喊声、哀嚎声和痛苦的呻吟声。
“李将军,俺老樊没力气了,你先顶着。”
樊越以一己之力斩杀了近十名夏将和上百名夏兵,体力和真气早已将尽,趁乱夺了一员夏将的战马,斩杀掉数名夏兵之后仓皇逃离要塞,投一线天关口而去。
周统与李弘双方走马盘桓,你来我往,打了百余合竟不分胜负。
周统心道越拖下去对自己就有利,因为陈穆的数万大军正在向要塞赶来,他只要再拖住李弘一刻,李弘这几万兵马定能被他吃掉。于是周统只与李弘且战且退,故意拖延时间。
李弘也是久经沙场的宿将,只打了片刻,便知晓周统的意图,一剑挡过之后,李弘退回到一群凉军中,呼道:“留下五千精兵,全军后撤!”
军令如山,在严厉的军法之下,凉军如退潮的潮水一般缓缓撤出要塞,周统见自己的计划被李弘识破,当即下令全军追赶掩杀,不料大军追至要塞西侧城门时却被残垣断壁下的数千凉军死死阻挡,竟一时被堵在了门口。
此时火势已停,焦尸碳石随处可见,不少未死尚在痛苦呻吟的凉军士卒皆被精悍的夏兵补上致命的一刀,草草结束了他们的生命。
周统扯着嗓子指挥夏军,终于将西城门攻破,五千殿后的凉军无一人生还,全部战死。周统再寻李弘残部,早就不知所踪,只剩下西方的漫天飞舞的黄沙。
周统垂头暗叹,李弘不愧是凉国名将,关键时刻居然敢壮士断腕,自己还是未留下李弘啊!
乌云笼罩,天色阴沉,忽而已下起朵朵白雪,大地再次被银装素裹,火势完全熄灭,只留下数不尽战死的壮士。
待陈穆率后军赶到,打扫战场完毕,夏军虽占据火攻优势却仍损失了近三万人。十三万夏军锐减到十万余。
再观凉军,待李弘逃回一线天关口,收拢散兵逃卒,竟也得了十万余,再加上原本一线天关口拥有的十万新兵,一共加起来尚有二十万人。董馥醒后,大悔未听辛评之话,不过并未对李弘的后策指挥多加赞赏,董馥得知损失二十万大军之后,一片颓然之色,似乎整个人一下子老了十几岁。
辛评虽也有叹息,不过这一切却在他的意料之中,所以并没有同董馥一样黯然神伤。碎步上前参道:“事已至此,大王应立即发兵再攻一线天要塞,夏军烧了要塞,无凭无借,我军此刻一股作气,定能再克一线天要塞!大破夏军!”
董馥哪里还有半点主见,连连点头应允。
不料,李弘刚点齐十万兵马,还未冲锋,却听得前面巨响,派斥侯察探一番回报,原来是夏军旧戏重演,又砸断山壁,阻断了凉军攻打一线天要塞的道路。
辛评得知,摇头苦笑:“陈穆用兵果然神速,竟丝毫不与别人喘气之机会!此人不除,夏国不灭啊!”
是以,凉军只得一面派兵清理阻挡在峡谷的山石,一面养精蓄锐,训练新兵。董馥又派武尉窦元回都城远京城催粮,辛评与李弘整日商议对策。
就这样,夏军与凉军隔“山”对呼,却老死不相往来。
可未过几日,夏国朝廷下诏令陈穆回都叙职,陈穆只道老夏王姬华病危有急事与他相商,见此时要塞也无战事,想要再开战也得数月之后,于是陈穆便找周统等军中将军、副将、偏将前来商议对策。
※※※
一缕柔和的晨曦透过檀木窗投到一座宅院中,满地银雪闪烁着金色的光芒。院子里的百年古树擎着一个脸盆大的燕巢,几只留在北方过冬的燕子叽叽喳喳清脆地叫着,好一派生命景象。
“呃……我……我……我这是在哪里?”陈玄感缓缓睁开双眼,许久未见到阳光的杏目不由得感到刺痛,适应之后却见眼前有一位身穿白衣的女子端着青瓷碗走了进来。
陈玄感欲起身,却觉浑身疼痛,接着又躺倒在床。
白衣女子忙将手中青瓷碗放到檀木桌案,上前扶住陈玄感,两条细长的柳眉紧蹙,嗔道:“你的伤还没好呢!怎么就起来了,赶快躺好。”
陈玄感昂首问道:“我怎么在这里?”
白衣女子转身将青瓷碗从桌案端过,坐在一旁的木凳上,道:“前几天我和爹爹从锦官城回安阳城的路上见到你浑身是血埋在雪里,我于心不忍,所以命人将你从雪中挖出来,见你还有口气,所以将你安置在家中休养。你伤还没好,就不要动了。”
“我躺了多久了?”
“四天吧。”
“什么?四天!啊……”陈玄感张口惊呼,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不料却站立不稳,重重摔在地上,全身的伤口猛然崩裂。
白衣女子急忙上前扶起陈玄感,娇声责备道:“我都说过了,你的伤还没好。”
“可是……”
“可是什么!”白衣女子将陈玄感扶到床上躺下,“你的腿受了冻疮,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不下十处,又失血过多,我真觉得奇怪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陈玄感深吸口气,如今姬广篡位,下一步肯定就是要对付手握重兵的父亲陈穆。可现今他身负重伤,动弹不得,又怎么回一线天要塞禀报?若不及时告知父亲,父亲必然遭其所害!怎么办?该怎么办?
陈玄感望着白衣女子,道:“多谢姑娘相救,但我要事在身,希望姑娘能助我一臂之力。”
白衣女子欣慰的露出一丝微笑,闭月羞花般的容貌和妙曼的身姿使陈玄感不禁失神,白衣女子点头说道:“公子请说,只要小女子能办到的必然相助。”
陈玄感用力撕下一条衣襟,咬破食指,血书而下:“贼子篡位,滥杀无辜,屯兵要塞,谨慎当心!儿,陈玄感。”写完又对白衣女子道:“劳烦姑娘让人快马赶至一线天要塞,把这封血书交由定国侯陈穆。”
白衣女子聪明伶俐,不多问,收起血书,道:“我这便让下人将这封信送走,这碗汤你可得喝了,是我好不容易熬的。”
待白衣女子走后,陈玄感躺在床上,感受着体无完肤的身躯,姬广篡位,必然会加害陈家,已经过了四天了,也不知道现在通知父亲还来不来得及,娘亲和陈诩还在锦官城,可他们却不知宫内情形,想到这里陈玄感再也不敢想下去,心中默默祈祷他们平安无事。
却说黄成,自从得杨易叮嘱后便暗中保护陈玄感一直到锦官城,直到陈玄感和周九龄等人进了王宫才在王宫外面守候,不料等了一整夜也没有见到陈玄感和周九龄等人出来,黄成心中不免大急,到了四更天摸进王宫一打听才得知昨晚宫廷大乱,老夏王驾崩,公子广继承王位,王世子姬文造反被平,四处追杀逆臣,平时与姬文交好的大臣全部下狱,而陈玄感是唯一漏网的逆臣。
论打仗统兵黄成可能不及杨易,可论细心却是远超杨易。
黄成笃定,姬广那小子肯定是弑父杀兄篡得了王位,将军等人发现了他的罪行,他小子就想杀人灭口。
现今将军人已经跑了,那么以姬广那小子的性格必定会迁怒于陈家。黄成想罢,趁天未亮,飞奔至定国侯府,见到陈玄感的母亲沈氏和陈诩,将自己身份和王宫发生的一切悉数告知。
陈诩和沈氏听罢皆深信不疑,陈诩蹙眉道:“全府上上下下几百口,要想全部撤离肯定会被姬广发现,只能带走一部分人。”
定国侯府的好多下人都在陈家伺候了十数年,要让沈氏弃他们而去,沈氏终究于心不忍。
沈氏询问道:“子言先生,能否带上这些下人?”
陈诩知沈氏心中所想,摇头道:“不可,在下也知老夫人是不忍抛下这些下人,但大难临头也不能管他们了,待我们走之后可多给些银子散给他们逃命便是。”
沈氏叹道:“也只好如此了。”
接禁军中郎将许武之令,城门早已戒严,准进不准出。是以,黄成带着陈诩等数人从他事先挖好的狗洞逃出。
待到了城郊,黄成辨别方向,指向西方,道:“子言先生,你且带着老夫人去一线天要塞投侯爷去。”
陈诩问道:“公然意欲何为?”
黄成字公然,故陈诩称之曰“公然”。
黄成沉声道:“成保护将军不力,还将去寻。”
陈诩又问:“去何处寻之?”
黄成一时语塞,随即道:“将军肯定不在锦官城,但也离此不远,我到附近城镇挨处寻他。”
“哎呀!你们快看,这里有血啊!”沈氏捂口尖叫。
一片片红猩猩的血液已经凝结成血冰,在雪地的映衬下显得十分明显和诡异,在雪地的周围还有些许的印记和一只银靴。
陈诩疾步上前,蹲身用手捡起一块血冰,若有所思,又拿过银靴,目视片刻,良久,陈诩眼中闪过一道精光:“这血是谁的我不知道,但这靴子肯定是将军的!”
沈氏立时眼中涌出玉泪,惊呼道:“为什么感儿的靴子在这里?既然靴子在这里,那么这血肯定就是感儿的血!莫非感儿已经……”
陈诩忙道:“老夫人,您先别着急,您看这边还有车轮印,将军肯定是被人救了,而且还不是被一般人家救的。”
黄成向车轮印记望去,自言自语道:“那么将军是往北而去了?往北是安阳郡,也就是说将军在安阳郡!”
陈诩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道:“安阳郡如此大,我们就先去安阳城看看再说!至于侯爷那边……”
“我去一线天禀报侯爷!”老管家孙伯自告奋勇道。
陈诩笑道:“如此甚好!老管家可得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孙伯笑道:“别看你孙伯老,可身子骨还硬朗哩!”
话毕,几人分作两路,陈诩、黄成和沈氏等十数名门客投安阳城而去,而孙伯则领着两三名门客去了一线天要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