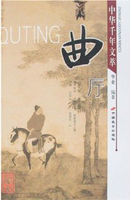“Andourlifeexemptfrompublichaunt,
Findstonguesintrees,booksintherunningbrooks,
Sermonsinstones,andgoodineverything.”
——Shakespeare
我们的生活
可以远离尘嚣
森林中有树木窃窃私语,
流淌不息的小溪似万卷书籍。
神的教诲寓于路旁之石,
世界万物皆蕴涵着启迪。
——莎士比亚
此刻富士山的黎明想
请有情趣之人看看此刻富士的黎明。
清晨六时许,站立逗子海滨放眼眺望,呈现在你眼前的是相模湾海面升起的茫茫雾霭,沿着水平面可看见海湾尽头泛出的淡蓝色。若不是望见耸立海湾北端同样蓝色的富士山,你或许便不知足柄、箱根、伊豆的连绵群山正藏隐在那一抹蓝色中呢。
海在沉睡。山在沉睡。
唯有一抹蔷薇色的光,在离富士山巅仅一箭之遥处逶迤缭绕。
忍着严寒,再驻足眺望片刻吧。你会看见那蔷薇色的光一秒、一秒地沿着山峰往下爬行。一丈,五尺,三尺,一尺,乃至一寸。
富士山从睡梦中醒来了。
她现在醒来了。看看吧,山巅东边的一角染上的蔷薇红。请定睛凝望吧,富士山峰的红霞眼看着将拂晓的灰暗驱散。一分钟,两分钟,由肩到胸。看吧,那耸立天际的珊瑚般的富士,那桃红溢香的雪白的肌肤。山,晶莹剔透起来了。
富士山在薄红中醒来了。请往下移动你的视线吧。红霞已罩在了最北的山头上,转眼间便转到了足柄山,又朝向了箱根山。看吧,黎明驱走黑暗的脚步是如此的神速,蓝色被红霞逐出,伊豆的群山已被染成一片桃红。
当黎明红色的脚步越过伊豆山脉南端的天城山时,请往富士山麓移动你的视线吧。江之岛一带紫气缭绕,忽有两三点金帆熠熠闪烁。
大海也醒来了。
倘若你仍无倦意地伫立此地,就请看看江之岛对面的腰越岬赫然苏醒的模样吧。接下来便是小坪岬苏醒的模样。假如再多驻足片刻,面前映出自己颀长的身影时,相模湾的水雾也已渐渐散去,海光一碧,宛如明镜。此时,放眼望去,群山已褪去红妆,苍穹泛出鹅黄,再变为淡蓝,白雪素裹的富士则高耸晴空。
啊,想请有情趣之人看的正是此刻富士的黎明。
大河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此言一语道破了人们对河川的情感,诗人们纵有千言万语,终不及孔夫子之此言矣。
大海固然浩瀚无垠,风平浪静时,便有如同慈母般的胸怀;生气时,又如同上帝勃然大怒。然而,所谓“大江日夜奔流不息”之气势与寓意,却又是大海所不具备的。
伫立大河之畔,看那泱泱河水默默地、静静地流淌、流淌、流淌,生生不息。“逝者如斯夫!”时间的流逝,便有如这河水般从亿万年的远古流向亿万年的未来。啊,看见白帆了……从眼前穿过了……漂向远方了……不见踪影了。古罗马帝国不是如此这般逝去的吗?啊,竹叶漂过来了,倏忽一闪,便又消失了。亚历山大、拿破仑莫不如此。他们今在何方呢?浩荡不息的唯有这大河之水。
与身在海滨相比,伫立大河之畔,更能让人感受“永恒”二字的含义。
利根川秋晓
某年秋十一月初旬,投宿于利根川左岸一个叫“息栖”之地。这里是利根川干流与北利根北浦下游交汇之地,河面宽绰,距对面的小见川约有一里之遥。客栈紧临河岸,夜半醒来,耳边不时传来阵阵“嘎吱、嘎吱”的橹桨声。
黎明起身,见店中客人尚在睡眠中,便轻轻推开木门,走到河畔。岸边堆着柴火,抖抖覆在上面的一层霜,坐了下来。天色朦胧,天空与河面尚未苏醒,一片铅色。身后昏暗的鸡舍里,雄鸡开始鸣唱报晓。片刻,对面小见川方向也隐约传来报晓声。隔着河岸,鸡鸣声此起彼伏,也着实令人心悦。切尔西的先贤与康考德的哲人想来也是如此这般隔着大西洋相互呼应的吧。
原来,在我看来,黎明正是从两岸的鸡鸣声中涌上河面来的。不一会儿,小见川方向的天空被染上了一层蔷薇红;再细看,河面上也泛起了淡红的涟漪,开始有水雾蒸腾。太快了!一眨眼工夫,夜色流向了下游,曙光洒满河面,鸡鸣声不绝于耳。水天一抹的蔷薇色开始消退,瞬间,闪烁刺眼的光芒便在水面流动。回首望去,杲杲旭日正从“息栖神宫”的树梢上冉冉升起。此时,一只乌鸦飞离枝梢,宛如背负朝日,在晨曦中飞翔报晓的神使一般向小见川方向飞去。小见川还依旧酣睡在碧蓝的朝雾中。
对岸尚在沉睡,这边的小村庄已经苏醒。身后的茅屋冒起袅袅炊烟,冲出栅栏的鸭子把脚印烙在霜地里,“嘎、嘎”的叫声划破晨曦的静谧,一路直奔水中。岸边的柳树上,小鸟婉转啼鸣。陆陆续续起床的村民们嘴里吐着白气,走向河滩,掬河水洗漱。其后,便面朝筑波圣山方向合掌遥拜。
此处真是一个膜拜的好殿堂啊!
上州的山
织机的声音,缫丝的烟雾,桑树的海洋。近可见高耸的赤城、榛名、妙义、碓冰群峰,远有浅见、甲斐、秩父山脉、日光、足尾山峰,以及越后一带的连绵群山。要么奇峭,要么雄伟,扎根大地,头顶苍穹,伟岸挺拔。行走在一望无垠的桑田道上,不经意间,放眼望去,这些层峦叠嶂总是泰然屹立着。
在日常忙碌琐碎的平凡中,心胸却能超然拔萃,仰视长空的伟人们不也如此吗?
每每来上州,总感到连绵群峰在向我如此细语。
空山流水
某年秋,十月末,我来到盐原帚川的支流鹿股川,坐在河畔的石头上。前日夜晚,强劲的秋风将红叶刮落殆尽,河面铺上了一层红彤彤的树叶。左右两侧高耸的峰峦直达天际,夹在其间的天空仿佛也似河川在流动。深秋时节,河水消瘦而干涸,在河面的乱石间流淌,顺地势蜿蜒穿行于峰峦深谷中,远远地可望见水流的尽头。在尽头处,恰有一高峰当河而立,挡住河水去路。远远望去,似乎河水会被此峰吞吸进去一般,又好似此山想要拥抱住河水,挽留她一般。“留下吧,离开故里有什么好呢?留下吧,留下吧。”然而,河水仍旧在河底的乱石间,在红叶覆盖的水面下唱着歌顺流而下。坐在石头上,侧耳倾听。这声音,是松风,还是无人弹奏而自鸣的琴音?怎么比喻才好呢?身在石头上,心却追逐着水流的尽头,远去、远去、远去。——啊,又依稀听见了这声音。
时至今日,夜半从睡梦中醒来,心灵澄净时刻,仿佛都会从远方传来那声音。
大海日出
涛声划破梦境,起身推开房门。此时正值明治二十九年(1896)十一月四日拂晓,我投宿在铫子市的水明楼,楼的正下方便是浩瀚的太平洋。
凌晨四时许,海面尚在一片朦胧中,只有涛声高亢。遥望东方,沿着水平线已泛出微暗的红黄色,灰蓝色的天空上挂着一弯金弓般的残月。月光皎洁清澈,仿佛在镇守着东瀛。左侧有伸出海面的黑黝黝的犬吠岬,岬顶灯塔上旋转的灯光,从海滩向海面不断地扫过一轮轮白色的光环。
过了片刻,冷飕飕的晓风刮来,掠过青黑色的海面,夜幕由东方开始揭开。黎明踏着鱼肚白的波涛涌了过来,浪涛拍打黑色礁石的白沫渐渐清晰可见了。仰目望去,那一弯金弓已变成银弓,方才东边灰暗的朦胧也渐渐清澈泛黄。海面汹涌,黑波白浪翻滚。夜的梦境尚在海上徘徊,东方的晨曦却已张开眼帘,太平洋的夜已经明了。
此时,黎明的曙光如花蕾绽放,一轮一轮在空中、在海面扩散开来。海浪渐渐泛白,东边天空的黄色更加浓厚,月色与灯光慢慢退去了光芒,消逝了身影。一行候鸟如太阳的使者,掠过海面,飞翔而去。万顷波涛企望东方,发出蓄势待发的喧哗——无形之声充溢四方。
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眼看着东方光芒四射,忽然,猩红的一点浮出了海面。哎呀呀!太阳出来了!一瞬间,令人来不及细想。屏息凝视,刹那间,海神高擎起手臂,只见浮出海面的红点化作金线、金梳、金蹄。随后,身躯一摇,毫无留恋地跳出了海面。那一刻,万斛金光从冉冉升起的朝阳中喷洒而出,万里洋面犹如金蛇飞舞,眼前矶岸边顿时卷起两丈高的金色雪浪。
相模湾落日
秋冬的风完全停息了,黄昏的天空一尘不染。伫立眺望伊豆山的落日,令人遐想到世上竟还有如此多的和平景象。
落日从沉下山头到隐没身姿需要三分钟光景。
太阳西斜时,富士、相豆一带的群山如轻烟薄雾。此时的太阳,为名副其实的白日,银光灿烂,令人炫目,连山脉都眯起了眼睛。
太阳再西斜时,富士、相豆一带的群山开始染上紫色。
太阳更加西斜时,富士、相豆一带的群山紫色肌肤上披上了一层金色的轻烟。
此刻,站在海边眺望,落日流过海面,到达我的足下,海上船只皆闪着金光。逗子海滨一带无论山峦,还是沙滩、房屋、松树、行人,以及翻滚的鱼笼,散落的稻草屑,无不泛出火红色。
在如此风平浪静的黄昏,观看日落,真有伺守圣贤临终之感。庄严之极,平和之至,连凡夫俗子也如同被灵光笼罩,肉体融化,唯灵魂端然伫立于永恒的海滨。
有感,融然浸润于心,言喜则过之,言悲则不及。
落日西沉,眼见着快要落到伊豆的山上,相豆群山忽而便被染成深蓝,唯有富士山顶依旧于紫色中泛着金光。
伊豆山已拥抱住落日。太阳每西沉一分,印在海面的光影便退却一里。夕阳从容不迫地一寸一寸、一分一分,顾望着行将别离的世界,悠悠然西沉而去。
只剩下一分了。太阳突然下沉,只留下一道柳眉,眉又变成线,线缩成了点——太阳消失了踪影。
举目仰望,这世界没有了太阳。光明消失,高山大海苍然失色,充满忧戚。
落日走了,然仍有余光如万箭齐发般光芒四射,西边的天空像金色,更似黄色,或许伟人辞世的模样便如此吧。
日落殆尽后,富士山暮色苍茫。片刻,西边的金色变成朱红、红黄,再转为灰蓝。如同是太阳留下的纪念物一般,金星开始在相模湾上空闪烁,仿佛是在承诺明日的日出。
杂木林
东京西郊至多摩川一带,有几处丘陵和山谷,几条道路顺山谷而下,沿丘陵而上,曲折蜿蜒。山谷中有的地方开辟出了水田,有小河流过,河上偶尔也可见水车。山坡大多被开垦成了旱田,四周留下了一片片杂木林。
我尤爱这一片杂木林。
林中有枹、栎、榛、栗、栌等多种树木。大树较罕见,大多是砍伐后的树桩上簇生的幼树,树下的草地被修整得干干净净。偶有红松、黑松等树种,秀枝挺拔,掩映碧空。
降霜后收获萝卜的时节,一林黄叶似锦,令人不慕枫叶红。
待树叶落尽,寒林中,千枝万梢,簇簇刺破寒空,好一番别致景象!日落后,大地雾气弥漫,空中的枝梢紫气环绕,月满如盘,更有一番风景!
春天来临后,淡褐、淡绿、淡红、淡紫、嫩黄,林中竞相长出了柔嫩的新芽。此情此景,又何必独醉于樱花呢?
新绿时节,不妨来林中走走吧。片片枝叶沐浴着阳光,如同绿玉、碧玉在头顶编织的翠盖,连面孔也染成青碧色了。假如在此假寐片刻,或许那梦境也是绿色的吧。
青乳菇长出的初秋时节,林子四周的胡枝子和狗尾巴草开始抽穗,女郎花和萱草遍生林中,大自然在此地营建了一座百草园。
有月亦好,无月亦好,风清露冷之夜,来林边走走吧。有松虫、铃虫、纺织娘、蟋蟀等百虫的唧唧声似细雨声传入耳畔,大自然宛如一只大虫笼,奇妙之极矣!
檐沟
雨后,庭院落樱如雪,也有片片点点漂浮檐沟中。
莫言檐水太浅,不曾见它拥碧空入怀吗?也莫言檐沟太小,不曾见它映照蓝天,漂浮点点落花吗?
樱花枝梢倒映水中,水底露出泥土的色彩。三只白鸡走过来了,红冠摇晃,俯身啄食,仰面饮水,身影映在檐水里,好不和谐相容,怡然共生!
相形之下,人类生活的世界又是何等的狭隘!
春的悲哀
漫步田野,仰望迷蒙天空,嗅闻花草清香,倾听流水歌唱。春风暖暖,拂面吹来,顿时,心中涌起阵阵难舍之情。想要捕捉它,它却身影荡然。
我之魂灵不由得思慕起那远在天国般的故土来。
大自然的春天犹如慈母。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在自然的怀抱中哀叹短暂人生,憧憬无限永恒。就如同在慈母怀中,矫情地倾诉悲哀。
自然之声
(一)高根山风雨
今年五月中旬,我登上屹立在伊香保西边的高根山,在峰顶席草而坐。
前面,一条大沟壑张着巨嘴。隔着沟壑,左侧耸立着榛名富士,右侧则有乌帽子岳矗立。榛名湖水如一幅窄长的白绸带散落二峰之间。湖对面有扫部岳、鬓栉岳等,山脚浅水环绕。乌帽子岳的右边是与信越交界的群山,身披银雪,如波涛横亘天际。
近处的峰峦,肌肤呈紫褐色。其中,巍然屹立于大沟壑旁的乌帽子岳,山头由峭立的岩石构成,山肌历经风霜雨雪,形成条条襞沟。
适值五月中旬,春,已来到了山里。山的肌肤上,襞沟处长出了枹树一类的树木,叶绿葱葱,犹如数条青龙蜿蜒爬行而下。又如绿色瀑布从榛名富士山麓落下,汇成绿色水流,一路向右飞奔涌入大沟壑,在壑底卷起几座小山,掀起绿色余波。
午后二时许,空气凝重而闷热。西边的天空露出古铜色,满目青山悄然无声,吓人的沉寂笼罩着山谷。
坐了片刻,见乌帽子岳上空乌云翻卷,如同泼墨。远处传来的殷殷雷鸣,似暴雨袭来前的鼓声。空气顿时沉滞,满目山色黯然忧戚。
忽然,一阵冷风袭来,湖水声、雨声、满山树枝摇撼声,回响山谷,弥漫天地,如山岳欲与风雨搏击的呐喊助威。
仰望上空,乌帽子岳以西的山峦已被朦胧灰蓝遮蔽,风枪雨弹,激战正酣。然而,边界的群山依然雪光灿灿,倚天而立,岿然不动。
前锋、二军、中军、殿军,布阵排列二十余里,仿佛在等待风雨的来袭,不禁令人联想起英军在滑铁卢的布阵,沉郁而悲壮。跌宕不羁的大自然之肃然威力让人刻骨铭心。
一株古老的枹树临沟而生,有枭鸟歇于树梢,鸣声不绝。
片刻,雷鸣声涌起,乌云低沉,在头顶盘旋,狂风撼动山壑,豆大的雨滴一点、二点、万千点,噼里啪啦地洒落下来。
我冲出风雨雷电的重围,朝着山口的茶舍飞奔而去。
(二)碓冰峰谷溪流声
欲寻觅碓冰峰秋景,某年秋日,我独自从轻井泽出发,沿古道而行。距碓冰峰顶约半里地处,红叶已零落殆尽,寒山枯叶间青松几点,萧瑟风景,如诗如画。
顺古道而下,满山芒草枯瘦,秋老矣,山苍矣。此刻,浅间山方向俄而乌云密集,山麓虽日影照耀,山上晚秋小雨却点点落到帽子上。“秋雨潇潇下,独行萱草山”,我吟唱着俳句前行。秋雨一阵又一阵,遍山芒草沙沙作响,如闻人语。举伞驻足片刻,阵雨戛然停歇。山中雨后的静寂,无以比拟。所谓“山中人自正”,此刻,我之(唐)孟郊《游终南山》中诗句:“山中人自正,路险心亦平。”心灵如水般清澈。忽而,不知何处传来一阵清越之声,清爽之气溢满山谷。啊,这便是碓冰的溪水从谷底远远流淌而来之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