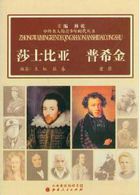清晨醒来,她有着上班的动力,充实了许多。她锁好木屋门,朝居委会的办公地点走去。
第一次她开始发现她的脚步是有目标的前进,眼前没有了往日的迷茫,睡一觉醒来,泡了热水的脚没那么红肿了,却似乎感到行进起来更有力了,她到达时门已经打开了。
一位戴眼镜的斯文且看起来有文化的男人,拿着垃圾正巧从里屋走了出未。
她很奇怪的问道:"大哥,你也是这儿的工作人员吗?"
"我不是的,我只是打扫卫生,我住在这儿。"他面无表情回答着。
“哦,每天都是你打扫吗?”
"是的,打扫这里是我每天要做的活,也是任务。这里是我的房子,我和孩子住在后面屋里。"说着就往后门走去,听到门吱呀一声关上了。
“任务,任务。”她脑海里随着这个词汇
走进这间放了两张办公桌的前堂,仅有几个热水瓶简陋地放屋里,她环顾了一下地面,洒了水已清爽干净,整个屋内还透露着湿润的气息。
九酒坐了下来沉思着。脑子里刚才那一幕让她有些疑惑,他觉得那男人冷漠的表情下藏着极大的不情愿和很想爆发的情绪。
可是他又不敢,他好像又怕着什么,就好像被蛇咬了般,踩着蝇子都怕得冷缩缩。
这时,李大爷进来了,眼晴从地面到桌上四处看了一下,道:"这个老周今天还算打扫得比较干净,这同志硬要批评几句才老实,不然总感觉他在对着干让人不舒服。"
她诧异地望着大爷说:"李大爷,这老周是不是给我们这专门打扫卫生的,我刚看到的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
"是的,老周是我们的改造对象,在监狱里关了两年,才放出来不久。这房子是他父亲的,他父亲是地主,在监狱经不起盘问死在那儿了。老周是老师,本来书教得好好的就算了罗,不知他哪根神经出了问题,硬是要我们腾出房子给他住,说三个孩子都大了一间房住五个人住不下。可我们是在这里工作啊,不是要占房子咧!好了,他把我们告到法院,法院把他作为坏分子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判了两年。我们是同情他,可是我们是干正当的事儿,他也不通情啊!"
听了李大爷这番话,又想着那双情绪低落的眼神,她不知应该对老周是抱以同情,还是要对李大爷所言认真思考。
在那个对错不分的年代,在那个法制不明的年代,很多人就象老周一样忍辱负重,低三下四,象一只只被庵了的公鸡叫一声就被割了喉。
他们的血液好像是凝固的,走在大街上象木偶一样,永远低着那抬不起的头,脸上面无表情,每天不断重复汇报自己的思想,被那些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得意的人指手划脚不敢坑半句声,只能走在那方圆一百米内可怜的一群坏分子。
冤各不同,心境却是一样,不得天日的灰喑,这景象又何时是尽头。
此时这位新来的治保主任一句话也不想说,她是穷苦人家出生的孩子,虽然她不是强者,但她永远同情弱者,她心里永远都有把平衡的尺子。
几个委员在这干净的办公室开了个碰头会,就各自行事去了,在李大爷的叮嘱下,她也一个人出去转去了,她也必须独立的行驶自己职责,直到此时她才逐渐明白居委会大大小小,婆婆妈妈的事就是她们的工作,凝聚街道的安定团结是核心。
她手臂上戴了个红袖章,出门了,这就是街道委员们身份的象征,虽然心里有种自豪感和归属感,只是这一天的感觉有点卡得慌。
她真的很想走到办公室的那张后门去看一看五个人住在一间房子里的状况,但又没有,她怕这样太鲁莽。
她觉得这不是她要管的事儿,但一想到那周老师眼神又有着极大的同情,她刚脆不想,穿走在大街小巷。
昨天走过的角角落落她又走了一遍,没人认得她,直到了她住的那条街附近开始有人向她打招呼了:"九酒,参加革命了啰,红袖章戴起来了,还真像管事儿的。"附近居民开起玩笑来。
她回答得极快,道:"你们莫笑,怪难为情哟,我以后有工作了,不是家庭主妇了,你们还要笑我,也真是的,要祝福我啊!"说这话她有些自喜的得意表情。
九酒这个名字人们已无法改口,既使她有了孙子,也伴随着她整个一生。
这第二遍的巡视,她觉得没有那么累,转一个圈下来,脚也没那么疼了,她默念了一句:看来,人还是得走出来活动,这筋骨动一动,人都精神不少。
她确实有着这体会,哪怕是这丝毫的变化她都觉察到了。回到办公室,这时已是中午11点多,她对于早晨经历的事情一直耿耿于怀,她向后门望了一下,那是静悄悄的没有声音。
她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只觉得这世道怎么了,属于自己的东西若是心甘情愿或者自己用不上奉献出来那是自愿的,而违背心愿想争取回来却被人当头一棒打得再也不敢做声,犹如被恶狗咬了一口,连预防针也不敢去打。
是生是死任由命运的安排,苦得闭气,她现在的感受和周老师一样郁闷,她无资格插嘴。
可她那抱不平的心态又萌生了起来,只是她想,这是自己无论如何也帮不到的,可是却又偏偏第一日去居委会上班让她遇到,她闷闷不乐。
回到家,她饭也没吃,就往床上一躺,哪里也不想去了,她觉得这个世界太复杂,她现在开始怀疑自己选择的路到底对不对,她闭上眼睛只想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