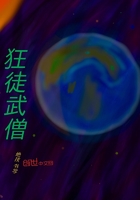再次醒来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吉雅望着乌仁图雅苍白的面容高兴道:“公主你终于醒了,可着急死我了。”
乌仁图雅淡淡一笑,低首瞥了瞥缠在自己胳膊上的纱布,心中微微一愕,吉雅是个大马虎,不可能包扎得如此细心,难道是?
吉雅见她左手摸着纱布凝眉不语,嘟囔道:“公主,其实塔布囊心里是有你的,这伤口就是他亲手为你包扎的,药也是他亲自为你煎的,他来看过你三次,只是你一直没有醒来,他还吩咐我好好照顾你呢。”
心中的错愕更胜,他竟然会照顾她么?那块千年寒冰要融化了吗?想到这里,乌仁图雅冲动地展站起身伸手便要去拿大氅。
“公主你要出去吗?你的伤还没好,不能乱动的。”
是啊,即使去了又能说些什么呢?只不过是徒增尴尬罢了,乌仁图雅收回刚刚迈出的脚步,又叹了口气坐在了床上。
几里外的马厩旁,应城掀开帘子跨入一座破旧的毡帐,毡帐里以为五十岁开外的中年男子正在独自饮酒,见应城来一脸的喜色,叫道:“来,喝酒。”
“大哥真是好兴致,躲在这种地方日日逍遥快活。”
“哈哈哈,落小弟也是好兴致啊,不然又有谁会知道,在这马厩之中的是和昌国二皇子应城,扶南的驸马,武林新秀落梅风,惜君刀的主人。”
应城笑了笑,别有深意地望着眼前饱经沧桑的中年男子:“谁又会想到,昔日的“小季子”会是扶南马场上的弼马温。”
我在手中的酒囊动了动,中年男子又继续道:“此话怎讲?”
“你独自一人,日日都需生火做饭,但你拿柴火的姿势却异于常人,比起劈柴生火,你更像是拿着一把尚未锻造成形的宝剑细细端详,更何况,你手臂上的云形文身是是练剑世家冯氏所独有,若果这些都不能说明你就是二十年前的“小季子”冯玉宽,应某也无话可说了。”
冯玉宽闻言叹道:“我一生遮遮掩掩,谨小慎微,没想到还是在你这儿露出了马脚。”
“前辈既已孤身一人,又何必躲躲藏藏?”
沧桑的双眼里沉淀出几分淡然,冯玉宽笑道:“人,无不生活在枷锁之中,如果我能放下一切,还不如去做个吃斋念佛的和尚。”
灶火发出哔哔啵啵的声响,破旧的毡帐里传出几声爽朗豪放的笑声,然而,谁又能想到,这笑声是从一个内心千疮百孔的人的嘴里发出的呢?
远处豪华的毡帐里,却有一个拍案而起,满脸怒容的人:“什么!应天打算派人从葵水出发,辛余国也要派兵?”
脱脱长叹道:“内忧外患啊。”
帖木儿紧紧攥着青筋暴露的拳头:“鼠疫解决得怎么样了?”
塔拉吞吞吐吐道:“中鼠疫的人越来越多,波日特将军也在家养伤,无法上战场。”
帖木儿心中虽有怒气,语气却是冷静,坚定无比:“即便拼尽最后一把力气,我们也要战斗到底,我们是草原的王,如今,只有本王亲自上战场了。”
脱脱急道:“那我们的扶南大营怎么办?”
鼠疫,干旱和和昌国的野心让扶南内外交困,帖木儿与塔拉一行人商议许久,都未能想出一个上上之策。已经有很多扶南子民染病,能够着急起来的兵马也不足五万人,可是仅辛余国派出的军队就有二十万之多,敌众我寡,扶南又粮草不继,命运堪忧。饭菜换了好几次,帖木儿始终没吃一口,最后索性命人不要在端上来,独自一人在帐里思忖对敌之策。
“哥哥”
不知什么时候乌仁图雅端着一盘饭菜来到了帐中,帖木儿叹道:“哥没心思吃饭,你撤了吧。”
“妹妹就是来为哥哥找对策的。”
帖木儿闻言急道:“妹妹又办法?”
“也不是什么好主意,只是还算得上是个办法,成王败寇,哥哥得自己拿主意。”
“你快说。”
“让应城南下对敌,哥哥坐镇大营。”
帖木儿闻言眼前一亮,随即目光又暗了下去。他虽然对应城没有好感,但他也知道应城绝对不是个简单人物,江湖上不知有多少人为了惜君刀明争暗抢,但惜君刀却始终完好无损的在应城手里,单凭这一点他就已经十分可畏,只是,他毕竟是应天的哥哥。
“为什么会是他?”
“他不止一次说过,如若他再和应天相见,必是生死相搏,前些日子,和昌来了他一位朋友,说是和昌先皇曾有遗命,如果应天为政不仁,可命令神电营软禁应天,并且取而代之。应城当时并没有答应,但却说过要去报仇。到时候,哥哥只需要召集众人,命应城统领大军,至于辛余国,妹妹曾跟他们的统帅侯胜勇有一面之缘,我可以去说服他。”
迎战和昌决定着一众草原儿郎的命运,一念之差将会永无翻身的机会,帖木儿长舒一口气:“南下是大事,你先下去,容哥哥再好好考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