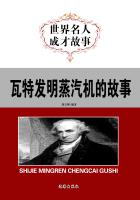云天师似乎早有准备,一见屋中扬起清风,便从怀中掏出一张符纸贴在额心,口中念决,符纸化为飞灰,已经能通阴阳。听见秦辰那似是而非的话,云天师蒙了蒙,问道:“怎么?我看错了?”
“岂止是看错?”秦辰嘴角勾起一抹玩味,“那姓龙的勉强还行,其他人嘛,呵呵。”
“这么说,我们这些人去不了了?”云天师脸色一沉,惊慌追问。
“那倒不至于,就是会辛苦一点。”秦辰摊了摊手,不以为然的回他。
“哎……”云天师捋了把胡须,写满皱纹的脸拧巴了些,心里是各种打鼓,虽然此行诱惑挺大,但是,这事儿搞不好真会丢掉小命啊……
几日前,秦辰喜滋滋的过来找云天师,说是发现了个好买卖介绍给他。起先云天师并不相信,可等秦辰将情况一说明,这穷得叮当都不响的老头又开始心痒痒了。
按照秦辰带来的消息,据说秦岭一带的深山埋了很多古墓,不过经千百年的偷盗和考古挖掘,绝大部分墓地已经被发现,剩下的屈指可数,而且格外凶险。而秦辰介绍给云天师的那个墓,与普通古墓有所不同。按理说,能在这样险峻的地方开山凿石建造巨型工程的,怎么着也是个大官吧?或者是个能在历史上找到名字的人物吧?
可是,这个墓却是个无名无姓的野坟,它不但是数代人合葬,而且这些人在历史上都没有名气,所以根本没人注意他们死后所在。
据闻,那些人是秦朝末年的叛兵和流民,因为厌恶征战逃亡于此,后来扎地生根,繁衍生息,与外界完全隔绝。而在这些流亡的人当中,不乏能人贤士,其中有一个鲁班真传的后人,极为善于机关之术,传言那座墓便是那位后人和他的徒子徒孙耗费好几代的时间和力气建造。
当然了,如果仅仅如此,云天师是万万不会答应去那鬼地方的!他对机关之术毫无兴趣,并不想膜拜前人的遗作,且不说里面暗危重重,还又是个群葬坑,指不定会有些僵尸粽子或者厉鬼阴魂什么的,不如让那些脏东西困在那里,永无天日最好。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却有一个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诱惑,那就是——钱!
二战期间,战火几乎烧遍了整个中国,当时附近一带的商贾都怕哪天枪杆子指到自己头上,一辈子的辛苦积蓄被抢了不说,还要将命给搭进去。所以,当地慢慢掀起一股避财免灾的风气,后来,又由一个巨富牵头,以自己在村里乡里的信誉,大放厥词,说是他有全天下最好的藏金库!
来找巨富的人越来越多,巨富便临时建了个合作银行,不多久,又请遍周近的风水术士,历经多年寻找,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桃花源”,并以十几辆马车托运,在数百精壮男子的护送下,连夜出发将金银财宝全部送去藏起来!
可是,那些送金银财宝的人去了竟然死伤大半,只有几个人成功逃了回来,伤的伤,残的残,瞎的瞎,哑的哑,那些回来的人当中,有一半的人已经疯疯傻傻神志不清,只有几个还能说话的,一提到那一趟旅程,都会惊恐的抱头尖叫,叮嘱他人千万不要再去那样的地方!
人们被他们的话吓到,自然不敢再去,这么多年过去了,知道这件事的人已经寥寥无几。
云天师听这事儿玄乎,便想到里面可能有什么厉害的角色,凭他一己之力难以抗衡,于是直打退堂鼓,奈何秦辰又鼓励他找些在盗墓界有经验的人一同前去,拿到金银财宝大家一起分,云天师便这么稀里糊涂上了贼船。
不过,这些信息都是秦辰一面之词,又没什么确凿的证据,折腾了好几日,云天师甚至连个正经方位都不知道在哪儿,说出来的话也没底气,更别说去说服别人了。
那些有头有脸的人一听这事就不觉得靠谱,且又跟云天师不熟没交情,所以压根儿不搭理云天师,后来,他好不容易撞见老熟人田家父子,那父子俩这些年混得不好,已经很久没沾荤腥,心里着实痒痒得很,不论什么鬼地方也想冲一冲,所以才掺和了进来,还帮着联系上了胡老大,不过,胡老大也看不上他们这支小队,随便打发了两个人刚进组织的年轻人过来,也算是薄施恩惠了。
经由云天师长长一番介绍,管宛才大体明白这事情的整个脉络,想来昨天看见云天师兴奋得喝得烂醉,应该就是见到久仰大名的胡老大,并从对方手上领了两个人,以为此行十拿九稳了吧?
“你为什么让师父去那么危险的地方?钱?你不需要,你的目的是什么?”管宛沉思片刻,秀气的脸上冷冷淡淡,看不出任何情绪,只见她轻轻抬头,目光微微扬起一些,朝着秦辰问道。
见管宛主动搭话,秦辰立即露出一副十分狗腿子的猥琐笑,“口袋里有钱说话才硬气,我是不需要,但你需要啊!老公出去压趟镖,赚点小钱给老婆花!”
管宛冷着眸子想了想,觉得这个理由可信度不高,便继续追问:“秦家产业雄厚,随便搬点出来不就够用了,何必冒险去那么远的地方?这不符合你的行为,想当初你连道观的东西都能顺走,何况是你自己家的?你继续编,我听着!”
秦辰不料那些陈年小事她还记着,顿时冷汗速速,心里一阵发虚,看来女人聪明起来也是相当可怕啊!
他苦着脸嘴硬道:“你讨厌我妈,我怕那钱你用着不舒坦……”
“哦?真可惜。”管宛捋了捋身上的衣服,唇角略微有些紧绷,垂下目光遮去眼中繁复,好在,并未失去理智。
“小宛啊……你没事吧?”旁侧的云天师也察觉出管宛眼中的神色变化,小心翼翼的关怀了一句。
管宛轻轻摇头,目光却直直看向薄唇紧抿的秦辰,语声清淡道:“我信你一次。”
“什么?”男人骤然一惊,仿若幻听般满脸呆滞。
“有关秦夫人的事,我信你一次。”她曼声重复一遍,转而低头喃喃,仿若自语,“希望不是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