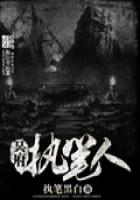管宛低头苦笑一阵,再仰起头的时候,那副半生不死的面容,已经被一种傲然替代,她微微垫脚,仰头附上他的唇,主动去吻他,即便畏惧到耳鸣,头脑麻痹,她还是用两根木棍似的手臂拥抱他,迫他贴紧自己。
温热的舌尖舔过他的唇,他的脸颊,她微微张开眼睛,看见他眉头浅拧,一动不动,便加重力道去撬开他紧闭的唇齿,贴在他耳边故作低吟,但因心中过于浓烈的畏惧,声音听上去无比颤抖,就像尚不更事的少女,渴求,诱惑,却窘态百出:“王珺胥,你在等这个吗?”
直呼其名。
充满不敬。
管宛依稀记得,当初他透过琉妘珠,教她对付玖笙时说过,可以野蛮一点……
就是不知,对他有没有效果。
而且,此前玖笙告诉她,琉妘珠里的人是王珺胥,音色听上去也的确很像,但眼前的男人却比透过琉妘珠和她对话时冷漠许多,几乎连个正经的笑脸都没有,只有轻蔑和讥诮。
管宛捉摸不透,只能一点点去尝试。
被她揽住的君王垂目扫她一眼,眸光渐渐发冷,不过片刻迟疑,竟猛地将她推出去摔落在床上,王珺胥居高临下的望着她狼狈的模样,故意羞辱,故意冷嘲:“你已经脏了,阿音,你给别人生了孩子。”
语中的不屑与抨击,似乎是要让她羞愤至死。
但那女人偏偏不,管宛挣扎着坐起来,她清楚的知道,爱上秦辰,为秦辰生子,自己从未后悔,她不觉得脏,不觉得那是一件可耻的事,不论王珺胥是何种态度,都不会改变她的想法。
反倒是他,口上如此说着,当年却做出那样没有水准的事,还毁灭与自己相互依存的玖笙,所以,该羞愤的,该惭愧的,是他才对!
管宛支了手臂,斜倚在床上,不知是嘲讽,还是勾引,笑得邪气而充满挑衅:“听说你不育,难道……连正常的功能也没了?啧啧啧,可怜。”
王珺胥冰冷的视线寂寂挪来,眸光深处似有怒焰纷飞。
他慢步走来,与她面对面,互相逼视,宽阔的身躯将她重新压制在柔软的床榻上,缓缓贴近,不动一字,不说一语,就是这样简单的举动,证明了自己。管宛察觉被什么硬物顶住,嚣张的气焰立刻荏了几分。
她终究还是怕他的,即便已经看透参透,即便为了目的决定割舍某些东西,可王珺胥那双比刀锋还要寒彻的眼眸,如此近距离的迎难逼来,毫无怯色,冷漠的扣住她,与她正面相抗之际,她的眼神终是不由自主的闪躲了一下。
“套上狼皮,你还是只羊。”冰冷的声线,此刻华丽低转,充满欲念。
管宛全身不由绷紧,她强迫自己迎上他的眼眸,无视他的话语,扯出一个自己都不知道算不算得的笑,压住自己颤抖的凌乱,反唇相讥:“不行不要勉强。”
说一个男人不行,无疑是一种侮辱。
但王珺胥却没有明显的波动,事不关己一般冷冷的凝着她,他清晰的感受到,在他靠近的瞬间,她连呼吸都吓得止住了,一直偷偷憋着气,像是怕露出一丁点混乱,可却不知,闭气只会叫她看上去更蠢。
许久沉默,王珺胥宛如石刻的雕塑,不见动作,正当管宛以为他会保持这样的姿势,到全身肌肉酸疼不得不退时,他却突然埋下头,贴到她的脖子上!
管宛迷惑的颤了一下,瞳孔微微放大,便觉有尖利的獠牙挑衅的摩擦她的脖颈,她心中惴惴,畏惧又不解,突然袭来一阵刺疼,锋利的牙齿刺破她的肌肤,深深埋入体内,吸食血管里温热的猩红。她仿佛听见肌理被切割的响动,震惊不已,疼痛不已,却死死咬住下唇,不发出一点声音。恍惚中,好像听得他说:“你的血,可比你干净多了。”
“……”管宛被他制服的动作微仰起脸,喉口滞塞到无法呼吸。
他稍微停下几秒,目光隐隐绰绰的看着她痛苦的模样,轻声说:“这样,才能品味出你的鲜美。”
“变态……”管宛心中暴动,用力挤出两个字,又迅速将后面的谩骂全部吞回腹中。
要忍。
不能退缩。
必须先降低他的防备,才可能有机会跟他搏一搏。
要、忍……
“呵,看你享受的样子,你不是恨我吗?真有趣,原来你视若至宝的爱情,不过就是块遮羞布,随便谁都可以扯碎。阿音,你不但坏,还放—荡,那只臭蟑螂看见这样的场面,会难过死吧?”
王珺胥抬起头,瞥见被他扎破的伤口落下两注血痕,探出手,冰凉的指尖轻轻擦拭,猩红染指,男人将指腹的残血微含在嘴里,目光迷离,色—气摇曳,竟有种诡异的魅惑与性感,他语中带笑,缱绻绵长,第一次在她面前露出一点零星笑意,却是建立在对她羞辱的痛苦之上。
“坏丫头,你再乖一点,我可能就舍不得吃掉你了。”
管宛正觉羞耻,却被他一句轻得几乎听不完全的话打断,她茫茫然睁开紧闭的双眼,就见王珺胥起身离开,玄色王袍化为烟淼穿过房间,门一开一合,人已离去。
他最后那句话,说了什么?
管宛拧了拧眉,又觉脖子上疼得要命,伤口处新冒出一点血来,将洁白的床单染出一块微小的血斑,她挣扎着坐起来,低沉无言,默默去找纸巾,却恍惚发现自己双手打着石膏,根本无法自理……
她扭头望向镜子里的自己,脸色苍白,神色疲惫,两只眼睛毫无光彩,又粗又笨重的石膏限制了她的动作,她像个废人一样仰躺在床上,黑沉沉的眼瞳,默默滑下眼泪。
笨蛋,要忍住。
不能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