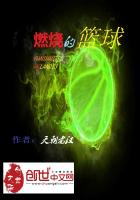85年出生,到今日已过30岁了,毫无成就却也能平凡的活着,我相信像我这种状态的人有许许多多。我想把这种人生回忆起来,记录下来,以便到了我们老的时代,我的孩子们能更多了解我们,虽然他们可能懒得读得半篇,但我可以自己读给自己,自己纪念自己。
我的出生地是华北地道的农村,可以说当时农村典型的缩影,村里满地是散养的鸡鸭,偶尔有猪因为拱坏白菜被菜地主人家追赶,村里有全县唯一条两车道沥青省道穿过。那时候农村是包围城市的,农村的人要远多于城市,农村的气息远多于城市,电视和广播除了广告、电视剧是普通话外,其他节目到处有农村的气息。而我家也是典型的农家庭,家里只有两辆自行车、一辆两轮木拉车,甚至连一个轮胎打气管都没有,蓝色的砖房下雨时房顶就要漏水。这些现在看来并没有什么,但最令人遗憾的是那时基本没有书,这应该是真正的贫穷。因为没有书,我不得不在自己的无知世界里靠直觉和经验前行,那时自己最大榜样是村里的一个孩子王,最大的权威是村里一个“老干部”。但无知的也有一定“好处”,就是怂恿你的自尊,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那时反而不知道什么是自卑。
我7岁大约是1992年开始上学,大概6月的一天我放羊回来路过超家的门口正好遇到他,他让头羊啃他的苹果,然后趁机压住头羊一个跳马跳过来,“你今年上学不,我娘已经帮我给未老师报名了,到时候我们在一个桌吧”,“真的,我回去问一下”,我回到家赶紧问“娘,你帮我报上学的名了吗,燕超他已经报名了”。“开始了?我咋没听说,即使你上学了,放学你也要去放羊”,母亲她提前给我打预防针。
放羊简直就是一个无法摆脱的阴影笼罩着我的童年,在我姐上学后,我接替我姐成为全村里知名的6岁羊娃,虽然我并不讨厌羊,但惮于每那种天定时定点去放羊的“重复”与“孤独”,我的朋友曾认同说这和她每天放学后弹古筝时的感觉很像。自从有了上学这个“希望”后,我母亲形容我是每天”耷拉着脑袋”去放羊。是的,我感觉我的“苦难”全是这群羊造成的,虽然有时候我想揍它们,可是我的个头比羊高不了多少,特别是那两个公羊。放羊也有放羊人的江湖,我本来是和一个老头结盟一起放羊,偶尔能抢占最好的草坑,有时我还能央求那个老头帮我照看一下羊群,我借机偷着去挖“胶泥”或者抓蝗虫将军(一种很大很帅的蝗虫),可是这两个公羊老是去性骚扰老头的羊群里的母羊,搞得羊群不能安分。几次下来,老头认为这很伤害羊安静的吃草长肉就抛弃了我。外村的几个放羊的羊主更是挤兑我,不允许我的羊群吃他们所抢占优质草坑,还有几次那两只公羊受人家羊群里的羊姑娘吸引跟着人家羊群回家了,人家几乎不肯归还。
放羊这种需要独立承受的事情倒是对日后的独立和忍耐有一定的帮助。有时候夏天一阵狂风大雨袭来,羊群四散,只剩下一个弱小的孩子站在天与地的中间,就像一个被上帝抛弃的孤独的天使。但我已经学会不哭泣不哀怨,有时我甚至继续蹲下去玩我的“胶泥”,或者躺在泥水里扑腾。雨终究会停,而且有时彩虹还会出来,我重新聚齐羊群像胜利者一样回家。我母亲已经在家门口等我,她清点好羊,有时还给我一杯热水喝,然后我脱光了湿透脏透的衣服躺在凉席上能睡上好长时间。
现在我终于能上学了,我能有近7个小时的时间摆脱父母亲的指挥,农村的父母禁止孩子做什么情况比较少,规矩很少,但喜欢命令指挥孩子烧火、倒水等等杂七杂八的家务活。因此在我的家庭,我不知道我不能做什么,但我清楚我不愿做什么,而且我能根据情势很的推断出他们准备指挥我做什么,所以很我擅长逃溜。到了第一天上学的时候,我很早就起床了,我已经有一个母亲用旧衣服剪下的布头缝好的书包,还有一个新做的木凳子,我已经用小刀把上面的毛刺削干净了,我本想在上面刻上我的名字,可惜我还没学会姓字“瞿”,而姐姐又不肯使用我的那个刀子。我问母亲要学费,母亲说“我记得是11块,也好像是9块,你先拿9块,不够的话可以跟校长讲讲价”,但我担心母亲的糊涂记忆,我还是带上了自己5块私房钱,一个糊涂的母亲往往能够反向帮助孩子储备怀疑的精神,正因为他们的糊涂,我从小就不相信父母的话,一般我会留着自己做决定的回转余地。
学校在村东头,燕超应该是他哥哥带过去的,我也有一个姐,但她已是在3公里外的初中上学了,我只好自己的拖着75公分高凳子蹒跚着前进,路上遇到几个邻居叔叔、婶婶,他们戏谑的问一声“哎呦,二青,你不放羊要上学了呀”,我会带着解放翻身的腔调回一声“再也不放了!”。等我到了学校,我看见大家已经在院子里按高矮排队组同桌了,校门口放了一个新生报到的桌子,后面有一个漂亮的老师姐姐,她问“你是谁家的孩子”,我报了我父亲的名字,这便算核实了身份。
“学费是11块,你今天带来了吗”,
“够的,老师”我暗自庆幸不用回家取钱了,但我真的是不舍得我的私房钱,还好我分到了三本书。
“小二青,你赶紧过来排队”,校长几乎知道村里所有的孩子。我因为比较矮被校长摸着脑壳在队伍中插来查去,最后插到第三个,正好和第四个小胖子男生“小康”做同桌。第一天就课堂讲了什么几乎记不得,只是发觉这也有一个“江湖”。我的榜样“孩子王”已经排不到大王了,新的大王应该是一个“刘姓”孩子,他虽然不是最高大的,但是最匪气的,他敢和老师顶嘴。刚开始根据以往交情熟悉程度,一共20个男生分成三拨玩。刘姓孩子王一拨刚开始没有欺负我们,课休期间他们组成小团体划好范围玩玻璃球、摔三角,还有一拨围绕二年级的孩子王在玩骑马打仗等游戏,剩下的几个就是没人要的了,其中也包括我和我的同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