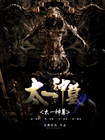大唐国极边的辽西城,此时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阴沉沉的天气映着黑黢黢的城。
辽西城里有家大善人,人称黄四爷,古稀年纪,会一手望气相面的功夫,少有的灵验,因此颇受人敬重。
这天天刚亮便起了床,推开宅门,只见雪皑皑的大街上人来人往,四下里破烂家什扔了一地,行人神色仓惶,往日熙熙攘攘的来往客商现在半个也见不着。
外面响了一夜,黄四爷也睡不着,此时只把眼睛往里屋张望,一条半人高的大黄狗悠悠地踱过来,到黄四爷裤腿上蹭了蹭。
“阿福!”黄四爷喊了声。
“哎,老爷,就来!“后院里遥遥地传来声吆喝,不多时,一个青灰麻布衣裳的老仆匆匆赶过来。
阿福是黄四爷家的老管家,虽说也是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但平日里最重体面,这时候也灰头土脸,忙了一夜,两眼红肿,一鼻子灰。
“老爷,车马细软都收拾妥当,城里军卫李督头派给咱们的健卒方才也到了,就看老爷您什么时候启程?”
“唔……“黄四爷闭了眼睛,手指掐了会儿,阿福束手立在一边,脸上带着些敬畏。要说这老爷趋利避害的本事,至少是阿福这么多年来见到的术士里首屈一指的。
大黄狗这时候却莫名地有些焦躁,突然站起来,着急地转着圈,龇牙咧嘴地“呜呜”叫,阿福慌忙想去拉住它,但半人高的大狗,却怎的能拉住?
就在此时,黄四爷脸色突然一白,“哇”地吐出口鲜血来,冒着热气儿,溅在雪地里格外刺眼。
“老爷!”阿福惊了一咯噔,手忙脚乱想去扶,然而年纪大了手脚不利索,眼看黄四爷摇摇晃晃要倒在地上,大黄狗“腾”地窜出去,在后头稳稳地托住了。
阿福喘着粗气,惊惶地叫喊起来,门里门外平日里认得黄四爷的,敬重黄四爷的纷纷过来看,一干家眷手忙脚乱把黄四爷抬进了屋。
谁料刚抬到半道上,黄四爷突然便醒了,一把抱住跟在一边的大黄狗,死死搂进怀里,声嘶力竭,“走!马上就走!”这凄惶的声音仿佛从那九幽黄泉迸出来,浑然不似这人间的调子,说完便晕了过去,只是攥着大黄狗项圈不松开。
门外那些看热闹的素日里也识得黄四爷的名声,听了这声怪叫更是仓惶起来,各自舍了手底下的大物件,纷纷逃命去了。
家眷老小和军伍的健卒急忙把车马赶来,把黄四爷放在后头最宽敞的车里躺下,攥着的手一时也松不开,便让大黄狗和黄四爷同乘了一个车,一行人锁了院子,并着车马匆匆地出了城。
刚出得城门,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那雪下地又密又大,片刻功夫便盖了城头,平了官道。路旁树头一片银白,远处高山银白一片,影幢幢只看个轮廓。回首看时,黑黢黢的辽西城也似飘在云里雾里,车走的远了,城也不见了。
健卒往牲口背上盖了蓑笠,各自躲到车里,单留着六个车夫在外头赶着车。
不知不觉车马赶了半日,城早已是不见了,官道上不时可见到三五成群逃难的百姓,间或还可看着几个微微隆起的雪堆,旁边散落着一些细软家什尚未被盖住,那些是不慎落难的百姓。
死来地做衾,黄泉雪为被。从来无福享,归时天地藏。这情景看得黄家众人各自面色惨淡,心里也多了几分惊恐和焦急。
大车里,黄四爷颤着手摸过大黄狗的脑袋,双目瞪着棚顶,却没了半分往日的神气。
他方才刚出城不久便醒了,只是浑身疲软没有气力,也便一直躺着。
“黄酒啊黄酒,乱世之人贱如狗,大唐的气数却是尽了啊!“黄四爷呜呜咽咽,浑浊的眼里洒下泪来。
大黄狗凑上前,趴在一边,也不动弹,油亮的毛皮子蹭着黄四爷,软软的舒服。
“唉……到如今,也就你还陪着俺……”黄四爷长长一叹,这黄狗是他十一二岁的年纪捡到的,因当时手里提着一壶黄酒,自家也姓黄,便把“黄酒”予了这狗做名字。后来偶遇一奇人,教了他算命卜易的功夫。
原本四十岁那年,这黄狗已是垂垂老矣,眼看不行了,只等天一明变拿去安葬。谁料第二天一早,只见黄狗在外面活蹦乱跳撒着欢,原先的枯槁杂毛褪了一地。
初时也担心,只道这黄狗吸了人气成了精,但时日久了,家宅照常安宁,黄酒偶尔还抓着几个小毛贼,便也不管了。
老伴儿早早离了世,家眷也因他这手卜算吉凶的本事对他敬畏有加,只有黄酒不离不弃,陪伴至今。算来,这黄狗如今也已是六十多岁年纪。
“先前算起来,此行大凶,但留在城里却是必死无疑,天轨九万万,有一线生机,终究还是道行太浅,算不出这生机应在哪里……“黄四爷平复了心情,只顾喃喃自语。
黄酒喷了个响鼻,换个姿势躺着,看得黄四爷一时失笑,“你这畜生活得久了,倒是非凡,朝代更迭与你何干,便是天翻地倾和你也没甚关系。“
黄酒惬意地翻个身,颇有些灵动的眼睛瞟了瞟黄四爷,自顾睡觉了。
闲话休叙,一行车马走走停停,奔着北漠而去,已有半个月的功夫,此时却是不下雪了,周边景致渐渐荒起来,稀稀疏疏几颗歪脖子柳树,斜斜地插在黄色沙砾里。
原是在北漠有一家吴姓官人,为人很是仗义,早年受过黄四爷恩惠,念念不忘到如今,一个月前辽军鞑子动兵时便投信与黄四爷,叫他前去避灾。
几天前辽西城破的消息传来,听说鞑子进了城大庆七日,不少栈恋家园不舍离去的好人家被奸杀掳掠,城里火光妖艳,映红半个天,不知多少冤魂投告无门,自此化作孤魂野鬼。
黄四爷听说了之后又是大哭一场,当着一家老小又是吐出几口鲜血来,自此萎靡不振,便只在车里躺着,间或着家人扶着坐在车边上,也时常唉声叹气,望着天际念念有词。
说来也怪,不知何时起,黄酒的身体便一天不如一天,原本油亮的皮毛到如今已大半没了光泽,相比往日更加慵懒,往往一睡便是大半日。
家眷都说这狗通了灵,老太爷如今受不了长途颠沛,这身子眼看不行了,老狗也要伴主西归。
于是一家老小行走交谈时,眼色里都带着些惊惶。就盼着黄四爷能多撑几日,只因习惯了黄四爷主持家里事务,如今大树将倾,一窝猢狲难以自处。
又行了几日,车队渐渐地出了关,车队后头也多了一群“挂搭”的难民。旅途凶险,大漠里常有马贼横行,轻则破财消灾,重则丢了性命。这些人见黄四爷车队庞大,还有军伍健卒,便远远跟着,也不靠近,如此少了很多凶险。
出了关有百里,正是晚上,无垠的荒漠上,挂着一轮红月,隆冬时节,荒漠的夜更是冰寒刺骨,车队停了下来生火歇息。
“老爷,老爷……“阿福在车前轻声喊。
“咳咳……”厚实的门帘掀开一条缝,“什么事?”声音疲惫而虚弱。
“老爷,您这身子……”
“不妨事,让你留意的事情怎样了?“
“哦,着老爷吩咐,今日小的特地看了,后面跟着的还有约莫百人,青壮二十余人,穷苦人家,缺衣少食,几日下来,已有不少掉了队。”
“他们只看到人多好行路,却不知树大招风……咳咳……咳咳……”话说到一半,便是撕心裂肺的咳嗽。
阿福大惊,一把撩开门帘窜上车去,“老爷!”声音在死寂的大漠显得格外凄惶。众人纷纷围拢过来。
四爷瘫软在车里,胸膛像几十年的老风箱,“呼哧“地喘着气。面色灰白,衣襟上一大摊子血迹。
“都过来做什么?还死不了,烦请吴都头和阿福留下,其余人散了吧,咳咳……”黄四爷挥挥手遣散众人,待他们走的远了,才叹口气说道:“老儿自知天命将至,只是有一事还放心不下。”黄四爷倚在苍老的黄狗身上,茫然地盯着顶棚。
“老爷若有什么烦心事,尽管吩咐小的,可是因为后面的流民?“
“这是小事,吴都头,烦请您带几位军爷,到后面尽量招募些鳏寡的青壮,拖家带口的就不必了,不知还要在这大漠上走几日,多些人总是好的。”
那吴都头是健卒的头领,闻言目光微闪,拱了拱手领下命来。
“老爷仁慈,但我们的粮食……”阿福有些担忧。
“粮食尚够,症结不在此处,俺却是另有考虑。此事吴都头比你看得清楚。“
“难道说……”阿福一个激灵,悚然。
“这乱世啊……最不值钱的便是人心,最值得畏惧的是一无所有的人,而且,连日来总感觉心里头不踏实,前路不可知啊……”
第二天一早,黄四爷由阿福搀着,在营地里散步,一晚上的功夫,营地里多了些生面孔,俱是先前后面流民里面挑出来的青壮,瑟缩地站在那里,受着吴都头训斥。
“四爷”见黄四爷来了,吴都头一拱手,毕恭毕敬,与先前相比,更多了几分恭顺和敬重。
“吴都头客气了,”黄四爷摆摆手,虽是病弱之身,却有气定神闲的风度。
“尔等既入得俺黄家,过往事情便抛了罢,不过丑话在前头,老头如今也是朝不保夕,这茫茫大漠,前头百里就是出了名的断魂坡,有马贼盘踞,说不准便是俺的葬身之地,若有心不甘情不愿者,趁早散伙。”黄四爷双目深抠,眼神却着实犀利无比。
“这……“一众鳏寡面面相觑,踌躇不决。
“腌臜泼才,除了这条性命,你们可还有别的长物?若不搏一个出身,趁早转世投了胎,做猪做狗也比这畅快许多!”吴都头厉声呵斥,声色俱厉。
这倒是个人物,只是不知缘何而立年纪才做了都头。彼时所谓都头,不过是尊称,似这吴都头,算起来不过是个伍长,一没金印公文,二无军职衔资,更别提其他特权,不过是图个出身。但此番吴都头的机敏和作为都让黄四爷高看了几眼。
果然,这些青壮各自面色铁青,猩红着眼睛,喘着粗气拱了拱手,自家眷手里领了被服武器,立在吴都头身后。
“都头,“黄四爷拱拱手,“可否借一步说话。”
“但凭四爷吩咐。“
黄四爷挥退身边人,单带着吴都头到营地外面,太阳还未升起,天色略灰,只东面泛着点白。
“不知吴都头今年几庚,家中可还有亲眷?”
“都头不敢当,从来独身一人,却是自在惯了。“
“哦……”黄四爷沉默片刻,由吴都头扶着缓缓上了一个小沙丘,向远处眺望”再往前百里就是断魂坡,大漠上马匪剽悍,此行凶多吉少。“
“但有俺一口气在,保得四爷一家老小周全!“
”当真?“
“千真万确!”
“为何?“黄四爷目光灼灼,面容枯槁却有着凛然的威风。
“忠义而已。”吴都头毫无惧色地与黄四爷对视,神色一片平静。
“我于你一无救命恩,二无过往情,何来忠义?龙游浅水,鹰翔荆棘!你到底是何人?“
”四爷过奖,吴某不敢当。只是四爷可还记得北陌雄城吴相公?“
“此行本就是去投奔他……嘶……你……”黄四爷倒吸一口凉气,上下仔细打量,脸上确实渐渐露出狐疑。
“四爷莫要误会,小可怎敢与吴相公相提并论,本是一亡命徒,错蒙相公赏识,赐了吴姓。受命于相公,伺伏在辽西城中,只等风声一起,便带四爷及家眷脱了这城。任务在身,不敢钻营,故而至今仍只是个火头,于四爷帮衬极少,还请见谅。”
“他到底是何人物?能驱使你这等豪杰!”黄四爷自傲识人从未偏差,本以为只是个一时落魄、病倒街头的生意人,怎知当时一时善举,得了今日的善果。
“相公是何人四爷到了便知,只需知晓世事无常,任那九天神龙也有落难的时候,仙家之人,更是三灾六难。晓得难让四爷信任,特差人赐予小的此物!”吴都头摸出一块玉坠,只见上面流光溢彩,隐约有风呼海啸之音,一个“吴”字熠熠生辉,不是凡物。
“如此……罢了……”黄四爷恍然,心里疑虑顿消,大唐崇仙尚道,各地早有一些异人传闻,修仙问道亦不是空穴来风。
蓦地,黄四爷一拱手,长揖及地,慌得吴都头急忙扶起,连说不敢当。
“老儿痴长这些年纪,家中无成才后人可以担当,自知时日无多,烦请吴都头日后多加扶持!拜谢!”
“您这说的什么话,便是小的不在了,到了北陌城,吴相公也会照顾好您。”吴都头有些惶恐。
“老儿不才,这些年景还是攒下了几分薄财,待安顿家眷完毕,尽数奉予都头,还请都头务必答应!“
“这……”吴都头目光微闪,他本不是一个安分的人,虽说如今在吴相公手下奔忙,却也爱财,连日来望见黄四爷家底丰厚。只是他虽贪黄白之物,却也极重承诺,故此犹豫。
“吴都头勿再推辞,拜谢拜谢!“黄四爷诚恳道。
“罢了罢了,答应你便是,有俺在一日,便不叫你家眷受人欺辱半分。”
“如此甚好,甚好……“黄四爷长叹一口气,抬头望着即将升起的太阳,眼睛微眯,口中喃喃自语,“浪荡四五载,漂泊六七年,八九苍茫天,因果了难全……”话音未落,推金山倒玉柱垮了下来,吴都头一把抱住,大声喊叫,整个营地又乱作一团……
自这一倒下之后,黄四爷便再没起身,每日里有人端茶倒水,吃喝拉撒便全在厢车里,形容枯槁,涎水四流,如那中风之人一般不能自理。
老黄狗虽说身子疲弱,行走间倒也矍铄。不时叼着弄脏的衣服被褥下车,交与家人清洗。吴都头自是担起了整个车队的大小事项,为人倒也规矩负责,不曾有丝毫越矩之事。
车队向前行了百里,果然遇到马匪,吴都头神勇异常,然而双拳难敌四手,黄四爷一家老小多少死伤了一些。
值得一提的是,老黄狗一反常态,端的是凶猛无比,护得黄四爷的厢车如铁打的桶盘,但凡有敢于上前的马匪,便支起庞大的身躯,一通狂抓乱咬,令数十马匪不敢靠前。
然而黄狗终究老了,那马匪的头领也不是等闲,便下令放箭,箭翎穿过厢车的窗子,黄四爷难以闪避,一命呜呼,黄狗也被扎得如同刺猬一般,趴在地上奄奄一息。
便在此时,一团流光水银泻地般从吴都头胸口涌出,护住其全身上下。吴都头如同天兵下凡,变得力大无穷,又仗着刀枪不入,强夺了一匹马冲进战团,迅即取了马匪头领首级。
马匪溃退,吴都头率着家眷重整行装,将黄四爷和黄狗找了个高处埋了,继续向北陌前行。
黄四爷终究难逃一劫,客死他乡,忠犬一生相伴,与之同穴。一家老小托付他人,不知前途几何,然而世事无常,天道轮转,谁又知晓未来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