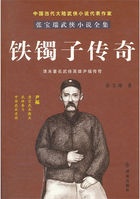但丁面对女人哭泣的时候,已经是第几次来到那扇铁门里了,他似乎记不清楚,这让他晕眩。他为什么要这样呢?他的步子是沉重的。他看见过母亲的哭泣,邻家女孩的哭泣,大学女友的哭泣,还有后来姐姐的哭泣,可是这个女人的哭泣却有一种令他难忘的力量。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暗淡的天花板上有一些水渍,弯弯曲曲像一条蛇。但丁想,我们都不能被蛇所惑。他记得不知是在哪本书上的一句话:肚脐之下无道德,但是撒旦就在那儿。这话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这是深刻的箴言,可怕的悖论。大学女友已经从他的眼前消失了,确切地说,已经从他的房间内、怀里、天花板上,甚至那个简陋至极的抽水马桶上,还有唇边,彻底地消失了。大学女友将门狠狠地关上了,留给他一声关门的巨响,但丁觉得脸上像是受了一记重重的耳光。
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他为什么要撵走女朋友?为什么要将自己从生活里开除,置自己于一种绝境?仅仅就是因为要前往K市寻找自己的亲姐姐吗?或者说他就要真的去过一种一天一个馒头,一根萝卜条的艺术家生活吗?再说那种寻找,无论是对姐姐,还是对艺术之真谛都是一种不确定的寻找,很有可能一无所获。他后来如此对姐姐说:“我那会儿觉得就是和命运偶然打了一次赌。还是必然胜了。”
但丁将目光继续盯住天花板,那里似乎在滴水,那滴水就要滴下来,甚至就要滴到他的鼻子尖上来。当然这是他的一个幻觉。他的确对那个女人的鼻涕记忆犹新。他记得那滴鼻涕,清澈浑圆如水滴挂在她美丽的鼻尖上,但是很快,被她用手掌轻轻地一抹,就不见了踪影。但丁开始有一种饥肠辘辘的感觉,饥饿在啃着他的肠胃。
他还没有吃早饭。时间已经不早了,太阳高过了那边楼顶。那边楼顶上的镏金水塔闪着刺眼的光亮。他开始寻找吃的东西。在寻找的过程中,他的肚子连连地鸣响着。他没有找到吃的东西,桌上、抽屉里都没有,它们出乎寻常的清爽。他本能地摸了摸口袋,口袋里空空如也。他记得自己从厂里回来,那情形历历在目。他一把抱起女友说:“我不用去上班了,我解放了。”你真的去做了?这一切不是玩笑。女友捶了他一顿,并且无情地痛骂了他:“那我们吃什么,你疯了吗?”她这句话还在他的耳朵里回荡着。是的,他真的疯了。他开始从那个简易的塑料衣橱里找到另外一件冬装,他记得有钱放在那衬里的一个口袋里。可是他摸索了半天,没有。口袋同样空空如也。后来他才想起来,这笔钱早就花光了。但丁开始痛恨起钱来。他坐在床沿上,开始将一件件旧衣服拿出来,心存一丝希望,最后在一件春秋装里找到了一个硬币。
口袋里面有一个丝缝,硬币就从那儿滑了进去。他沿着衣服的下摆,摸到了一个硬币。那个硬邦邦的物质使他差点要流泪,之后又摸到了一个,又摸到了一个,竟然一共有九个硬币。他后来下楼去附近的一个馄饨摊上吃了一碗馄饨。他有点百感交集,想起了在县城剧院门口妹妹渴望一碗馄饨的情形。馄饨摊子很简陋,几乎就是一个平板车改造成的,上面案板干净,那些玲珑的小摆碟里的葱花绿油油的,锅里水在翻滚,馄饨一个个白白的,懒懒的,软软的。下馄饨的是一个四十岁开外的女人,脸面素净,双手纤细,上面沾着葱花和油彩。
他为什么要一步步地走向那栋楼呢?他知道他的好友、那个憨厚的家伙并不在家,而她是在家的。一个月前,那家房地产公司因为一栋危楼官司消失了,她由此失业了。她说她已经换了几个工作了。她现在每天就在等工作,等工作也是她的工作。而他却彻底地抛弃了工作,曾记得有人这么问他在什么地方上班。他说抄抄写写,然后就是在大街上看看逛逛。说起来,这个古怪的工作别人很难相信。世上还有这么个工作?后来他跟女朋友戏谑地说,那是一个低头和仰头的工作。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女朋友那会儿总是笑着捏着拳头打他。现在没有人问他做什么工作了,人们总会不无谴责地说,干吗好好的工作不要,有人找不到工作,你不是有病嘛!那个女人也这么问他,你为什么要抛弃你的工作呢?他说,我要过一种自由的生活。他当时是这么说的,脸上满是欣喜的光亮。
那栋楼似乎很近了,小区里安静得很。很多的树,绿阴如盖似乎更增添了小区的静穆。
他为什么要去呢?他本可以一走了之。他应该直接上车离开。这种可怕的渴望撕裂着他的内心,他似乎听见另一个人在他的体内呵斥他。你要去干什么呢?你去了不等于是要深陷泥潭吗?你应该止步。
但丁在大楼下有点迟疑。他记得每次他去的时候,她总是眼露惊喜之色。他想起来了,这里有一个过程。先是但丁拒绝了她,她的倾诉夹杂着泪水和鼻涕,然后她悄悄地置身在沙发上,紧紧地贴近了他。她要将舌头伸过来,把他的手领到了她的身上。他的手像一个迷茫的孩子,来到一个山冈上。突然,一切就戛然而止。他几乎大喝一声,不。房间里的一切中了魔法一样,停止了。呼吸和尘埃。
后来他夺门而出,下了楼梯,奔了出来,上了大街。楼洞犹如火热的枪膛,他就像一颗子弹射出来似的,扶住一棵树。喘了一口气。待他喘息而定,重新进入生活,下面就意味着谎言的开始。首先是她的女朋友,那时候她总是问他,你怎么了,心神不宁的?要么直接用玉指点了点他的头,你在发什么大头愣呢!或者会这么说,你坐在这儿,魂还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呢。之后就是那个好友,憨厚的田径运动员,那是个好哥们儿。他憨厚的笑脸,总会飘荡在他的天花板上。但丁觉得他的憨厚正是对他的告诫,或许还有对自己的嘲讽。他感觉到面红心跳。谎言开始,覆盖了真相,一切循环往复。他每次去他家,总是和他喝酒。而和他的女人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既没有她的鼻涕,也没有他的惊愕。这就是生活的奏鸣曲。
可是,这一切是真的吗?还是缘于他阴郁的思想,无聊的想象?过去的生活和微薄但有力的想象交杂一起。无法剥离,难分彼此。这一切是模糊的,又是真切的。谁都知道但丁是一个耽于幻想的人,他有时候被自己所惊吓,一颗想象里的沙粒却有千钧之力。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会因为一件花衬衫而号啕大哭,还会因为一个美丽的背影、健美的小腿,而诗兴大发。这一切都是真的吗?但丁同意他那个写小说的朋友林苑中的说法,较之于小说,生活有时候真的只是一种更为拙劣的讲法。但丁已经无力记起了,他也不愿去分辨什么,他只记得清水鼻涕挂在一个不育者的鼻尖上。对了,这是关键。不育者。
他们是从这儿开始的吗?女人的叙说是从这儿开始的。她哭哭啼啼,这是大不幸。谎言继续着,他成了这个家庭生活秘密的窥探者,应该说这是偶然间完成的,但是他却必然地面对这个生活和道德难题。他的手被她的手紧紧揣住,一手颤抖激烈的汗。她告诉他,她很想要一个孩子,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家伙。她想得要命。她还说自己去查过了,问题大概出在她的丈夫身上。可是他不肯去医院检查,死活都不去。就是这样。说完,有一滴清水鼻涕来到了她的鼻尖上,悬而未决。
她说:“难道我不够漂亮吗?”当时她就是这么说的。但丁说,不,这不是一回事。她的眼神他记得清清楚楚,后来在天花板上直射着他。她妩媚动人地说,其实是一回事。然后她就消失在天花板的潮斑里……似乎但丁总是疲倦地睡去。他能给予她那一滴珍贵的精子,那一小滴黏稠夹杂着狂欢气质的体液吗?不,但丁在内心里拒绝将自己的那滴射进她湿润的体内。他要做一个背德者吗?可是天花板上的那副眼神,几乎让他又肝肠寸断。他的脚步随着他的追问,变得一会儿轻快,一会儿沉重。但丁和她的故事晃荡着一连串的“不”字,他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肉体和灵魂的搏杀。
后来但丁在他的一篇文章里如此写道:她很性感,动人,是有足够的魅力让我进入她的裙裾的。
那是一个熟悉不过的门楼,灰暗的色彩,里面几乎塞满了生锈的自行车。但丁扁着身子拾级而上。楼道里一直是黑糊糊的,充满了一股霉腥味。但丁是不能忘怀的,他记得楼道的黑暗里还传来一些孩子的嬉闹声,他们的声音在安静的楼道里产生回响,这种回响犹如来自一个美妙的子宫。就在他一直盘旋上升的过程里,他还能听见有优美的钢琴声传来。那美妙的旋律在幽暗的楼道显得异常动人。后来他在独处的时候,这一美妙的旋律就会袅袅向上,一路将他提升。他总会感到灵魂出窍,飞上了天宇。旋律慢慢地远了,就在脚下的楼梯口飘荡。事实上,他来到了她的门口。
女人果然在家,她慵懒地拖着长长的声音说来了。他等待她开门。他忽地有点紧张。双手在发汗。他能听见她的脚步在水门汀上滑过的声响,那丝款款而来的波浪。
女人拉开了门,她对他的造访似乎已经没有多大的惊喜,但还是很有礼貌地将他让进屋内。他习惯地坐在她家客厅的沙发上。沙发的对面墙上可以看见女人和他的好友的结婚照,女人披着洁白的婚纱,脸部发出迷人的微笑。他的好友偏着头,姿势和表情都略显生硬。以前来,他都要对此说上一两句,甚至有时候会逗笑女人,也就是说但丁有时候是一个俏皮幽默的男人。这次,他没有这样做,甚至没有看墙上的照片,他的视线一路越过客厅,厨房的窗口飞向了外面那一片白光。那片白光很耀眼。但丁忽然觉得自己的身体内部有一种欢腾。他甚至觉得自己犹如一根白色的羽毛飘出了窗外,在飞扬,然后轻轻地下坠。
女人给他沏好了一杯茶,然后在他的对面那张椅子上坐了下来,他闻见了空气里弥漫着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息。女人先是静静地坐着,然后就在他的面前走动了几回。如果说以前他的目光可以停留在她的额头,甚至美丽的躯体上,那么这次他无法拥有一道坦然清澈,活泼而惬意的目光。的确,这一次他的目光用胆战心惊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女人去看了窗户,或者去了洗手间。事后他明白她的走动是为了引起注意。是为了让他的目光降落在她的腹部地带:那里已有骄傲的内容。她依旧款款地在水门汀上滑着美妙的波浪,然后依旧坐在他的对面,看他喝茶。过了好一会儿,她才问,这段时间过得好吗?你好像有好些日子不来玩了。女人的声音还是那么富于磁性,她的喉间似有一个美妙而动人的簧片。但丁喝了一口茶,眼睛不敢看她,只是点了点头。
他的目光有一个小小的圆圈,在那个圆圈里,她穿了一双拖鞋,拖鞋像是几个绿色藤条编成的。他看见女人的脚指头,安静整齐地排列着,充满了贞节的色彩。她似乎意识到他的视线投向了这里,然后本能地往后移了移。他还看见了她的脚踝,她的脚踝骨从一片柔滑里突兀而起,非常性感。但丁听见自己的呼吸开始有点杂乱,他再次喝了一口茶水。
这一幕但丁是无论如何都忘记不了的,他的视线是慢慢地上升的。女人的腿白皙无比,上面还可以看见蓝色的血管。女人的两腿很快消失进了那裙裾的深处,但丁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他的目光停止了,女人的躯体显得臃肿,他明白了过来。女人的视线和他相遇了,就在客厅里,他似乎又重新找到了那次街头的那种目光。但是很快就是一片慌乱。但丁感觉到体内的热血砰的一下全部涌到了脸上。他像是受到了一场莫大的屈辱。
这就像一个秘密被揭露后的那种残酷。那种以往到来时候房间里的那种迷人,甚至那种谎言夹陈的暧昧,一下子化为齑粉,然后经不住呼吸和一阵微风,便消失了。他和她的故事就是这么结束的。但丁坐在沙发里,好一会儿他才开口说话。他像是忽然间找到一个话题,那几乎是一个美妙的借口。
他离开后不久,他又为这个借口痛恨起自己来,他忽然间觉得,女人应允的那点路费几乎把他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收买者。但丁在他那篇文章里如此写道:“那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借口,巧妙地阉割了真实。当她站起身来,来回地在我的面前走动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美丽的魔鬼有了身孕。其实她摇晃着臃肿的身躯向我的道德提出了挑战(她的眼神似乎一直在说,你不帮我,有人帮我)。我红涨着脸,在她问我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我顺口说,我想借点钱。我要前往K市。事实上我还没有抵达目的地,就蓦然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个双重屈辱。这个美丽的魔鬼啊。”
6.相会在K市
但丁终于来到了K市。他一下车先找到了他那个搞艺术的朋友,并且在那儿住了两三天,然后就离开了。他找到那儿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他的朋友正站在那儿作画,但丁的到来令他倍感意外,他将自己拮据的零钱拿出来,在旁边的一个叫金凤酒家的小饭店吃了两碗面条。他沾有油彩的指头和欢快的语气使但丁难以忘记,他对但丁说:“谢谢你来,我从来没有这么奢侈过呢。我一直对自己很苛刻,这没有办法。”这个场景后来还多次被他和但丁所提及。
他们从小饭店出来,穿过一路的灯火进入暗淡的小巷,然后到达朋友的蜗居。这间小窝的背后,就是一条铁轨。他们激烈地谈论了一夜,天快亮的时候,他们才模模糊糊地睡了一会儿。在睡梦中,火车穿过了屋后的黎明。在那两三天里,但丁感觉到他的梦境一直是剧烈地颤抖的。
他不得不选择离开。一个是他无法忍受火车在屋后的轰鸣,他简直无法入睡。在他朋友的蜗居里,那两三天的时间他的睡眠总计不超过三五个小时。这让他大伤脑筋,但丁是一个需要梦的人,他需要一个开阔的梦境,为花丛的光芒所照耀,那里聚居了他的傻子二哥,父母亲人。再一个是他的艺术家朋友那一天几根萝卜条的生活他真的应付不来。那位朋友姓刘,和他一样有着长发,桀骜不驯的脸孔。他的蜗居只有几平方米,整个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凳子,一张桌子,此外就是满目的书籍。书一摞一摞堆放得到处都是,看上去摇摇欲坠。
朋友有一张大大的画架,因为没有地方可放,画板被巧妙地钉在了墙壁上。那幅画至今还印留在但丁的脑海里,画面充斥了纷乱的色彩,犹如一个旋转的星空,漩涡一层层递进。你的目光不得不被吸了进去。这幅画几乎就对着门,一进门就能看见。他的朋友一手拿着画笔,他的形象后来被来西郊的记者描述为:门槛上的天才。在关于这位西郊艺术家的文章旁边还附了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位身体瘦削长发飘飘的年轻人正是站在门槛,手执画笔,伸向墙壁上的画作。后来这位朋友一直坚持画漩涡,他是巧妙地将行为和画作结合起来的一位艺术家。他告诉过但丁,他要一生只画一个事物。那就是漩涡。因此圈子里人都叫他漩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