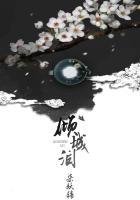向晚,我在澜沧江边散步。
落日隐藏在彼岸原始森林上方的浓云中,云罅中泻出一道道金红的瀑布,瀑布飞扬开来,染了半天的妃红。云山雾嶂宛若卸去了白沙笼包巾和蝉纱的依少(傣语:姑娘),祖露出奇绝秀丽的姿容。背光的森林和岩模模糊糊,色泽沉郁,在妃色的天幕上勾勒出清晰的轮廓;而远在下游方向的勐买山却呈溟蒙的银灰。天野里是一幅明暗强烈的奇景。晚霞透过低矮的林梢,摇碎在宁静的江波上,在两岸苍山间曲折而去的澜沧江是愈加幽邃壮丽了。
陡斜的堤岸上霞朵浮动,身穿筒裙的橄榄坝的傣家姑娘下到江边来了。肩头晃动着一双水桶,手拎彩色的塑料网包,紧裹花裙的身子苗条绰约,眼前的风景画顿时变成一幅有浓郁生活气息的滇边风俗画。
沙滩上,留下一片水桶。
依少们踏进江边浅水,拾起鹅卵石细心地擦拭脚跟上的泥巴,掬一捧水痛痛快快地洗满脸的汗垢,面容鲜亮起来,如一朵朵盛开的粉团花。纵使她们生相各异,却都有饱满明亮的额头,淡淡的弯弯的蛾眉,泉水般清澈的动人的大眸子;纤巧的鼻子和嘴唇,使清秀的瓜子脸生出几分妩媚。橄榄坝的依少是富有吸引力的,难怪有人喟叹她们是天下最美的姑娘!
一件件水红的、浅绿的、粉白的窄袖短衫零落在水边,浅排色紧身小背心也从肩膀上卸落,露出白哲细腻的肌肤,依少们将长裙束起,一边翻卷裙边,一边朝水深处走去,裙子低低地压着水面,当筒裙像花头巾一样缠在头上时,便在江波里自由自在地游戏着了。
她们就是白天我瞥见的在田陇割稻打谷的姑娘,挑着两长挂香蕉向绿荫中的竹楼走去的姑娘,行驶东方红拖拉机从路边扬尘而过的姑娘。傣家姑娘是沉静腼腆的,午后,我在曼春曼寨子的竹楼上做客,主人的女儿埋着头,为我端茶,之后,躲进里屋再也不露面。此刻,她们却那么潇洒大方,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获得了任情放性的自由。
顶在头上的花裙仿佛是波面上新开的荷莲,那么艳丽。有人解下裙子,当浴巾使唤起来,于是,澜沧江浮动起一私彩色的波涛;长发顺着浪波起伏漂泻,常年用浓浓的糯米水梳洗的头发,柔美乌亮,是姑娘们的骄傲,难怪在漂洗着的时候也带着几分悠然自得。簪在孔雀髻上的缅桂花,粉团花,桅子花随波而去,是一首音韵优美的乡土小诗;花朵儿飞快流逝,看似宁静的澜沧江水势原是很湍急的,年轻的身子在激流中浮沉,为热带阳光蒸烤的肌体毕竟有太阳的那份美丽、强健,使人想起云冈石窟、敦煌壁画中表现人体美的杰作:那些翱翔碧空的飞天、那些翩翩起舞的乐伎,那些东方艺术史上的辉煌作品……确实,自我从远处走来,便觉得面前的景象恍惚不是现实,而是神话传说中的场面。
是的,面前的景象,使我瞥见一个从远古洪荒中走来的民族。
古老的民族有古老的习俗。在酷烈的热带气候下,也许,从傣族先民在这片土地上劳动生息开始,便有沐浴的习惯。书籍上不乏有“白夷性好浴,每日必赴清流,赤身露体,洗浴身体”的记载。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每个民族总在不断地改革故俗;傣族是滇边诸多少数民族中最为文明开化的民族,如今,现代物质文明迅速地进入傣族社会,在录音机前听赞哈,从电视屏幕中了解外部世界,小伙子骑着“永久”、“飞鸽”串姑娘,姑娘撑着尼龙自动伞赴摆,在生活的剧烈演变中,他们却依然保持凌波沐浴的村野风俗。我想,不止是解热冲凉的需要吧,与丢包、对歌、赠槟榔(情人之间相赠槟榔,以表爱情的坚贞。槟榔拌石灰而嚼,嚼时满嘴血红。)一样,恐怕还表达了本民族的美好情怀和审美情趣。看这幅风俗画,使野性和文明失落了界限,你不会去感伤原始初民的生活方式,却引走对美的憧憬。
一条窄长的木槽船从山深林密的上游乘流直下,船上是四、五位赶街归来的依少,头上兜着崭新的花头巾,耳上挂着亮晶晶的钻石耳环,一条漂亮的筒裙更将她们点缀得花枝招展。船儿驶近的时候,她们站起身子,向沐浴的女伴投掷沿江采集的野芭蕉,还有集市上卖剩的柚子、木瓜;浪朵进溅,也溅起了阵阵娇喧笑语。木槽船泊岸未稳,她们便迫不及待地和衣跃入江中。依少们像森林里的绿孔雀一样爱干净,每日要在水中沐浴两、三次,她们是在澜沧江里泡大的呀!
自古来,傣族人懂得水,也离不开水。在西双版纳境内,他们世世代代聚居水滨,依仗水利之便,开垦出一片片逸满稻香、果香的坝子(山间小盆地),因此曾被称为“水摆夷”。有些山上,旱地刀耕火种的少数民族,认为水边有鬼,他们却将水视为幸福、吉祥的象征,不然,怎会有傣族特有的“泼水节”?每逢“泼水节”到来,男女追逐,水花满天,用泼水表达诚挚的爱情和新年的祝福。傣家人将澜沧江称为“难夕江”,意为母亲江,可见他们与水生死相依的特殊感情。他们的民族气质,也糅和着水的情味,虽少了些剽悍勇武,却不失优美温和,淳厚质朴,尤其是女子钟灵毓秀,给人以“娴雅如水”、“柔曼如水”的感觉。她们平时像池水一样恬静,内向里却流水般的自由,放达,无拘无束,此刻悠游于清波,如鱼得水,与其说沐浴,且不如说饱享着欢愉。她们真不愧称澜沧江的女儿。她们怎舍得离开养育自己的母亲?
对岸的景色,消淡的妃红中已渗进许多靛蓝,使奇特的山峰、苍郁的森林显得十分安宁、明净。澜沧江泻开悠长的水波,是那么闲适。景物清晰起来,树林里伸张着苍古的藤葛,钛树冠悬垂到江边;高大的野安息香在山岩上默立着,撑开一片紫气;美丽的白鹇拖着长尾巴,在凤尾竹林前飞来飞去。两位小伙子挥动长竹桨,从江心驾舟而过,用戏谑的调子唱着情歌,而浴女们只管在水中浮沉,斜卧着,或是仰坐着,无意应对。置身在如此宁谧的风景里,只能用宁谧才能领略到其中的妙处……不久,三、二浴女朝向对岸立起身来,有一位昂着头,双手举到空中剔理拖垂于水面的长发,仿佛做着孔雀舞中袅娜的摆手动作。她面部、胸部、腰部的曲线映现在余霞隐约的浪花天里,这些山峰与波涛的曲线,形成一尊风格沉静、流畅、富有民族情调的雕塑。在自然界,没有比因劳动完善的人体构造,具有更谐美、更富有生机力量的线条了,人类的审美观照最初不是由人体的美培养起来的么?
晚霞洒落的光斑终于在江面上消失,依少们出浴了。顶在头上的筒裙滴水未沾,她们渐次将裙放下,踏出水面,又将裙子束起;有的则将筒裙散开当作围帘儿,更换衣裙。水面上响起棒捶的脆响,银手镯在腕子上叮叮当当地跳荡;有人哼着歌子,从鹅卵石上采集绿丝丝的青苔菜,也有人披着及臀的水淋淋的头发,迎风而立,让风鼓扬长裙,见上游漂来野花,便捞起管到鬓边。快活得像小牡鹿一样的依因(小姑娘),在人群中踏水穿行,搅碎了倩影;白的肌肤,绚烂的花裙,在水中晃动迷离。
江天间,岭峦林莽,影影幢幢,化成淡墨色的剪影。白雾从江上升起来了,从森林里逸出来了,依少们赤着双足,细竹扁担扫逮一双水桶,聘聘婷婷的身影消失在晚暮的雾霭里。一轮月亮从江尽头浴波而出,也是水淋淋的,那么晶莹纯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