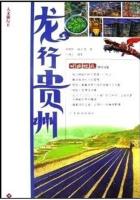我跟一群十七岁的女孩子聊天,她们问起我平时有些什么娱乐,当时我几乎愣住了:我有些什么娱乐呢?
若照一般人的娱乐标准,我大概要被归类为几乎没有娱乐的人吧?幸而,就在一般的标准之外,我仍然有着一些纯粹自我认知的娱乐。在旁人看来,那些也许根本不能称之为“娱乐”,而只是一些卑微甚而荒谬的沉溺或者自我放逐吧。然而它们确是属于我的娱乐,是我这饱受挫击的生命中的秘密的狂喜。我真心而执著地享受它们,从其中获取如肌肤般的丰腴和血液奔流般的喜悦。
提到我的娱乐竟包括了“暗中静坐”时,那些十七岁的女孩子差不多都睁大了眼睛,仿佛充满了疑惑和惊骇,同时掺杂着一种欲要探索真相的兴味。那天我恰好感冒了,头晕目眩,又没睡够觉,加上天生的言语迟钝,似乎怎么说也不能使她们心领神会我所沉溺的那个暗影生异彩的境界。我于是颇为困顿地止住了。说来说去都那么琐碎,不完整,既然无物,又何必多言呢?
后来我回想起来,即使我舌灿莲花,怕也未必能使她们洞悉其中的真意吧?我终于想通了,那根本不是语言的问题。语言在生活上虽然占着重要的地位,然而,暗影生异彩的境界,却是纵以千言万语,也难能道破其中一二的。一个人若没有经过泡沫的挥发,没有经过先作垃圾再化沉为泥土的蜕变,终其一生也未必能窥破那个一顿成圆再现无穷的境界的。
其实,不能心领神会暗中静坐的乐趣,毋宁是十七岁女孩们的一种福分,或者,该说那才是她们的一种本分。天真浪漫而且充满了梦幻的她们,时常无端端地强说愁,无端端地怒目圆睁或欲说还羞,甚至于时常无端端地疯狂嘻笑如天空中自由飞翔的快乐小鸟,她们的快乐和愤怒往往是赤纯的,可以一目了然的,而她们的所谓“忧愁”,也往往并无难以解析的实质。她们的生活本就像阳光里的泡沫纷飞,瑰丽多姿,哪知道生存的背后尚有暗影呢?
我也曾经十七岁,曾经活得喧哗多姿,曾经充满了泡沫般华丽飞扬的梦幻,而那些,终于都在生存的这条路上渐次挥发,终而远离了。如今我早已不是十七岁,且在梦幻碎落后经历了一段像垃圾般的生活。这活生生的经验,把我蜕变为一个像泥土一般具体而又不易死透的女人。
我幼时住在乡村,最能领略先作垃圾再作泥土的过程之艰辛与庄严。乡村的农家,大都有一间作堆肥的房子,他们把所有会腐烂的垃圾都堆在那无窗而仅有一扇门可供出入的房子里。所谓垃圾,其实应解释为“剩余物质”是被利用过了的一种废物。没有任何东西天生是废物,垃圾也是一样。他们把垃圾堆在一起发酵和腐烂,还得泼水和翻搅使它们腐烂得更快。谁都不喜欢走进那闷热而且充满了恶臭的房子,因为堆肥的本身在发酵腐烂的过程中是会产生高温和沼气的。过了一段时日,垃圾都已腐烂,他们就装进牛车,运到田里去施肥。到了那个时候,它们的身份和价值有了奇异的质变。它们不再是垃圾,不再是堆肥,它们化为泥土,而且化泥土为沃土,使地上的生命因而活得腰杆更直,收获更好。它们消失了本来的自己,但是它们成为能滋养生命的泥土了。在一般的价值观念里,如若垃圾也有价值,这大概就是它们最高的价值层次吧?
在我的生命发酵和腐烂的那段时期,我时常想起垃圾、堆肥、沃土之间的逻辑关系。那段时期,我承受高温和沼气的煎熬几至窒息。但是我深知更多的垃圾可以做更多的堆肥,而更多的堆肥可以造就更广阔深厚的沃土。这种逻辑关系看似十分浅显,然而蜕变的过程却是艰辛无比的。那是一种长久的窒息,是只剩一口气的苟延残喘。
然而,我自那无窗的满是恶臭的房子走了出来,在生命这片土地上寻得一处委身与就的泥土。我依赖这泥土重新滋长我自己,滋长我的儿女。更重要的是,许多过去被窒息了的欲望,又在这滋长的过程中伸出了敏锐的触角。这些触角时常在我脑海里张牙舞爪,跟我的脑子争辩。它们总是跟我的脑子说,为什么我在你的生活里长时扮演抽象的角色?为什么我不能在你生存的那方泥土上扎根成长为一种具体的生命?面对那样的抗辩,我只能说:我赖以生存的这方泥土太小了,或许,也太贫瘠了。这方泥土滋长我自己和我的儿女都还嫌贫瘠,怎能再容得下那许多欲望的触角扎根成长呢?
任何一种生命的复苏本都是庄严可喜,然而,我的复苏却产生出这样的并发症来,却也未尝不是一种苦恼。最顺遂的人生境界是无欲则刚,然而,我的欲望却是无穷无尽,我跟它们的争辩也就无时或休了。它们总要怂恿我放弃这一方小小的贫瘠泥土去作另一次开拓,另觅沃土以让它们栖身。然而,每一次的争辩,我都得作最后的妥协。我仍得在这小小的泥土上生存,仍得视它们为一种幻影。我是一个持家的女人。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是被牢固在困顿的生活里的人。我没有自由可尽情挥霍,不能满足那些欲望,只能任让它们在“不自由”的云层下游移徘徊。时日既久,伤感乃生,我的心境于是渐渐有着一种“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的凄楚了。
细究起来,这些欲望都是与生俱来,是和我的生命共存亡的。它们起先也许很小、很少,然而,岁月、情感、天象、知识逐日滋润它们,使它们渐次壮大日益增多。它们不是蝼蚁,不能一脚就可踩死;它们也不是游鱼,离水即成涸辙。它们是不死的精灵,是固执的恋人,纠缠着你,苦恼着你,却还让你感觉到生命的丰硕和甜美。我于是顿悟了,如若连这些欲望都没有,我的生命或将更为庸俗贫乏吧?除却现实里的一些残渣,闭起眼睛也许就是一无所有了!从这个比较宽容的角度来面对那些挥之不去的欲望,我对它们竟只有心存感激了!天涯觅知音,与君共生死,这偕行的路途是何其庄严啊。
我天生是一个不拘小节,不墨守成规,有时甚至也不按牌理出牌的人。从小我就向往一个比教科书更宽阔渊博的知识的世界;我向往那个静态的世界所呈现的动态世界的相貌,一如我向往整个大宇宙存在的一切伟大的事物;我向往高山大河、波涛壮阔;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和草原上的牧人;向往神游太空,伸手摘星,翻掌覆雨;向往大博物馆的阴凉、古朴、丰盛;向往原始森林的小径和荆棘。我尤其向往的是许许多多在我内心中澎湃不已的人间角色:小贩、浪人、农民、工人、推销员、艺人、精神病患、孤儿……我渴望进入他们的生活,和他们闲话家常,了解他们的爱憎悲喜。我挚爱这些坚忍或者沉默的手足同胞,他们在我内心中的地位甚至超越一个大政治家或大企业家。大政治家或大企业家的权势往往可以决定众多人的命运,但我特别关切的仅是那些依靠自己的劳力或毅力去决定个人命运的人……
我的欲望有这许多,如今我却得为卑微而繁琐的现实生活所牢固。我不能出走,不能挥洒自如地去接近那些向往已久的事物,为此我时常觉得郁闷,想从这现实的一点上破窗而出罢了!
就在这样的困顿无奈中,我终于自寻出路,和我的欲望取得了另一种妥协。白日已尽,俗缘暂失,我在暗中静坐。只见得那许多欲望的精灵都化作实实在在的生命,在我眼前歌咏不止。暗影重重,我竟得和它们玲珑相见,灵犀互通了。它们不再仅是脑中的幻影。它们是嶙峋高山,是我航行过的大海,是绿得无边无际的大草原,是故宫,是荆棘,是一群群劳动者疲乏的脸和枯涩的眼神……我不仅看见,而且我还倾听,草原风声、浪涛击岸、林中猿啸、民歌悠远、牛羊哞咩……这是一片大好风景,一片在暗影中更显得清晰的异彩。只在这时,我才真正的无虞匮乏,充满喜乐。攀登高山、乘风破浪、驰骋草原,仿佛都一蹴而就。人生至此,尚复何求呢?而这样壮观的娱乐,又有什么他物可以取而代之呢?
这样的娱乐,或许要被人讥为“只不过又落入梦幻的陷阱罢了”。而我是不在乎这些的。那些欲望,对我来说,也不会是永远的幻影。我不知何时能逐一将它们由幻影化为真实,如今我只知道在每日的暗中静坐里,我能和它们玲珑相见,灵犀互通。而且我相信在这浑噩尘世里,也有许多人俗缘半生,却也能曲径通幽,在暗沉沉的黑影里,瞧见那繁复不尽的人间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