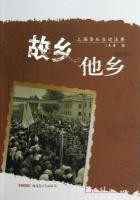我来到白桦树众多的地球上四十二年了,才第一次见到白桦树。不是油画、照片、电影上的白桦树,是生长在北国山林的活生生有灵性的白桦树。
我的心田早已种下了一棵小小的两个枝杈有着金红色叶子的白桦树,那年我还是个十七岁的扎着蝴蝶结的小姑娘,在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当舞台美术学员还没毕业。剧院演出话剧《以革命的名义》,剧中有一场戏是列宁和瓦西里在一棵白桦树旁接头。这棵小树在舞台左前侧是演员活动的唯一支点,不能用布片画成软景,须做一棵立体逼真的树,队长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
生平头一次独立进行艺术创作,十七岁小姑娘的处女作,我是怎样的虔诚和认真!我找了大量的资料,列维坦风景画集,施什金风景画集,《白桦林》、《金黄色的秋天》、《绿莲喧闹》、《白嘴鸭飞回来了》……凡是有关白桦树的画册都看个仔细,可以投入创作了。我砍下一段小叶棒的树枝充当主干,从扫院子的大扫帚上拔下一根粗苗浸在水里泡软,然后把它烤弯,就成了弯弯的枝杈。树皮,是用制作舞台纱幕的边角条儿缠绕而成,涂上青白色的颜料,再画上点点花斑。叶子,颇费功夫,先从白布上画下大小不同的叶子,一剪下来,拴在一根根铁丝上,一片一片拴到树枝上,最后再画出淡黄、金黄、火红、褐色、暗绿等等叶色……
小白桦“种”在舞台上了,灯光一打,自然逼真,栩栩如生,立即把观众带入俄罗斯原野的情调中去了。
小白桦,获得了导演、美术设计、演员、观众的一致称赞,老师揪揪我的辫子说:“好好干,你的艺术感觉很好,会有出息的。”
我很想在自己的第一件作品跟前照一张像。穷,没有照像机。散戏后,拍剧照的摄影师,给“列宁”和“瓦西里”在小白桦旁拍了一张又一张。我们学舞台美术的,命中注定一辈子干幕后劳动。再说,我只是个小小的学员,躲在侧幕后面望了又望,没有勇气走上台去站在那璀璨光圈里的小白桦旁。每天演出开场之前,我都早早地赶到剧场,把我的小白桦搬到舞台上去。大幕敞开着,观众席里空无一人。后台除了一个小工作灯,黑黝黝的,小白桦像是在暮色中幽幽闪光。我抚摸着她们,只有在这黑暗和寂静中,她才属于我。
嗳,这简直是我的初恋!处女之树,青春之树,梦幻之树,种到我心里了。
岁月的流逝,尘嚣的骚扰,浩劫,挫折,疾病,贫穷,出嫁,生儿育女,失败,一次又一次舔干伤口,名利场,人情的淡薄……皱纹多了,梦少了,心冷了,唯有小白桦,悄悄地在心灵的暗角闪着银白的光……
我的母性大于对名利的追逐,为了孩子,较少随作家们出游,每每收到笔会邀请,我都是热了一阵子,临行时又收回脚步。不知为什么,《天津文学》邀我去森林草原,我竟不顾一切拖儿带女出发了。或许,那心灵暗角的小白桦以她洁白的闪光在召唤着我?很多年了,我以为自己把她淡忘了,谁知此时她竟像《黄鹤的故事》中的黄鹤,穿透岁月的重重灰雾显出她清晰的身姿。
我来了,小白桦!终于见到你的真面目了,小白桦!久别重逢的老友?还是千里相识的新朋?熟悉?陌生?我坐在森林小火车上远远地望着她们的时候,一时闹胡涂了。只有当我靠近她,仰望她的树冠,抚摸她的枝杈时,才意识到自己心中的感觉凉奇!令人惊奇的美,难以描绘的美,无法复制的美。
我惊奇她的洁白,真像挽留住严冬的皑皑白雪。记得当初我在画小白桦的枝干时,以为是树皮总要有一些青白色或灰白色的,便调进了不少群青和灰色。现在看起来,那真是给这洁白的姑娘蒙垢了。如果不是亲眼见到,谁能相信树的家族能有这般冰清玉洁的肌体?高高低低远远近近的山岭上,墨绿色近于发黑的松林中,亮着一道道耀眼的闪电,一把把闪光的银剑,一盏盏明亮的水银管灯,点亮了莽莽苍苍、沉郁冷峻的北国山林。哪里有白桦树,哪怕是手指粗的幼树,哪里就有了夺目的高光点。哦,森林的闪电,森林的银剑,森林的明灯,森林的高光点!
我惊奇她的秀美,水灵灵犹如出浴的少女。纤细的嫩枝儿是那样柔弱,山风微微一吹,便颤栗着摇摇摆摆,一副病西施醉美人儿的娇态。无法相信威严肃穆的大兴安岭能够生出这般柔弱聘婷的丽质,又怎能想象她们是如何顶住一年中长达九个月封冻期的朔风寒流的?尤其她那翡翠雕成的绿叶,叫我目瞪口呆——叶子!叶子原来这般玲珑小巧!可是当初我给我的小白桦缀上的叶子,竟是按照小叶杨树叶的大小制作的!失真,粗糙,经不住推敲的处女作呀,我竟洋洋得意了二十多年!观察生活,长期的仔细的观察生活,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终生的功课。白桦树叶沙沙地响,她悄悄地对我絮语,我听见了上面的话。
我惊奇她的挺拔,笔直的树干一点也不亚于刚劲的青松。白桦和青松并肩而立。竞相向高空射去,竞相向太阳奔去,同是一副刚直不阿的铮铮铁骨。大兴安岭的土地是贫瘠的,山上只有尺把厚的土层,往下即是灰白色的沙石层了。真不知这样薄薄的一层土,这样短短三个月的春光夏日,白桦和青松怎么能够生长得如此挺拔茂盛?看来,他们需要的极少极少,献出的却很多很多。强大的生命力,自强不息的独立性格,似乎专门挑选了这个艰难的生活环境。京城温柔繁华之乡,温室精致的花架上,没有她的身影。热闹的花展,名贵的盆景,客厅里的小摆设,她都显得不可雕琢造就。于是,评奖啦,选美啦,国花国树市花市树啦,当然没有她的份儿。她也愿意变成木器家具造福于人,但加工时稍不顺应她的个性就宁折不弯。嗳,姿色绝伦的白桦呀,只肯自由自在散散淡淡高耸于北原幽谷、边陲野岭。其品其格其洁其傲,令人可钦可叹!
我们来到了一个叫伊图里河的地方,这里的白桦林格外繁茂,密密匝匝满山满坡。相比之下,松林极少;有松树也是些未成材的幼林。我问这是怎么一回事,主人痛惜地说:“这是一片过伐林。”经过解释,我才知道“过伐林”就是砍伐过分的林子。果然,仔细一望,山坡上到处是青松树墩,光秃秃,黑糊糊有的已经发松了。林业工人管这些树墩叫“山神爷的供桌”不许坐在上面。更不许踩在上面,一派恭敬虔诚。可是,满山遍野“山神爷的供桌”太多了,人类是怎样怀着恭敬虔诚向大自然“上供”的呀!大自然发怒了。严酷地惩罚滥伐森林的愚蠢行为,这里很快就要变成荒山秃岭了。小白桦,小白桦站出来了!主人们说,哪里有过伐林,哪里的白桦就飞速生长,小树很快地蔓延覆盖。个中奥秘,实在弄不清楚。噢,怪不得眼前的白桦林如此葱茏茂密!闪闪发光的小白桦挨着挤着列队林立,组成高举绿色旗帜的仪仗队,遮掩了青松哥哥的残躯,保护了山林母亲赤裸的胸脯。哦,小白桦,山林母亲的女儿!待到大兴安岭八百里冰封,积雪不化,山川大地一片洁白,白桦也抖落掉绿裙,裸露出洁白的肢体。归于雪山,隐于雪原,加入到百色归一的纯净中去。到那个时候远远望去,你再也看不清哪里是山川,哪里是白桦,她和白色的大兴安岭浑为一体了。
你见过白桦树的血么?不是人们常把树的绿汁比喻的“血”,是和人的鲜血不差分毫,殷红殷红的血。我头一次看到她流血,惊骇得失声大叫。前面几棵洁白的树干上,拦腰有一道道血红,在阳光下发出刺眼的血色。对于我的大惊小怪,主人解释:“白桦树只要被剥了皮,就是这个样子。”我问人们为什么要剥她的皮,主人淡淡笑道:“为了烧柴时当引火儿,桦皮晾干了很好烧。”我追问:“剥了皮的桦树还能活吗?”得到的回答是:“顶多三五年就死了。”主人见我们如此痛惜,又安慰说:“树,多得很哪!”人类往往破坏自己热爱的东西,又往往能够自圆其说,自行麻木。后来,我们沿着森林公路前进,几乎到处都能见到白桦树的血,也就见怪不惊。通过白桦幼林的缝隙,可以望见一截截“山神爷的供桌”。需要几百年才能长成的原始森林,大片大片地消失了。山岭沉默着河流沉默着,青松白桦都沉默着,或许它们在告诫着人类听不懂的语言……
当我告别森林时,热情的主人问我要不要一张桦皮,制成美丽的工艺品留作纪念。开始我表示辞谢:“不要又毁了一棵树吧!”可是,主人指着一片被推土机推过的空地说:“这里要盖房子,反正这几棵树也要砍伐的。”我太喜欢白桦树了,如果能够用桦皮制成永久的纪念品,也不枉千里此行。何况主人这么热情,何况树即将砍伐了……当我抱着桦皮告别森林时,忽然怀疑起主人说的“反正要砍伐的”这句话了,他们知道不这么说我是不会接受这件珍贵礼物的,那么那白桦树的血……唉,难道我不是和所有的人类一样,往往破坏自己热爱的东西,又往往能够自圆其说,自行麻木么……
火车在暮霭中运行,朝着更沉的夜色奔去。当我们告别山林时,山,路,松林……都模糊地隐没在黑暗与寂静中去了。只有白桦,在沉沉幕帷后面闪着幽幽银光。呵,这是舞台?还是人生?亭亭白桦,依依白桦,把我送回十七岁的梦幻中。
一九八六年十月九日写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