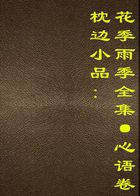公共汽车沿着乌鲁木齐至阿勒泰的公路,绕过白雪皑皑的天山,驶进了准噶尔盆地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我俯在车窗边,睁大好奇的眼睛,饱览着大漠风光、边塞景色。和万里之外的江南家乡那明丽秀巧的小桥流水柳如烟的景色相比,天山北麓的漠漠沙海,以它那壮阔的风貌,对我是很有吸引力的。瞧,那无垠无涯的大沙漠,那从沙堆里蹦出来的旭日,那远处的几峰驼影,那一行横空南飞的秋雁……像是一帧帧画幅,嵌到车窗口,陪我在沙漠里穿过了一天,两天,三天。
一天,两天,三天,每天映入眼帘的,除了沙漠,还是沙漠,一片单调的枯死的灰黄的颜色,涂抹着高天阔地,染得我的眼光一片枯黄,心儿也变得枯黄。就连我一向喜爱的桔红的朝阳,竟也似被黄沙淹成枯黄的模样。这时候,我的记忆中爆出了“纷红骇绿”、“摇黄绽紫”这些五彩缤纷的词汇,浮出了柳碧花鲜的洞庭家乡。我真盼望大漠送给我一双彩色的眼睛,让我双眼里嵌满鲜花、芳草,映进多姿多彩的画面。即使办不到这点,哪怕是送来一朵绿色的云,一片碧青的绿洲,一缕澄碧的泉水,用湿润润的绿,来揩拭我眼里和心头蒙上的一层枯黄,带来一点生趣也好啊。
第四天我睁开双眼,四顾一望,依旧是一片无际无边的枯黄的沙漠包围着。初次见识大漠风光的那种新鲜感消失了,我干脆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磕睡,任凭摇摇晃晃的汽车载我在沙漠里横渡,在枯黄的颜色中钻穿,而不愿再让它渗进我的眼睛,渗透我的心境,淹漫我的感情。
蓦地,不知是谁激动地喊了起来:“快看,绿色的太阳!”
终于,像荒芜的土地盼望种子一样,从人们嘴里播出了第一个“绿”字,立刻把全车人的睡意全都掠走,大家都振作起来,挤向西边的车窗,让眼光驰向远处的天边。
天边,不知是一片草原,还是千顷麦苗,像一座绿色的大海,绿油油地从地平线涌来,即是南飞秋雁衔来的秋意,也没有能够在那儿降落。就在这绿碧丛中,在绿色的地平线上,现出小半个快要沉没的夕阳。通常见到的落日,或是橙红,或是桔黄;前几天见到的沙海落日,则是毫无生气的蜡黄色。可是,眼前看见的夕阳却很奇怪:它留在绿色地平线上的那一部分,既没有五彩云霞簇拥,也没有暮霭烟雾笼掩,因此,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它由枯黄渐渐变成绿色,射出像草地那样绿茵茵的光辉,染得天空也绿油油的,使远天远地都变得嫩鲜鲜的,显得十分美丽。
绿色的太阳,像是一乱绿色的泉水,润湿了我们干涩的眼睛和干枯的心,润湿了我们干涩的喉舌和子涩的感情。车上的旅客活跃起来,车厢里响起了兴奋的话语。
“真怪!”一个跟我一样初次来边疆出差的广东同志,像是问别人,又像是问自己,“红太阳到了阿勒泰这地方,怎么就变成了绿太阳呢?”
“告诉你吧,同志”和他并肩坐在一起的,穿一身旧军装的汉族老同志,拍着那广东来客的肩膀,风趣地说,“一九五○年我们进军新疆解放阿勒泰以后,就留在原地办军垦农场。那一片绿油油的,是我们农垦战士在戈壁沙滩上开垦出来的麦田瓜地。那太阳是让麦苗瓜叶映绿的!”
“大叔,您说错了!”一个带上海腔的年轻人,一定是支边青年,笑着说,“那一片碧青青的,是我们开垦种植的苹果园、葡萄园,太阳是经过苹果林、葡萄架下的时候,叫我们的果树染绿的!”
坐在年轻小伙前面的一个穿绣花连衣裙、带银饰羽翎帽的哈萨克姑娘回过头来,不服气地笑着说:“那一片绿得无边的,是我们把乌伦古河的水引进沙漠,撒下种子,让沙漠变成的大草原。那太阳,是让我们的渠水浸绿的,是让我们的草原渗绿的。”
“你看,那太阳露出的小半边,圆圆的,绿绿的,多像我们瓜田里的一只露出绿叶来的大西瓜哟!”老农垦战士没加反驳,却用一个新颖的比喻,在坚持自己的意见。
“我看,像我们果园里一棵枝叶茂盛的果树的浓荫。”支边青年马上用另一个新鲜的比喻,来支持自己的说法。
哈萨克姑娘很聪明,也说出了自己的想象:“你们看,那太阳像不像一座架在草窝里的牧民的绿毡篷呀?”
“你们说的都对。”一个干部模样的维吾尔族中年男子,沉思地微笑着说,“是我们几个民族团结一起,建设边疆,给沙漠披上了绿衣。那一片绿色,是我们的青春染绿的。那太阳是感染了我们的思想才变绿的。”
从一本科普刊物上,我曾经看见过一篇文章,介绍过奇异的“放绿光的太阳”的自然现象。那篇文章上说,早在六千年前建造的埃及金字塔里,就画着向四周发射绿光的太阳,而在一百多年前,一艘名叫“晨星号”的纵帆船,在太平洋上航行的一个傍晚,也看见了绿色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