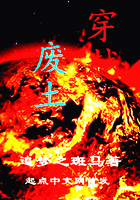又一日天高云淡,光影斜疏,总督府后院一座精致的小园中,一白衣黑发小胡须的文士正以书覆面,悠闲的小憩,此人在躺椅上懒懒晃脚,俨然很享受,正是做了两天总督府公子门内清客的长空孔常先生是也。
虽然才来两日,总督府许多人都知道孔常如今可是庞公子门客中炙手可热的人物,刚来就被奉为座上宾,单一人住在这么个独立静雅的小圆子,地位就非比寻常,下人们不敢怠慢,都尊称一声孔先生。
昨日庞敬宇带了最近作的几首诗文去给他奶奶请安,老太太一见宝贝金孙也能静下心来舞文弄墨一番,就欢喜得合不拢嘴,不知内情的以为整天斗鸡走马、逍遥散漫的庞大公子开始务正业了,他周围那几个跟班随从却晓得这都是孔先生的功劳。
是以长空姑娘孔先生近日来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好不潇洒自在。整天最喜欢的事就是抱一本书躺在榕树下,下人们都以为她好学上进,勤勉不辍,其实长空不过是帮墨煞打掩护而已,那厮不知得了谁的忠告对自己寸步不离,长空只得选了这座有着巨大荫蔽榕树的园子居住,以防某个不协调的黑影吓坏在此战战兢兢的庞家下人。
不错,战战兢兢。下人们表面恭敬,背地里却对孔常嗤之以鼻,认为此人乃十足的书呆子兼谄媚者,非必要事件绝对能离她多远就多远。原因无他,只因孔先生爱文如痴,随时随地能和你探讨诗词歌赋,经书史卷,满口之乎者也,之兮哉也。下人们大多都是不识字的,每天杂务繁多,谁有心情与你孔大才子论文评诗。
开始大家都委婉拒绝,后来孔先生变本加厉,无论什么都用文言,诸如“水兮何在?”“饭兮上否?”“尔等且驻足一听,吾方得一诗。”“此衣过华,汝岂不识吾之装乎?且换哉!”此类。下人们忍无可忍近乎崩溃,又因着庞敬宇的宠信不敢过于表露,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在此处做哑巴做聋子,做事的动作比在他处不止快了一倍。
本来众人都以为庞大公子也不能幸免于孔先生的之乎者也的荼毒,没想到庞敬宇一来,孔先生平素的高傲神态立马消失,面对庞公子的是一张笑的恰到好处的脸,谦卑不失风骨,侃侃而谈间哪还有晦涩难懂的文言文。
此时众人才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情,原来又是一个巴结逢迎两面三刀的小人,不免更加鄙夷,于是乎如今长空身边五丈之内无半丝人影,甚至有时想使唤人都找不着。
感受着沉静舒凉的四周,长空眼中金光闪亮,甚是满意。别看她一副悠闲的样子,其实这两天她也憋得慌。要不是庞敬宇身边那个高壮小厮赵洪谨慎小心,安排人来监视自己,她也不至于整天装豆腐儒酸秀才。
伸手拿下脸上的书,长空闲闲坐起来,眼梢轻弯,眼眸迷蒙,恰方从午后梦中醒来。偏头看看略略偏西的日头,合上书起身往大榕树边一间简朴的房子走去,打着哈欠咕哝着什么,素白的身影慢慢掩在门扉后。
此处园子地势开阔,虽是园子却无围墙,只有矮矮的一圈木栅,园内光景谁都能一览无遗。五丈开外的府卫仆人都知道,这是孔先生要补眠了,大概有些才华的人都有些怪癖,这人就喜欢在别人午睡时在树下看书小憩,午后便要回屋补眠,连庞敬宇都知道他的日间作息,所以午时到申时都不会来找他。下人们当然巴不得他时刻睡觉,故而也无人过多关注。
屋子虽然简朴,但却也应有尽有,外间会客,内间歇息,内外间放一拦墙而隔的阔大屏风,从外面看隐隐约约看不真切。
长空将床帏弄散,素帐轻垂,隙开些许小缝,清布简绣着几只翠竹的被角露出来,床尾帷幔显出一只脚的轮廓,两日来大家都知道孔先生睡相极差,这障眼法倒也好做。
迅速换好昨晚墨煞找来的婢女的衣服,稍微整整面容,便悄无声息从后窗翻出。
这个时辰,日光微醺,正是令人昏昏欲睡的时候,防守也相对松懈。要找到朝廷正二品大官的罪证,着实不易,蛛丝马迹还得先和章素卿见一面才能细究。根据墨煞先前探查,长空早已将那张路线图烂熟于心,要说长空还有值得骄傲一下的长处,就数她过目不忘的本领了。
西跨院后面便是总督府的一处花园,虽栽种繁花,但女眷们都居于东边,故而人迹稀少。
长空穿过雍容的牡丹丛,绕过几棵矮树,停在了一片紫兰色前。明媚暑光下,蓝兰色的形似轻飞之燕的花朵更加色泽鲜亮,纤细笔直的青茎上绽开三四朵魅惑的紫色,蕊中泛白,似燕子白腹,正是泻火止痛的好药,飞燕草。
轻轻连根拔起一大把,长空起身走出花园,穿过清水回廊,走上高岩桥拱,过门庭,绕假山,曲曲折折,环环复复,最终走进了总督府深处一座院墙高筑,看似与其他居处无异,实则戒备森严,守卫繁多,寂静沉暗的院子门口,院门口上书四个方正的大字,苟惑慎勤。
总督府的人乃至整个凌州都知道,庞博有一处庄严堪比祠堂的院子,专为晨昏自省自律,名曰:苟勤院。百姓都深感父母官的深明大义,德貌高阔,很是敬重这位方正勤勉,严于律己的总督大人,就连华皇似乎也是知道的。
是以此处附近几乎无一个闲杂人等,安静得连苍蝇的声音都听不着。
看着这四四方方,高墙尽卫的苟勤院,长空心中冷笑,表面功夫做得不错,民心尽收啊!安淮水线修了一年多,还在向朝廷要开支,眼前的院子的价值怕是还不止修好一座安淮水道大堤,再看这铺张奢华堪比一座行宫的总督府,只有四个字,虚伪,作死。
院子门前值戍的侍卫看着低头快步而来的丫鬟,如狼一般的目光更加严厉,握紧手中的红缨长枪,在那人及近之时,嚓一声,交叉横架,随即厉声呵斥:“何人在此?”
丫鬟紧张的抱着胸前的一捧蓝紫色的花,胆怯的抬起头来,满眼都是害怕的神色,随即她将手往前推了推,示意侍卫们看,然后用蚊子一般小的声音说:“奴、奴婢是、是来为里面的人送药的。”说完又极其害怕的低了头。
“那你的药呢?”
又小心的将手里的花往前推了推,丫鬟小声回答道:“这是飞燕草,可泻火止痛治腹泻。方才前院庞管家说这里有人腹泻不止,让送点药过去。所以奴婢就过来了。”许是不那么怕了,丫鬟说话顺溜多了,也清楚多了。
那问话的侍卫本是例行公务,总督大人亲自交代过,无论谁来都要盘查讯问的,眼前这女子文弱胆小,想必也翻不出什么浪来,更何况里面确实有一人从昨夜就开始腹泻,庞管家也吩咐过有人会来送药,却没想到是这种药,想来是庞管家没有给银两买药,这小丫鬟只得自己找些野草来了,这种事情也是见怪不怪了,谁让里面的人不能放还不能杀。
于是那侍卫检查了下那花没问题,便挥挥手,长枪收回,显出一条狭窄的通道,那丫鬟怯怯行了礼,便抱着那捧花跟在带路的侍卫后面快步走了进去。
不管后面跟着的两个人,长空低着头打量着四周,正房大门紧锁,四周也都是和门口侍卫一样的守卫,看似闲散的站在四周,却都有意无意的成合围之势将院门右边的偏厢圈住,长空正是要进这偏厢,暗暗记住各方守卫的数量和分配,便听见前面带路人开锁的声音。
如此精心细致的布置,与外面丝毫不同的长缨侍卫,看来此次是下了必杀的决心了。
进了偏厢,虽然也守卫森严更甚,那三人依旧若有若无的将长空围在中间,带着她来到已经与众人隔离开来的腹泻得下不了床的人床前。
好在长空虽然毫无内力,但洞察力极佳,隐隐听见几声议论,或急切或愤慨,想必是其他监察官员。
“赶紧给他治,治完了赶紧走。”
“是是,不过能不能给我一只碗,一个勺子,一盆清水,用来捣药。”
话刚说完,三样东西已经放在了床边的小桌子上。
长空也不多说,将紫蓝色的花全部摘下来放在桌子上,把带着些微泥土的根全揪下来,不错,是揪,方才不费吹灰之力就连根拔起,没想到花茎不粗却异常柔韧,长空只能使劲用手把它弄下来,用水洗净之后,开始用勺子在碗里碾烂直到将内部的汁水全部弄出来,去渣加花再碾,忙活一阵之后,一碗深绿透着幽蓝的止痛去火腹泻药就出炉了。
有植物特有的香味轻轻飘散,不过卖相嘛,连旁边那三个人都有些不忍直视,这玩意儿真能治病,不约而同的看向床上那人,面色发白,嘴唇干裂,眉头纠结在一起,额头密布冷汗,显然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不过这倒不算什么,接下来才是真正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