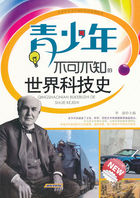野餐前一天晚上,星期一,玛莉拉一脸烦乱地从她的房间出来了。
“安妮,”她对这个小人儿说,这个孩子正坐在一尘不染的桌前剥豌豆,嘴里还唱着《黑尔兹谷的奈莉》,精力充沛表情丰富,这模样显然不是戴安娜教的,“你见过我的胸针吗?昨天晚上从教堂回来时,我把它别在针垫子上了,但现在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我……下午您到互助区去时我看见它了,”安妮慢腾腾地说,“我路过您房间,看见它在垫子上。”
“你碰它了?”玛莉拉严厉地问。
“嗯,”安妮说,“我把它摘下来别在我胸前,想看看它看上去怎么样。”
“这可跟你没什么关系,小姑娘多管闲事太糟糕了。第一,你不该进我的房间;第二,你也不应该动不属于你的东西。你把它放在哪儿了?”
“哦,我把它放回桌子上了,都没超过一分钟。真的,我没想多管闲事,玛莉拉。我没想过进您的房间试一下是不对的,但现在我明白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这对我来说,是件好事,我以后就不会重犯了。”
“你可没放回去,”玛莉拉说,“胸针没在桌子上,你把它拿走了,安妮。”
“我放回去了,”安妮飞快地说,但玛莉拉以为这是种反抗,“我只是不记得我是否把它别回垫子上了,还是放到瓷器盘子里了。但是我肯定放回去了。”
“我再回去看看,”玛莉拉说,决心做得公正些,“要是你放回去了就应该还在,要是不在了,就是你根本没有放回去!”
玛莉拉进了她的房间,彻底地搜查了一遍,在桌子上和任何一个她想可能会找到的地方都找过了,但是没有。她回到厨房里。
“安妮,胸针不见了。根据你的话,你应该是最后一个见过它的人了,现在,说说你做了什么吧,我要听的是真话。你是不是拿出去玩儿,然后又把它弄丢了?”
“没有。”安妮严肃地回答,直直地迎着玛莉拉愤怒的目光,“我没有把它拿出房间,这就是真话,肯定中间出了什么问题,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就这么多了,玛莉拉。”
安妮的“就这么多了”原本只是想强调她的声明,而玛莉拉却把它当成了蔑视的表现,“我知道你在撒谎,安妮,”她一针见血地说,“我知道。那就别说什么了,除非你打算说出真相,回你房间去,你想说的时候再下来。”
“带豌豆吗?”安妮温存地问。
“不用了,我自己剥。你按我的话做就行了。”
安妮走了,玛莉拉开始着手做她晚上的工作,心里很不放心,她在担心她那无价的胸针。万一安妮把胸针弄丢了怎么办?这孩子否认拿走了胸针,简直是太可恶了,明明别人已经知道是她拿的了,她却还是那一脸无辜的样子!
“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玛莉拉一边心神不宁地剥着豌豆,一边想,“当然啦,我不会以为她是想偷这胸针的,她不过是拿去玩玩儿,帮她幻想一下罢了。但也很清楚,她的确拿了,按她说的,她在房间里时,那儿连鬼也没有一个,然后就是我上楼去了。胸针不见了,这已经肯定了,她不敢承认,因为怕受罚。太可怕了,她竟然说谎,这比她发火还要糟糕,屋里有个根本不能信任的孩子太可怕了。狡猾,不可靠,这就是她的表现。我觉得这比那胸针更让人不放心,要是她说了实话,我根本就不会这么生气了。”
玛莉拉整个晚上不得安生,每隔一会儿就跑到房间去看看,但还是没有找到。上床时间到了,到东山墙一趟,也没有什么结果。安妮坚决不承认,但玛莉拉反而倒更确信是她干的了。
第二天一早,她把整件事情都告诉了马修,马修震惊得晕头晕脑,他没办法这么快就不再相信安妮,但是他也承认这情形对她不利。
“你肯定没掉到桌子后面吗?”这是他唯一能提的建议了。
“我把桌子移开过,而且把抽屉都拆下来看过,甚至连每道缝隙都没放过,”玛莉拉肯定地回答,“胸针不见了,就是这孩子拿的,她在撒谎。这很清楚,丑陋的事实,马修·卡斯伯特,我们还是正视事实好点儿。”
“嗯,那你打算怎么办?”马修一脸孤绝,心底庆幸是玛莉拉,而不是他要处理这事,这次他一点儿也不想介入。
“她要是不承认的话,就待在房间里吧。”玛莉拉冷酷地说,她想着这个办法上次已经成功了,“然后再看看,要是她告诉我们拿到哪儿去了,或许我们还能找到。不管怎么说吧,应该严厉地惩罚她,马修。”
“好吧,得好好惩罚,”马修拿起帽子,“我不管这事,记得吧,你自己不想让我管。”
玛莉拉觉得所有人都背弃了她,甚至想听听林德太太的建议都不行了,她冷着脸上楼,下楼时脸色更严肃了,安妮依然拒绝承认,她声称她没拿胸针。这孩子显然哭过,玛莉拉压抑着自己的痛惜,到了晚上,她决心,用她的话说,就是“搞定”。
“安妮,要是不承认的话,你就永远待在这儿吧,你可以做个决定。”玛莉拉坚定地说。
“但明天要野餐呢,玛莉拉,”安妮哭着说,“您不让我去吗?您就让我下午去吧,好吗?之后随便您让我待多长时间,我都会高高兴兴地待着的。我得参加野餐呀!”
“你哪儿也不许去,直到你承认,安妮。”
“哦,玛莉拉。”安妮喘着气说。
但玛莉拉走了,关上了门。
星期三的清晨,晴朗而明亮,如同为野餐特意定制的天气。鸟儿在绿山墙上歌唱,花园里的圣母百合散发出缕缕清香,携着风穿过每扇门、每扇窗,如同善意的精灵般在房间、厅堂里逗留游荡。山谷里的白桦树像每个早晨一样,远远地挥舞着手招呼安妮,但是安妮不在窗口,玛莉拉端着早餐上楼时,发现安妮正呆滞地坐在床上,脸色苍白而坚定,嘴唇紧紧闭着,眼睛闪闪发光。
“玛莉拉,我决定承认。”
“哈!”玛莉拉放下盘子,她的办法又一次成功了,但这种方法也让她痛苦,“那听听你准备说什么,安妮。”
“我拿了紫水晶胸针,”安妮像背书一样,“就像您说的那样,我拿了它。进屋时我没想拿走的,但是玛莉拉,它很漂亮,我把它别在胸前,我抵抗不了它的诱惑,我想象要是把它戴到野餐会去该带来多么兴奋的颤抖啊,我假装自己是凯迪莉娅·菲茨杰拉德,戴着紫水晶想象自己是凯迪莉娅小姐就容易多了。戴安娜和我戴着酱果当项链,但酱果哪儿能跟紫水晶比呢?所以,我就拿了那胸针。我想我可以在您回家之前放回去的。我在路上闲逛的时间太久了,我走到阳光水湖桥上的时候,把胸针摘下来了,又看了它一眼。噢,它在太阳下的光芒啊!然后,我侧着身子过桥,它从我的指间掉下来,掉下去,掉下去,闪着紫色的光芒,永远地沉到了阳光水湖底。这是我承认得最漂亮的说法了,玛莉拉。”
怒火再次在玛莉拉的心底澎湃,这个孩子拿走了她心爱的胸针,丢了它,现在她却平静地坐在这里背诵每一个发生的细节,脸上没有一丝悔意。
“安妮,这太可怕了,”她努力让自己平静些,“你是我认识的最邪恶的孩子了。”
“是我的话,我也这么想,”安妮镇定地同意道,“我知道我得受罚,这是您的责任,玛莉拉。您立刻就来吧,因为我想了无牵挂地去野餐。”
“野餐,真的!你今天不能去野餐,安妮·雪莉,这就是对你的惩罚,这可还没有你做的事情一半严重!”
“不能去野餐?”安妮跳了起来,抓住玛莉拉的手,“您答应过让我去的!玛莉拉,因为我想去,我才会承认的。用其他什么方法来惩罚我吧,但别这样,玛莉拉,求您了,求求您,让我去野餐吧,想想那冰激凌呀!不管怎么样,要是不去,我可能再也没机会尝冰激凌了。”
玛莉拉冷漠地推开安妮像粘胶般的双手。
“你用不着求啦,安妮,你不能去,就这么决定了。行了,别说了。”
安妮明白了,她说不动玛莉拉的,她紧紧地揪住自己的手,发出刺耳的尖叫,然后,脸朝下扑倒在床上,绝望地哭叫、翻腾。
“主啊!”玛莉拉喘着气从屋里跑出来,“这孩子是疯了,没有哪个孩子会像她这样的。她要是没疯,那就是个坏孩子,噢,天哪,我怕雷切尔开头就说对了,但是再艰难也得往前走,不能回头看哪!”
这是个阴沉凄凉的早晨,玛莉拉拼命地干活,等她觉得没事可干时就开始擦洗走廊上的地板和牛奶场的架子,其实根本没必要擦,但玛莉拉这么做了,然后她又跑出去耙地。
午餐做好了,她上楼叫安妮,一张泪水斑驳的脸出现了,悲惨的目光穿过楼梯扶栏。
“下来吃饭,安妮。”
“我不想吃什么午餐,玛莉拉,”安妮呜咽地说,“我吃不下。我的心都碎了。总有一天,您的良心会自责的,因为您打碎了我的心,玛莉拉,但是我会原谅您的,记住吧,到时候我就会原谅您了。但请您别叫我吃什么东西,特别是煮肉、蔬菜啦,苦恼的人觉得它实在是太过平庸了。”
玛莉拉被激怒了,她转身回到厨房,把安妮悲伤的故事全倒给马修听,马修呢,则成了个处于正义感和对安妮不合法的同情之间的伤心人。
“嗯,她不应该拿胸针,玛莉拉,还有,不该撒谎,”他悲哀地目测着一盘子平庸的猪肉和蔬菜,就像他也觉得这菜不适于情绪危机似的,“但她这个小东西,这么有趣的小东西。你不觉得她这么想去野餐,不让她去太过严厉了吗?”
“马修·卡斯伯特,你实在让我吃惊。我觉得你太轻易放过她了,她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做得有多坏,让我有多难过。要是她有一点觉得抱歉,都不至于这么坏。你好像也没意识到呢,我看得很清楚,你在不停地为她找借口。”
“嗯,这么个小东西,”马修无力地重复着,“应该宽容一些嘛,玛莉拉,你知道没有人教过她。”
“好了,现在有人正在教她。”玛莉拉反驳道。
她就算没说服他,也让他沉默了。这顿午餐很沮丧,唯一有点儿快乐的就是杰里·布托,那个雇用男孩,玛莉拉把他的快乐当成了人身侮辱。
玛莉拉洗完了碟子,把抹布放好,喂了母鸡,想起来她那条最好的黑色缎带披肩上裂了个口子,她星期一从妇女缝纫小组回来就把它放起来了。
她要去补补,披肩就在她箱子里的一个盒子里。当玛莉拉把披肩取出来时,穿过藤条的阳光从窗口透进来,被披肩上的什么东西反射回来了,闪烁出不同方向的紫色光彩来,玛莉拉一把抓住它——啊,是那个紫水晶胸针,它的钩子挂在一线流苏上。
“我的天哪,”玛莉拉茫然了,“这是怎么回事?胸针好好地在这儿,而我却以为它在巴里池塘里,这个女孩说她拿走了弄丢了是什么意思?绿山墙有鬼了,我记得,星期一下午我把它摘下来,放在桌子上一会儿,可能就这么钩住了吧,天……”
玛莉拉拿着胸针到了东山墙,安妮正一个人坐在窗口伤心地哭。
“安妮·雪莉,”玛莉拉严肃地说,“我在黑披肩上找到了胸针,我想知道今天早上你的胡言乱语是什么意思?”
“您说我不承认就不让我去,”安妮倦怠地回答,“我想去野餐,所以我就得承认。昨天晚上我就想好怎么承认了,还得尽力把它编得有趣点儿,我一遍一遍地说,好让自己不会忘记,但您还是不让我去野餐,所以那番功夫算是浪费了。”
玛莉拉笑了起来,但良心却刺痛了她。
“安妮,真是想不到!但是,我错了,我现在明白了。我不应该怀疑你的话,我不知道你在编故事啊。当然,你也不应该承认一些你没有做过的事,这样做太不对了,但这是我逼的。要是你肯原谅我的话,安妮,我们应该再次公平点,现在,准备去野餐吧。”
安妮像火箭一样飞起来了。
“噢,玛莉拉,这是不是太晚了点儿?”
“没有啊,现在是两点,他们应该还没组织好呢,还有一个小时才喝茶,洗洗脸,梳梳头发,穿上外套。我把篮子替你装满,这儿有不少烤制食品呢。我让杰里把马车套起来,把你带到野餐地去。”
“噢,玛莉拉,”安妮欢呼着飞奔到脸盆架边,“五分钟前我还那么悲伤呢,我真希望自己从来没有生出来,现在呢,连天使要跟我换个位置我都不愿意!”
这个晚上充满了快乐,安妮回到绿山墙时已经完全累垮了,充满了无法形容的喜悦。
“哦,玛莉拉,真是滋味妙极了,滋味妙极了这个词我是今天才学会的。我听见马丽·艾丽丝·贝尔用过它。是不是印象深刻?每样东西都那么可爱。我们喝茶,然后哈蒙·安德鲁斯让我们六个人一条船,简·安德鲁斯差点跌下船。她斜靠在船边想采水百合,要不是安德鲁斯先生恰好抓住她的腰带,可能就被淹死了,我真希望那是我,差点儿淹死真是一种浪漫的经历,可以讲一个令人颤抖的故事呢。我们吃了冰激凌,噢,真是难以形容的滋味,极度美妙的。”
那天晚上,玛莉拉拿着装袜子的篮子告诉马修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我愿意坦白承认,我犯了错误,”她直率地得出了结论,“但是我学了一课,想到安妮的招供我就想笑,尽管我真不愿意相信这是个虚构的故事,这个故事没那么坏,不管怎么样,这责任得我来负。这孩子的有些方面真的很难理解,我相信她长大后会好的,但有件事是肯定的,她待在哪儿,哪儿就不可能沉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