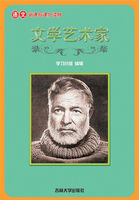八月的日子越来越少,小夏和小秋的上学费用仍差一大截。那天,他们去了学校。班主任和校长都非常同情,但也无能为力,只好以学校的名义写了封信给乡政府,请当地政府给想想办法。
当父亲在烈日下奔波了三天捧着由乡政府出面借的2000元贷款回到家里,一下子仰面倒在地上,昏了过去。十天来的劳碌和心焦,使这个在太阳地里劳作了半个世纪的硬汉子也趴下了。
上学的费用还不够一个人的,八月的日子所剩无几。
没想到这天邮递员竟送来了一张汇款单,1000元。学校来的。附言栏里只有几个小字:祝贺!全体教师捐赠。父亲从床上爬起,母亲赶紧将汇款单递过去,父亲的嘴唇嚅动着,发不出声音。
费用还只够一个人的,日子不会停留,小屋里的人立刻意识到事情的严峻。三个人的目光一齐盯着床上的父亲。父亲忽地一骨碌坐起来,说:“现在只有一条路,你们也都懂事了,自己决定吧。要不,抓阄也行。”
小夏和小秋顿像两个雕塑。
像是经历了一个世纪,小夏抬起头说:“小秋,你去吧,你的学校好。”小秋也抬起头:“不,我比你年轻一岁,哥,你去吧。”
这时谁也没注意小夏一个微小的动作。他把手伸进衣袋,摸出那张录取通知书撕了个粉碎。小秋醒悟过来后一下子跪在地上:“哥!”泪水夺眶而出。
八月的最后一天,小夏带着200元路费出了门,他去南方打工。父母欠下了许多债,小秋在学校还要许多开支。八月的阳光压在十八岁少年小夏那瘦小的身上,很沉很沉。
八月的阳光下,小秋站在村头的土路旁,看着那泡沫似的尘土上一行行深深的脚印出神。
麦秆儿
刘蒂
晌午,王老师放下饭碗,来到麦场上,从那些轧过的麦子中挑选没轧着的麦秆儿。
日头火辣辣的。比日头更叫人毛焦火辣的,是昨天下午发生的一件事儿。
二愣子的小叔叔从部队探亲回来,给二愣子买了一支钢笔。那笔杆上亮亮地绕着一圈圈金丝银丝,笔帽的舌头上还刻着一条龙。二愣子在同学面前着实炫耀了一番。可是下午只上了一节课,二愣子就哭哭啼啼地告状来了:他的新钢笔丢了!
这还了得!一支钢笔虽说不是一根金条,但对这穷乡僻壤的小学二年级学生来说,也是贵重物品了,连王老师用的还是蘸水笔呢。
王老师在课堂上大发一顿雷霆,然后苦口婆心地说了许多穷要穷得有志气之类的话,还说,只要悄悄承认了,就不公布他的名字。可是一天过去了,还没有人来坦白。
中午吃饭时,王老师沉着脸,一句话也不说。忽然,一个念头生了出来,于是一推碗筷就去了麦场。
下午上课时,王老师把齐崭崭的一把麦秆儿放到讲台上,严肃地说:“看来那个偷钢笔的学生是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了。但是,我有办法查出他来。你们看,这是三十四根麦秆儿,一样长,最粗的这根是我的,等一会你们一人拿一根,谁偷了钢笔,谁手里的麦秆儿就会多出这么一截。”说着,王老师用手比画了一下那一截的长度。
教室里静极了。王老师以威严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全体学生,让他们走出教室,经过讲台时,每人拿一根麦秆儿。最后,王老师拿起自己的那根,站在教室门口。他让每个学生再走进教室,进门时,把手里的麦秆儿与他的比一下。轮到第十九个学生了,他眼神慌乱,不敢看王老师的眼睛。当他举起麦秆儿与王老师的比时,刚好短了王老师刚才比画的那么一截,有一头显然是才掐断的。他立刻哭了。
十年后,这个孩子高中毕业回乡当了老师,学生们都喊他李老师。王老师已经调到镇办小学去了,李老师接替了他,在十年前自己曾坐过的教室里教书。
这天刚下课,一个叫玲子的女孩哭着来找他,说城里姑妈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一块漂亮的电子手表丢了,上一节课还在书包里。李老师在班里严厉批评了这种行为,希望拿手表的学生主动送还。可是两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人送还。
李老师坐在宿舍的灯下,想到十年前的麦秆儿,那只拿过麦秆儿的右手颤抖起来。
第二天,他向全班学生讲了麦秆儿的故事。最后他说:“那个拿手表的孩子,你现在还小,不懂事,老师不会用那种方法让你交出来。如果你不交,老师就进城买一块表给玲子。相信你懂事以后会后悔的,你会知道怎样做才是一个真正的好人。”
讲完后,年轻的李老师叹了一口气:“这些话,也许你们现在还听不懂。”
新年的康乃馨
金光
实在说,这样的天气她坐在这儿很委屈。可委屈有什么用啊,生活就是这样艰辛,只有这样坐着,每天看着一个个人从车站走出来,站在她面前拨打电话,然后付费,她才能有收入。
她只有十七岁,这个年龄应该上高中,可不行,她得坐守这个讨厌的电话亭。自从她爸爸出了车祸,她守在这儿已经三年多了。她想,她还得继续守下去。守到什么时候,鬼知道。
现在是除夕夜,远处早已有爆竹在响了,透过铁皮房的窗口往外望去,能看到天空中不时升起的礼花。铁皮房里冷极了,她冻得瑟瑟发抖,不停地两手搓着,哈着气温暖有点僵硬的双手,但这几乎没什么作用。
她的世界就是这两个平米,一天到晚看着人来人往,每张面孔她都陌生,偶尔会有一个人在她面前停留一下,拿起放在窗口的电话拨打,然后问多少钱,她就看看计价器上显示的时间,说出准确的价格。对面的人匆匆付账,没有人多看她一眼。
母亲下岗了,弟弟要上学。母亲就把她爸爸生前经营的电话亭交给了她,自己到菜市场上去卖菜度日月。在这儿,没有人肯向她说一句多余的话。她还兼营着一些畅销杂志,没事的时候总爱低着头翻看。她从来都是轻轻地仔细翻动着,生怕把杂志翻旧了卖不出去。杂志看起来很新,可哪一个角落都有她的目光。但这会儿和往常可不一样,她异常孤单,听着远处不时响起的爆竹声,她多想锁了铁皮房回家啊。可她不能,后面每隔半小时就有一趟向东或向西的火车经过,说不定会有一些下车的人要来打电话,她得这样待着,直到最后一趟车驶过。
一对恋人从她面前走过,那女的一袭长发,紧紧地依偎在男的胸前,留下长长的影子慢慢地晃动着。她起先看的是那对恋人,等他们从她的窗口走过,她便盯着那影子看,直到影子完全从她的视线里消失。她又转回目光,搓着手,看远处不时升腾的礼花。
电话响了,是妈妈打来的。电话里传来春节联欢晚会主持人倪萍的声音:“朋友们,再过五分钟,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了,让我们期待这一美好的时刻吧!”电话里,妈妈说的什么她一点也没听到。
“你好,打一个电话好吗?”突然,一张微笑的脸出现在窗口,是一位穿着大衣的小伙子。她一愣神,立刻笑着点了点头。她想,今天是除夕夜,很多人从外地匆匆向家里赶。她故意把脸侧向一边,不去听他的声音。
电话很快打完了,小伙子放下电话,依然微笑着看她:“冷吗?”
“不冷。”她也笑笑,望着那张笑脸。
“我不信,肯定冷。”他调皮地说着,然后掏出钱包,拿出一张百元纸币递给了她。
“对、对不起,找不开。”她的确没有那么多的零钱找他,她有点抱歉。
小伙子头一抬,指着她身后的杂志说:“那我买你一本杂志吧,这样总能找开了。”
“那也找不开。”
小伙子有点为难了,踌躇了一会儿,毫无办法。
她说:“你走吧,不收你钱了。”
小伙子不好意思了:“那怎么行啊?”
“咋不行,你快回家吧,家里人等着你呢。”
小伙子沉默了一会儿,只好向她点了点头,离开了。
她重新把计价器归了零,正要抬头眺望远处的礼花时,忽然看见刚才年轻人递过来的那张百元钞票躺在电话机旁边。她一愣,立刻拿起钱,门一关追了出去。幸好,小伙子还没有走远,她一喊,他停了下来。
“钱忘记了!”她走上前递给了他。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小伙子接过钱,反复在双手中递换着。“不为什么,这是你的钱呀。”她淡淡地笑了笑,转身离开了。小伙子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消失在车站广场……
早晨,阳光洒满了车站广场。她在爆竹声中醒来,这才意识到是新年了。她打开那扇冰冷的铁皮房门,向外张望,忽然愣在了那儿:门前站着一位邮差,正要举手敲她的铁皮门。那邮差手里捧着一束正在怒放的康乃馨,递给她,然后拿出一张签单让她签字。她懵懂地签了字,邮差转身就走。她喊住了邮差:“谁送的?”邮差指着花儿说:“他没留名字。”她便去看那束花儿,发现花丛中有一张小卡片:“但愿新年花盛开。”落款是“昨夜归人”。她的头“嗡”的一声,眼泪突然顺脸而下。
这是她真正的新年,有人知道了她的存在。
这时,一位老者走过来,拿起电话。打完了,问道:“姑娘,多少钱?”
“免费,”她高兴地回答,“今天是新年。”说完,看了一眼面前的老人,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一件皮袄的折磨
聂兰锋
大年初二,是闺女回娘家的日子,大叔却从农村来了,大叔来看我父母,一进门就找,二丫头没来吗?
脚跟脚的,我就来了。
掰一掰指头,二十多年没见了。
小时候在农村,生了一场病,肚子疼得不能上课了,就由老师背着回了家。躺在院子里的蓑衣上,抱着肚子打滚儿,滚到了地上,又从地上滚到蓑衣上。
小药房的医生说不轻呢,去县医院吧。
顶用的只有母亲和姐姐,姐姐十五岁。她们轮流背着我,在她们背上我还是疼得扭来扭去,她们又急又怕,还没出庄就都歪在菜园的小路边,大口地喘气,迷蒙中,听见母亲说“来了身上”,姐姐也说“来了身上”,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只知道谁也走不动了。
正在浇园的大叔发现了我们,撂下挑子,背起地上的我就去了十里外的县医院。
医生说晚半个钟头,这孩子就没命了。医生给了一瓶蓖麻油,让我喝下去,说要灌肠。
原来我的肚子里长满了蛔虫,多得没办法了,就结成了疙瘩拧成了绳,生生想把我的“小肚鸡肠”给拱破。
姐姐还说有蛔虫从我的嘴里呕吐出来,吓死人,有一根卡在了喉咙里,是大叔给拽出来的。我记不清了,在大叔的背上就已经人事不知。当我清醒的时候就又趴在大叔宽厚的背上,身体舒坦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了。那时正是下半夜一两点钟,没有旁人在那时候走路。不是大叔,那夜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敢回来了。路经一片坟地,大叔怕我看见“鬼火”,就脱了他的汗衫子蒙住我的头,光着脊梁继续背着我走。
母亲说:“可让这丫头咋孝敬你好哟!”
大叔说:“等二丫头长大了,给俺买件皮袄就行了。”
一转眼就是二十几年,这期间,我也曾假装是城里人多次回过老家,可一次也没有去大叔家里坐。原因是没有一件皮袄带在手边。有次在街上巧遇大叔,刚说两句话,手机响了,再说,手机又响了,大叔就挥挥手,忙去吧忙去吧。
终于,七十岁的大叔拔出腿到城里来了,一进门就找二丫头。我心虚,觉得大叔是在找皮袄。直到住了一宿要走,大叔也没提皮袄的事。
大叔要走了,问,火车站多远啊?我坐火车,回去说说脸上好看。
母亲说二丫头家有车,送你回去吧。
大叔脸上一下子绽放了光彩,皱纹也舒展了许多,我得坐干部座!大叔像个孩子似的高兴着,坐在了副驾驶座上,稳稳的,腆着肚子向后仰躺着。看来大叔真把皮袄的事给忘了。大叔越是忘了,我却越是想起,像做了亏心事一样。
我坐在后座上,我是不轻易坐副驾驶座的,不安全。就在发动车的时候,仰躺着的大叔惬意地说:“二丫头啊,我今天坐在这干部座上,可比穿皮袄舒坦多喽!”
我像一个偷玉米的孩子被无情地揪出了玉米地。
我再也不能忍受皮袄的折磨,天还很暖和的时候,我就把皮袄买好了,很舒展地挂在衣橱里。
说话的工夫,一年就过去了。又一个大年初二,大叔如约而至,滔滔不绝的话语中时时透着他坐干部座的风光。可以想象这一年他在村人面前是多么的荣耀。当我兴奋地拿出皮袄,帮大叔穿上,大叔一下子话就少了,哎呀你看这这这……极不适应这从天而降的皮袄,皮袄遮住了大叔退了色的外套和他说话的欲望,老半天都沉默着。别人说什么他不插嘴好像也听不进耳朵里,然后突然作出决定,走。谁也留不住。对于我,终于可以如释重负地送大叔回家了,可是无论怎么说大叔就是不坐二丫头的车,给他打开了干部座的车门,大叔也不坐,在大家疑惑的目光中硬是自己去了火车站,那样匆忙,逃跑一样。
我知道,这件皮袄折磨完了我又开始折磨大叔了。
追踪
彭育彩
雯雯的爸爸、妈妈,像鱼儿一样,在海水里畅游。
雯雯十岁了,她觉得自己长大了,不愿再与爸爸、妈妈粘在一起。她坐在柔软的沙滩上,揉着细滑的沙子。偶尔有贝壳从沙子里滤出来,雯雯便开心得好像灰姑娘意外得到了王子的水晶鞋。
夕阳的余晖,斜照在海面上,摇曳着细碎的金光。一艘渔船像凯旋的勇士,奏着欢歌,靠了岸。
从船里走出一个男子,男子从舱里拖出一个黑黑的、厚厚的塑料水箱,水箱里有不少捕捞来的鱼儿,鱼儿活蹦乱跳的,把雯雯的目光吸引了过去。
雯雯好奇地围在船边,看男子清理船舱。
男子的手,甩出一圈漂亮的弧线。弧线消失的沙地上,躺着一棵美丽的海藻。海藻一尺来高,茎和根须是黑褐色的,泛着光泽,晶莹透亮。叶子呈枣红色,一看就让人感受到海的气息。雯雯把它捡起来,小心地洗净海泥,拿在手中把玩。
忽然,男子发现了雯雯,他惊叫一声,盯着雯雯,眼神怪怪的。
男子满脸络腮胡子,黝黑的肤色,乍看像个土匪头子,他朝着雯雯大步走了过来,叽里呱啦地说着一些雯雯听不懂的话,让雯雯紧张得不断往后退,身子直打哆嗦。
附近有个茶座,有人登台献歌,围观的人很多,雯雯急忙混进了人群里。
当雯雯和爸爸、妈妈准备返回海边度假屋的时候,男子正准备用三轮车将鱼运回家里去,一瞅见雯雯,马上开着三轮车朝雯雯这边追了过来。雯雯眼尖,发现情形不妙,赶忙拉着妈妈的手撒腿就跑。
雯雯边跑边气喘吁吁地说:“妈,有坏人!”
雯雯的妈妈回头一望,果然,背后有一形迹可疑的男子急急追来。
听说这里地痞流氓敲诈游客的事情时有发生,难道这个男子就是来敲诈的?
容不得细想,一家三口,匆匆忙忙上了轿车,飞驶而去。
差不多到度假屋时,总算甩掉了那个男子。
夜里,雯雯全身起满了红疙瘩,星星点点,状如麻疹,痒痒的,好像蚂蚁钻心。雯雯忍不住伸手去抓,结果,越抓越痒,越痒越抓,皮都破了,渗出的黄脓水淋淋漓漓地向周围皮肤不断扩散,黄脓水流到哪里,红疙瘩就起到哪里。雯雯被折腾得哎哟哎哟地哭闹,一家人一夜未合眼。
好不容易挨到天亮,去看医生,医生说,这是无名中毒。服了医生给的药,雯雯的红疙瘩还是不见消隐。经人介绍,雯雯一家准备登门拜访当地的一位名医。
刚出门,就遇见了上回的那个男子。
男子看见他们,又追了上来,厚厚的嘴唇不停地张合,叽里呱啦地说着一些他们听不懂的方言。
雯雯的爸爸挡在前面,男子跑上前来扯紧他的衣服,指着雯雯对他又比又画。
好啊!不但抢钱,还想抢人?雯雯的爸爸气得握紧了拳头。
他对准男子的鼻孔,挥手就是狠狠的一拳。
雯雯的妈妈直奔门卫室去叫保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