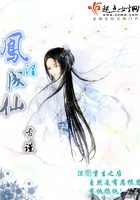秋九月,白虎郡王宫。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宫殿窗棂上的薄纱照在地上,形成一团晶黄,王后赵素心似有所觉,她扭头看向殿门方向那团日光的照影,不知不觉中出了神。
过了许久,身后的床榻上有被衾翻动之声,赵素心收回目光,扭过头来,榻上之人的目光也正好看过来。
“素心,寡人是不是错了?”金酉国主面色平静地发问,王后缓缓伸出手来,俯身替国主拢了拢散落在枕上的发丝,这才回应道:“嗯,是错了”,国主一听,叹息一声又说:“昨夜寡人走在这偌大的王宫里,突然想起沈相和大将军来,往日他们二人在朝时,国家虽有危急之事,寡人亦觉得万事皆在掌控之中,可如今,寡人竟是日夜难眠”。
王后扶了国主起身,神色郑重地说道:“大王,此次战事实乃我金酉空求国家荣耀,反倒置我国黎民于水火之中。而今远征之将士死伤者数十万,实乃国家之大不幸,当务之急,莫过于抚顺安民,使天下百姓忘却伤痛,重拾信心,其余之事可徐徐图之。另外臣妾希望大王深思本次战事,察查用人之道,摒退谄媚小人,拔擢正直之士,恢弘朝廷之气”。
金酉国主在一旁连连点头,王后言毕,国主急忙下榻着衣,也顾不得与王后共进早膳,呼了严朝忠径直向英武殿而去。
九月壬申,国相谭桓以身染恶疾之故去职。金酉国主下罪己诏,直陈罪愆。诏下,有百姓征召入伍而战殁者,每人发抚恤银百两,国库为之一空。
天星府西北方的白麟镇,这里人们的生活仍是一片祥和景致,因为地处金酉北疆,这次战事中被征召入伍从军的人数很少,绝大多数家庭的生活丝毫未受到影响。繁华大街上游人的面容也多是得意之色。从前并不起眼的白麟镇,如今的繁华在天星府也是少有的。这一切的原因,都归功于当今的国相谭桓——白麟镇是谭桓的故乡。
太阳慢慢落下山去,街上的游人也陆续归家准备晚饭,热闹的大街一时间又清静下来,恰于此时,从街口方向传来马车轱辘碾过青石地面的声音,有街边店铺的老板探出头来,却见是一辆搭着蓝色布篷的朴素马车缓缓驶来,驾车的是一个瘦小的老头,亦无甚出奇之处。于是人们又耽于自己手头的事情了。
马车缓缓驶过长街,又向右拐入街东的一条巷子里去,有两三个行人看到这一幕,都略有惊诧之色,因为这条巷子里只有一谭姓大户,正是谭桓的祖宅所在。
终于,马车停在了谭府大门之前,驾车的老者跃下车辕,在一旁掀开帘子,从车篷中缓缓走出一个身披青蓝色长袍的人,不过奇怪的是此人将自己的脑袋也隐在衣帽之中,似是不愿让人窥见自己的面目。
那人伸手从怀中摸出几锭银子给了驾车的老者,在后者的作揖和致谢声中轻轻挥了挥手,那老头也识趣,忙不跌解了套在马脖上拉车的绳子,并将马车掉头准备离去。
身着长袍的那人站立在谭府大门前,抬头凝视着有黑漆褪落的斑驳门扉,好半晌,他才拾步踏上石阶,扣响了门环。不多时,有苍老的声音从门户内传出:“咳咳,贵客稍待,这就来了”。
等在门外的人从容退了一步,拉开了自己与大门之间的距离,门扉敞开的声音随之响起,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仆一只脚跨出门来,其人笑呵呵地叨咕着:“贵客恕罪,老头子的腿脚……”,说话的声音戛然而止,这个老仆人张大了嘴,怔怔盯着来人含笑的面容,满是褶皱的双手竟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他的眼眶也微微发红。
这个全身裹在长袍之中的人,正是已辞官的谭桓,而这位年长的老者名为李双福,是为谭家辛劳了数十年的老仆。
“李叔,我回来了!”谭桓走上前去,紧紧握住了李双福的手。
“走,走,老爷,咱们回家”,李双福激动地拉着谭桓的衣袖,面上早已老泪纵横。
谭府是一座两进的院落,进了大门,正前方是带有穿廊的正厅,步行经过穿廊,出了正厅,又有一堵开了圆拱通道的隔墙,穿过这面石墙,就是谭府的居室。然而偌大的庭院里寂静无声,微风吹过,挂在屋门上的竹帘簌簌晃动,此情此景,竟别有一番落寞。而谭桓仿佛早已对此心中有数,他径直走向坐北的一间正屋,李双福用一只手拄着右腿,紧赶几步,抢在谭桓之前推开了正屋的门。
随着木门的敞开,正屋也亮堂起来,虽久无人居,但这里还是被打扫地一尘不染。屋子的上位,是一张摆放着两个灵牌的木案,上书“先考谭公讳君书之灵位”,“先妣陈母讳淑娥之灵位”,正是谭桓的生身父母。
当下谭桓整束衣裳,肃容上香叩拜,李双福也从礼附祭。
祭祀毕,李双福小心地问道:“老爷,要不要通报几位本家长老您回来的事情?”
谭桓不假思索地说:“不用了,今次我辞官回乡,主要来家里祭拜一下,或许明日我便要离开了,就不要惊动他们了”,李双福一听,急忙劝道:“老爷你上次在这府上,尚是八年之前的事了,如今难得回家一次,怎的这般着急要走?”
一阵沉默之后,谭桓长叹一声,声音低沉地回应:“李叔你莫要难过,其实这个家,在我心里只是剩下无尽的伤感罢了,他们都走了,我徒留此处,还有什么意义呢。李叔你的年岁也大了,府上的田产就给你养老用吧,而今我是用不到它们了。对了李叔,你且去备些香烛,待会儿我想去看看涛儿和梦晴”。
侍立在一旁的李双福只是老泪涟涟,他知道此刻说什么都只是徒添伤悲,遂一边用衣袖揾拭眼泪,一边蹒跚着准备祭祀之物去了。谭桓独自在灵案前驻足,他的目光穿过摇曳着的竹帘,停留在庭院西南角的一棵老桃树上。
十一年前,谭桓还只是天星府一郡下小吏,二位高堂椿萱并茂,他和结发妻子萧梦晴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夫妻二人膝下还生有一子,名叫谭逸涛,生的古灵精怪,甚是讨人喜爱。谭家家境殷实,人丁兴旺,镇上诸人俱是歆羡不已,谭桓对此也是志得意满,自感世间得天眷庇者不过如此。
然而就在当年的秋天,谭桓与友人在游山玩赏时,遇到一疯疯癫癫的道士前来纠缠,那道士硬要谭桓随了他去修行,还说谭桓命格里有孤煞星主镇命宫,注定一生要孤苦无依,一事无成,只能随了他去修行,否则便会殃及亲近之人。谭桓听了,气得只是握拳颤抖,一旁的友人连连呵斥那疯癫道士。后者见事不可为,便甩袖暂避了。
事情到此却未结束,那道士不知怎的钻了牛角,每日里盘桓在谭府左右,他不再央求谭桓随他而去,也不再纠缠谭桓,只是在路上与谭桓擦肩而过时咕哝一些神神叨叨的话语,久而久之,谭桓也就见怪不怪了。如是半年光景,那道士才从谭桓的视野里消失。
之后又过了一年,原本幸福美满的谭家竟开始连遭横祸。先是谭父傍晚外出时被毒蛇叮咬,未及救治便已离世,谭母伤心欲绝,竟于三月之后追随先夫而去。重丧累殃,谭家顿时显得冷清起来。谭桓与妻子萧梦晴也深陷悲恸,脸上失了往日的笑容。服丧半年,儿子谭逸涛没来由地身患奇痼,整日里昏昏欲睡,形容憔悴,夫妻二人遍访名医,却都束手无策。
恰于此时,那疯癫道士又找上门来,劝说谭桓随他去修行,并言唯有此法,方可解谭家之厄。谭桓本也恐惧这一切真如疯道士所定论,又处在万分悲伤急切之际,闻言擎起大棒直追了那道士二三里方才罢休。
夜半无人之时,惆怅独思的谭桓也欲听从了那道士的谶语荒议,奈何实在难以抛开桎梏。如是煎熬折磨了月余,爱子竟是夭了,经此大恸,谭桓内心懊悔不跌,却又难以申诉,脾性大变,在府里或仰天号啕,或摔杯破盏。萧梦晴痛失爱子,又被谭桓的癫狂举动所刺激,一时难以开释胸怀,竟吞药自尽了。
当谭家的长亲们赶来时,只看见谭桓抱着萧梦晴的遗体木然地落泪,当日夜半,谭桓留书一封离开了故里,连妻子的丧事也不再料理。谭府自此衰落下去,原本在府上做工的丫鬟仆人也各自散去,只留下管家李双福一人死守着这个府邸……
一幕幕前尘往事划过心头,恍惚宛如昨日,又仿佛已然隔世。谭桓长长吐出一口浊气,收回目光。
酉时许,街上已没了行人的足迹,谭桓披了长袍,携了香火,从谭府所在的深巷中走出,向北边的高山上行去。深秋向晚的天气已然显示出凛冽的寒意,田野里的虫鸣声早已消歇,四下一片宁谧中,只有一个孤独的身影在缓缓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