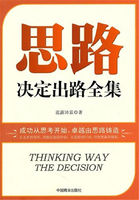符言乐如今已过了十二岁的年纪,他最近颇为高兴,这几日天气渐渐转暖,他在野外出去玩时,竟然又碰到那只奇怪的青蝉,而这只虫子好像还记得符言乐,竟破天荒直接扑落在符言乐肩膀上。“你说你到底是什么虫子啊,长得像是蝉,但看来又不是,过了一年,你怎么没有长大呢,看上去还是那样”,符言乐把青蝉抓起放到小臂上,盯着它开始了絮絮叨叨,但明显青蝉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只是掸掸翅膀,用前肢挠挠脑袋,像是在打扮洗漱。符言乐欢喜之余,带着青蝉跑到家里,寻了水果喂它吃,然后这只青蝉就赖在符言乐身边不走了,吕蕙对此只是笑笑,而符魁一见符言乐在逗弄这只虫子,嘴里就念叨:“有时间多看一点书,不要整天不学无术”,符言乐也就每天提心吊胆起来,生怕父亲看到这只青蝉。
清晨,符言乐趴坐在窗前的木桌上看书,而青蝉就在屋子里飞来飞去,好像小孩子四处翻找闹腾一般。“符二哥,出大事了!”耳边传来邻居张叔的声音,符言乐稍稍起身,就看见张言急匆匆跑去正屋寻父亲去了,符言乐也是坐不住的性子,当下也跑去正屋想听听什么事情。
“打仗!这日子好好的打什么仗?”符魁大吃一惊,这么遥远和难以想象的事情就这么突兀地发生了。张言愤怒之下,重重一跺脚,生气地说:“听人讲是南边的沉水国正在闹内乱,乱的比较厉害,国主是想借此机会抢地盘了。可恨的是咱风丞府离沉水最近,征兵的人数是九府之中最多的,今日早上镇里带来消息的人说,郡里的公文要咱镇上每户抽调一名兵勇,否则就拿银子来抵”,符魁吓了一跳,这出去打仗岂不是九死一生的事,他忐忑地问:“那多少银子可以抵去兵役?”
“听说要五十两银子,这谁他妈拿得出来!”听张言这样回答,符魁心里大大松了一口气,忽又面色尴尬地看了张言一眼,方才后一句话可不是骂了自己嘛。符魁和张言无言相对,唏嘘叹息一阵,张言起身说要去和大伙商议一下,符魁借口说一会立马过去。
吕蕙正在厨房里忙活,冷不丁符言乐跑了进来,面色苍白,神色慌张地对她说:“母亲,这下坏了,刚刚张叔说咱镇上要征兵去打仗,每户都要抽调一个人,这可怎么办?”吕蕙一听,一颗心在胸膛里扑通扑通翻腾起来。她拉了儿子,掀开帘子进了正屋,符魁正坐着皱眉愁思,吕蕙一看他的表情,方才的慌张略略收敛了一点。
“小乐刚刚说要征兵打仗,怎么回事啊?”符魁叹息一声,将方才张言的话简单复述了一遍,“五十两银子,还好还好”,吕蕙摸着胸口小声说,一旁的符言乐倒是懵了,他着急地问:“什么还好,五十两银子啊,咱家哪有这么多!”
“乐儿不要吵,咱家有”,吕蕙附在儿子耳朵旁轻轻说,符言乐张嘴惊讶地看着一脸淡淡笑意的母亲,又看看一言不发,但又不是很忧愁的父亲,顿时心里起了好大一个疙瘩……
“白谷村的村民都听好了啊,国主有谕,将起举国之兵,讨伐沉水暴虐朝廷,拯救黎民,现在王命已下,本镇每户人家须抽调一人从事兵役,这是攸利国家,建功立业的无上光荣,大家都必须全力支持。另外身体残疾之人可免除兵役,实在有特殊情形者,每户需缴纳四金,八十两银子来充抵兵役。若胆敢有自残身体或举家外逃以躲避者,以重罪论处。两日之内,请诸位自动前来镇守衙门报到,随后同去郡里编制军伍,训练军事”。
镇里来了三个衙卒来宣布此事,方才宣读公文的是居中一个看上去有点娘娘腔的衙卒,等他读完公文,白谷村全村村民顿时沸腾了。怎么又成八十两了!符魁和吕蕙站在人群中对视一眼,都为佘子青疯狂的贪婪而震惊,“喂,你回去告诉佘子青那个狗贼,若是他有胆同去战场杀敌,那咱们无话可说,否则,想从这件事上大发横财,鱼肉百姓,不妨让他小心自己的狗命!”方元彪的火爆脾气这次彻底释放开来。
“佘老狗真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黑心贼,上次咱镇上为了救困在映陶山上的人,给他送的银子加起来有三百多两,那狗贼竟只是修书一封,可笑书信还没有送出去,大伙就被澜宽的徐大人救回来了,那狗贼竟也心安理得受了那么多银子”,底下的村民对佘子青的诸般龌龊行径早已是恨之入骨,一时间骂声四起,挞伐不断。
“哼,你们,你们凭什么这样说!咱镇里至少要招募三百兵丁之数,那还不得给大伙饯饯行什么的,别人上阵杀敌,收你一点银子怎么了”,中间那个衙卒倒是牙尖嘴利,一张口便颠倒了是非,“你这个小白脸怎的和佘子青那狗贼一样无耻?郡里公文明明只要五十两银子,多出来的三十两饯行那是没门儿,装到你们自己腰包倒是肯定的”。
那人一听小白脸这个词,脸色瞬间涨红起来,他扭腰跺脚,对身旁的其他两人吼道:“你们听到没有,他们竟敢叫我小白脸,快!快去给我撕烂他的嘴!”
其余两个衙卒看来也不怎么待见他,两人互递一个眼色,竟一起转身离去了,留下一句“公文咱宣读完了,还是赶紧回去复命吧”。
“嘿,你们两个混蛋别走啊!你们等着,等郡里的大人们来了,可就没有这么好说话了”,那娘娘腔也不敢逗留,撂下一句狠话便追逐而去。
“唉,我看大伙还是各自想办法吧,八十两银子咱不理会它,可就是五十两,又有几家出得起呢,王命之下,咱们只能认命了,只希望老天保佑咱们村,大伙在战场上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杜允老人摇头叹息,大伙心里也明白王命难以违抗,当下只是暗暗骂国主昏庸,使普通百姓受苦。
符魁回到家里,坐在椅子上思索半晌,还是觉得不稳妥,“小蕙,我看咱们得想想办法。这战乱一起,天下的官兵不见能得比盗匪强到那里去,这次我能靠着银子撑过这道坎。但打仗就会有伤亡,到时候新的征兵命令下来,还是躲不过,所以咱家最好还是找个地方躲一躲,等局势安定下来了再回家里来”。吕蕙一听,也觉得符魁说的有道理,打起仗来十有八九还得继续征召兵丁民夫,符魁可是万万离不得这个家的。
“可是咱家搬去哪里呢?”吕蕙这样一问,两人反倒沉默起来,的确,一时半会根本想不到合适的办法,“好了,我们还是暂时不考虑这些了,再要征兵,起码也是数月之后了,办法可以慢慢想。你还是赶紧拿了金子,去镇里换成碎银子,准备应付这个当口才是,若是拿着金子缴去镇里,咱家可就惹上麻烦了”,吕蕙说完,和符魁来到院子里,警惕地关上木门。符魁拿了小铲子开始动手清理起埋陶罐的地方。符言乐这会本在自己的屋子里不停揣摩父母到底藏了多少银子,抬头一看父亲和母亲在院角拿着铲子捣鼓,他一下子兴奋起来,蹑手蹑脚来到院子,好奇地看着父亲到底能挖出什么宝贝来。吕蕙嗔怪地看了儿子一眼,也就没有说什么。
正屋内,看着散落在地上的一块块黄灿灿的金子,符言乐震惊地张大了嘴,他虽然对银钱没有渴求之意,但长这么大,他还是第一次面对这么多的金子。符言乐捡起一块来,拿在手上细细把玩着。吕蕙想了想,对符魁说:“拿二两金子就行了,咱家积攒的散碎银子还有二十多两,凑够五十两就可以了,明天你带了银子先去衙门看看,谅他佘子青也不敢明目张胆收八十两。从今以后咱家的日子必须过得清苦一点,否则容易招人怀疑”,“咱家日子什么时候不清苦了?”符魁笑着应了,要来符言乐手中的金子重新封装进陶罐中,一边叮嘱儿子说:“小乐你也懂事了,咱家这事对外人可万万不能提起,不然会给咱家惹祸的!还有你脖子上的银锁,那就值足足二两金子呢,你可仔细着”,符言乐一听很是惊奇,以前他只知道自己佩戴的银锁很是宝贝,但竟然值这么多钱。
……
第二日清晨,符魁早早起床,去镇里云锦阁兑了银子,未作停留便赶去镇守衙门。时间尚早,但衙门门口已排起了长队。
“你是来报名参军的还是缴银子的啊?”符魁前边的一个青年转身问,符魁苦笑一声回应说:“我哪里有八十两银子啊,只能参军去了,兄弟你呢?”
“咳,你还不知道呐,佘子青这个狗官本想从咱老百姓手里敲诈一笔,但好在郡里派来了监督的人,他怕官印不保,又变成五十两啦”,符魁一听心下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