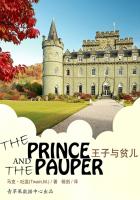一
Mayo和妮娜从香港回来,也许是得到了澳洲胖子支招,紧着就张罗召开特别股东大会,志在把北京那边的董事选出董事局,这样他的股权分配方案就可以顺利通过。胖子的钱就可以到账。股权分配方案也是随胖子的旨意。我隐约看出点猫腻儿:胖子是这个公司的操控者。
公司前期融资的钱几乎全投在了北京公司,现金账上所剩无几。重新上市,现金账上起码得有数百万的流动现金。现在,公司需要一只起死回生的神秘之手。这只手已经隐隐可见,那就是胖子。
特别股东大会的准备工作在紧张进行着。给股东的通知信像雪花一样发出去。还有一项工作,就是打电话。Mayo请来他的土著朋友帮忙,在黄页上查电话号码逐个拨。为了把北京的董事选出董事局,他玩拆股游戏,把他名下的,他私人公司名下的,妮娜名下的和他妈妈名下的股票拆成N股。土著朋友从电话本上找来陌生人使用拆股的投票权,按他的引导投票。酬劳是每人五十澳元。
董事局有北京两个董事:杨军和查尔斯·李;四个澳洲董事:Mayo,董事长,农场主安德罗和秃头法朗克。安德罗因为拥有巨大农场而得名。他是Mayo的好兄弟。法郎克因为年纪轻轻就秃头了,中国股东背地里就叫他“秃头”。他是胖子的代言人。一个上海董事:郑总,人称女枭雄。Mayo的目的是去掉杨军,换上澳洲的邓仁。新组合是:北京一个,澳洲五个,上海一个。这样,不管董事长和女枭雄站哪边,他都稳操胜券。
妮娜这次从香港回来,行头也大有改进,手上带着卡地亚手表,身上皱巴巴的一条裤子,她告诉我上万块港币。我入账时发现她花四万澳币买了两只表,一只送人一只留着自己带。一天,她拿来一张六万澳元的公司支票让我存进她和Mayo两人联名的信用卡户口。我做账时发现这张支票的票根写着作废。
董事长姓廖。上世纪六十年代随家人举家移民澳洲。扎在唐人街做餐馆。几十年的餐饮业做下来,肚子里填的都是些唐人街争地盘的伎俩。在唐人街训练出来的管理能力与IT行业这种西装上衣配牛仔裤的美国式的、技术含量高的现代管理相差甚远。他不懂账,不会看报表,不参与公司的管理,只管签支票。他认为只要控制住钱就是控制住公司。
Mayo与他合伙是看上中国的市场。在中国,他这尊神还是灵的。仅凭他的姓氏就能招来各路的投资者。如果说他是唐僧,公司还有位孙行者护法神─邓仁。邓仁一路追随廖董在中国招揽投资者。邓仁变戏法似的把廖董变成中国某领导人的后人,Mayo变成澳洲前总理的儿子。投资者中有中国军界的查理斯·李,也有上海地产界的女枭雄,他们就是冲中国领导人后人来的。
廖董不止一次在董事会上指出Mayo出差花销太大,飞机要坐头等舱,旅店要住香格里拉,还要捎上女友妮娜。
妮娜不是公司的人,她来上班不拿报酬。她愿意来上班,因为可以全方位看住Mayo。Mayo也愿意她来上班。她来了,就是他的私人秘书,买咖啡倒垃圾处理文件。工作不顺还可以向她吼几声。
这次他们俩在香港一个月,吃喝住行共花了六万澳币。廖董不同意报销。廖董说:“我在香港住一百澳币一晚的旅店,他们却住香格里拉套间,七百五十块澳币一晚。”Mayo申辩:“妮娜报销差旅费是应该的,因为她去是为公司工作,她工作不拿报酬。”至于住香格里拉,Mayo是这样回应董事长的:“你要我跟你一样住六百港币一晚的酒店?那是给人住的吗?是给猪住的。”
公司支票要有廖董和Mayo两人的签名才有效。Mayo不知用什么办法骗廖董签了张空白支票,他撕下支票,填上他和妮娜的名字和金额。票跟上写上“作废”。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差旅费给报销了。廖董见Mayo不坚持跟他要求报销这次的差旅费,“姜还是老的辣。”他得意地想,以为自己赢了这小鬼子。“想跟我玩?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啦。”他想到这,笑容也柔和了,心情比以往好多了,回到办公室来也没了往常的诸多问题。Mayo要召开特别股东大会,他没阻挠,也不参与准备工作,每天早上十点左右来公司溜一圈就到唐人街饮茶。Mayo玩的那些拆股把戏他一概不知。
股东大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Mayo让妮娜给国内来开会的人预订酒店。妮娜在网络上巡一轮,最后决定把他们安放在东区斯坦福酒店。“那可是克林顿前不久来悉尼下榻的宾馆呀。”Mayo在电话里用开玩笑的口吻跟邓仁说。他跟中国人打交道至今大约有五、六个年头了,深知中国人在乎这个。“但凡跟‘名’字有关联的,中国人都拥戴。例如名校、名牌、名车、名人,就连董事长与廖承志同姓也能募到钱。可笑!”轻蔑的笑意悄悄爬到他嘴角。
邓仁是澳洲公司聘的中国雇员,祖籍香港。Mayo看上邓仁的撒谎本事,一直想笼络到自己的麾下。这次是个机会,他要把北京的李军选出去,取而代之的是把邓仁选进来。他对李军的讨厌是不可名状的。他跟李军语言沟通的障碍不是主要原因。李军这位军人出身的高干子弟与他这位澳洲贵族后裔一样,血液里流着傲慢与武断的因子。他们的出生注定了他们的相互排斥。
邓仁当然要来参加会议,李军也要来,还有女枭雄。
邓仁和女枭雄在会议前一天就到了。
北京那边因为有廖董的支持,很是放心。李军安排在开会当天早上到。会议在中午十二点召开,飞机的到达时间是早上十点,怎么算都赶得上。他认为没有他,会是开不成的。在北京,他不在,谁敢说开会?
Mayo考虑到女枭雄不懂英文,让我给她当临时翻译。我与女枭雄是初次见面。她是位二十七、八,面如桃花,鬓发如云的平民美女。如果上帝这会儿站在我面前,我会冲动地抓起他的衣领狠狠地摇他:“为什么呀?为什么好处都搁她身上?怎么可以这样不公平?”如果我的视力正常,看到的白纸黑字都是真的;如果我的记忆力没骗我,没出现幻觉的话;在各种各样的文件里出现女枭雄的名字和头衔是:个人投资者最大股东;北京合资公司最大债权人;北京合资公司发言人等等。我给她勾勒出的形象是个饱经风霜,阅历丰富的中年商界女强人。
他们到达的当天中午,女枭雄跟我说去吃饭,当然不是公费,邓仁请客。这时的邓仁完全背叛他平时的精英形象,走在女枭雄的身边,上身微微前倾步伐稍后于女枭雄半个身子,脸上挂着谦恭的微笑,一路给女枭雄解说路牌、街名,可谓温馨体贴之至。我这个临时翻译完全多余。我默默地走在他们的后面。我不认为我应该出现在这里,在他们中间。我是会计,不是跟班。我怨Mayo,诅咒Mayo:“你投资中国,注定要失败,因为你永远把不准中国人的脉。看看对这女枭雄的安排,愚蠢之极。”
邓仁不会为了一个董事位置就旗帜鲜明地站在Mayo的一边。他属狼科,利益可以让他做任何事。在Mayo的面前他表现出全心全意,鞠躬尽瘁的态度,在廖董和女枭雄那儿又表现出不可为而为之的献身精神,伴君如伴虎的无奈。这时他鞍前马后地侍候着女枭雄。看来女枭雄不是很买他的账。她漫不经心地应付他,放慢脚步等我跟上来,和我搭话:“澳洲的财会制度跟我们中国的一样吗?不一样吧?”
“不一样。”我发现她已经拉着我的手了。我神经质地看看左右,同性拉手是同性恋信号。当然她不是这意思,我明白。
“比我们的复杂吧?”
“不,好像中国的更复杂。”我讲的是真心话。回去查账,发现澳洲的财会制度比中国的简单。可是中国还是有这么多假账。
“我也是财会出身。我想学澳洲会计。有空你能教我吗?”
“怎么教?”我试着挣脱她的手。我不只是担心周围的人误会我们是同性恋,我还担心背后那双眼睛。邓仁代替我刚才的位置─沉默的跟班。他的存在,我如芒在背:他会不会在Mayo面前造谣我和枭雄的亲密状。Mayo的多疑我是领教过的。刚来公司不久,初次见邓仁,我们用中文对话,Mayo立马打断我们的对话,支开邓仁,不高兴地说:“在我面前请讲英文。”我懂得讲大家都懂的语言是起码的礼貌,这是母亲从小教我的。我向他道歉。Mayo不乐意我跟别的员工走得近,尤其是中国的。因为我知道公司的秘密。廖董曾经几次请我喝咖啡、吃饭,为的是套出公司的财政状况。我岂敢透露半个字。我跟Mayo签有保密合同。当时我对合同中“不可以直接向CEO以外的人包括董事长汇报财务状况,除非经CEO同意”这话不理解,他说董事长应该向他了解公司的事情而不是跨过他向下级了解。
“我想啊,记账都是相通的咯,不同的是制度。该记为资本、债权或益损,根据制度而定。你只要以我们公司的账为例,给我示范它们的不同就可以。有困难吗?”女枭雄试探我。
“啊,明天会很忙…你什么时候走?”我再迟钝也领会她的意思,就是想看公司的账。我不好直接拒绝她,跟她打马虎眼。
回公司我就向Mayo汇报。我要抢在邓仁的前面。Mayo说:“你不需要给她做翻译了。回来做你的工作。”
谢谢,可恶的CEO。
开股东大会那天,早上八点,我和Mayo、妮娜就开工了,我们忙着搬桌子、摆凳子、分放大会决议,打电话定咖啡糕点,为招呼早到的股东们。为了走路方便,我和妮娜都脱掉高跟鞋打赤脚在地毯上跑来跑去。“工作着是美丽的”,我脑海突然跳出作家陈学昭的书名。《工作着是美丽的》很适合此情此景。我喜欢工作,很忘情很投入。
时间前移,十一点、十一点半,各路人马陆续到来,认识的、不认识的,摩肩接踵。十一点五十分,李军还没见踪影,廖董看表,Mayo看表。他们看表的目的各不同。廖董看表,是焦急李军怎么还没到;Mayo看表是等开会时间,“时间一到就开始,一秒也不等。”他想。他等够了,在北京,他等。每次召开会议,管理层的人总有迟到的。在这里他也等,等廖董。每次说好九点半开会,廖董总是十点才姗姗来迟。这次不一样了,这次他有胖子撑腰,这次他有他的计划。“这班Bloody Chinese(鸟中国人)!”他在心里骂。他和妮娜常常挂嘴边的话。每次听他们这么骂,我总是把脸转一边。我曾经对他们说:“请不要在我的面前这样讲!”妮娜说:“对不起,我们不是骂你,是指北京那帮人。”我阿Q地想,算了算了,不跟他们计较。他们这么气愤“这班鸟中国人”,说明被“鸟中国人”耍狠了。他把辛辛苦苦私下募集的钱放到中国,那边管理层有六个人,每人另有自己的公司,钱在六个公司的银行账号里转来转去就消失了。
会议只开半个小时就结束了,表决如Mayo的意思进行,决议顺利通过。李军出局,邓仁入局。Mayo傲慢地笑:“跟我斗?跟我斗就这个下场!”
会议刚刚结束,人们站起来还没走,李军风尘仆仆站在门口,以为人们也是刚刚进场还没坐下,脸上的表情写着:哎,终于到了。
“怎么现在才来?会议结束了才来!”廖董没好声气地说,目光是责备加失望。
“啊!完了?”李军没想到就连三十分钟也不等,他可是要出国要坐十个小时的飞机才到呀。十个小时换三十分钟都不行?他可是公司的董事啊!这点面子都不给?他由不知所措到愤怒,恼羞成怒。他看都不看Mayo和妮娜一眼,只跟廖董、女枭雄打招呼。我敏感地觉得邓仁肯定不在场,扫一眼现场,果真不见他人。
二
我从沉睡中醒来,已经是早上九点多。连日来忙活股东大会,身心的疲惫已经到了极限,尤其是昨天。啊!昨天?我一生中最想忘记的一天。
我躺在床上,透支的体力慢慢恢复,模糊的意识慢慢清晰,昨天的一幕,我最愿意忘记的一幕像我的个性一样固执地钻回记忆中:中午十二点半,特别股东大会结束。重组后的董事局接着在一点钟将召开董事会议。讨论决议1.发行新股以集资。集资对象当然是胖子。新股价格是零点一分,胖子投资一百万就拥有一亿股;讨论决议2.缩股,一百股变一股。中国股东花两毛一股买来的股票将缩水百分之九十九。原来跟北京谈不拢主要就是这缩股决议。反对这决议的还有廖董和女枭雄。中国股东都是廖董招来的,他无法面对他们。枭雄的利益和北京是一致的,她却聪明地不与Mayo发生直接冲突,想借刀杀人,利用李军为她挣利益。现在大势已去,李军和廖董是斗架败下阵来的公鸡,只能偃旗息鼓。绊脚石已经搬开,Mayo迫不及待要解决现金问题。他怕邓仁做手脚,不让他做女枭雄的翻译,指定我来做,同时北京的董事以电话会议方式参与,我的翻译也同时对北京。
会议前半个小时我才接到通知和会议内容。这就是Mayo,他不信任任何人,包括我。
我一脚踏进会议室,董事们已经在座。所有的人都看向我。
在吃饭的半个小时里我把会议大纲看一下。惶恐中开会时间已到,我把半杯没喝完的咖啡像喝酒一样一口干尽,付了钱,一手捂着手袋一手抓着几张会议决议奔跑回会议室,还是迟到了。
Mayo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宽容,也许在上一回合的争斗中取得的胜利令他有个好心情吧?他竟然向我微笑示意我坐下。在座人中唯有我没有利益冲突,这一属性使他们相对更信任我。或者说,对Mayo起用我代替邓仁更有说服力。
股东大会的翻译工作已经耗尽我的精气神,董事局会议上,我无法再集中精神。也许,这是我头一次参加董事局会议,连妮娜都没资格参加的会议,过于紧张,我把“为了能重新上市”翻成“为了不能重新上市”。对于我荒谬的翻译,邓仁和廖董几乎同时间给予纠正。Mayo满脸乌云,马上换上邓仁。我只恨地上没有洞好让我钻进去。丢人呐!丢我的人也丢Mayo的人。他力排众议推荐我进董事局当翻译,我就这么向人们展示我的能力?!我的失败就是他的失败。唉!唉!
事后,我每次回想当时的情景,都诧异自己事发时竟然没哭,没有脸红、羞愧、难堪,没有……怎么可以做到这样坚定、冷静、心静如水地听着邓仁翻译,一直到会议结束?
丢人都丢到北京去了,想起都心痛得想死。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在工作,我的工作还没结束,要坚持,坚持……
我翻身起床开电脑查收电邮。近几天没给张涛发电邮,想必张涛等急了?我比任何时候都想他,快疯了。工作中的挫折把我推向张涛。我需要一个支撑,需要靠一靠。他不是我的山,也不是大树,可能只是汪洋中的一根稻草,一个浪花就能漂走他,那我也不管,至少目前我伸手够得着的只有他了,就算借来的肩膀让我喘喘气吧,我还不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