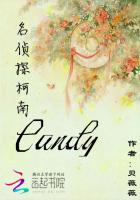白子画确实在加紧修炼。
他是骄傲没错,但不是狂傲,他做的每件事情,向来都极有把握。那么多次,他很少失手,不是因为他多聪明,运气多好,而是他每次都准备得非常充分。
除了眼下这件事。
拉扯两个四维空间,在他要的那个时间点准确地穿越回去,同时弯曲整个五维空间,达到六维的时空逆转——这件事,他真的没有把握。
没把握,但他还是会去做。
所以,除了日夜加紧修炼,争取让修为更上一层楼外,他也别无他法。每晚为小骨输的那些灵力,倒并没什么,对于他博大而浩瀚的修为来说,不过沧海一粟。但扭转时空,需要付出多大的力量,甚至过程中会出现哪些意外,他都无法预估。
白子画接任掌门的时候,就已经是九重天的修为,当时震撼仙界无人能敌。但因为后来那些事,身子整个被拖垮了,修为丢了个七零八落不说,险些连命都没了。若不是小骨牺牲自己,求师兄和师弟为她抽魂,保住神谕之力,又何来现在的白子画?
所以,那是他欠她的。
以前她还小,浑浑噩噩,不觉得笨一点傻一点有什么要紧,反正只要跟在师父身后就好,吃吃喝喝,玩玩看看,伤脑筋的问题搞得懂、搞不懂都没关系,反正怎么样师父都会护着她。
但慢慢的,时间过去,世界也开始变了。她要面对的已不再只是简单一个师父,一个樊离书院而已。依依、幽若、师叔、姐姐、姐夫、小鱼、小惜……甚至她最在意的师父,身边的每个人都在飞速地发展前进,以新的面貌、新的身份,更强大、更美好地亮相,他们在新的世界里如鱼得水,挥斥方遒。
唯独只有她,还是那个笨笨傻傻的样子,胆小地,缩在师父的身后。以前可以说,搞不懂没关系,长大就会懂了。但现在,一千年过去了,她还没有长大么?
有时候,师父带她去参加一些高级的酒会。她和那些妆容精致、举止高雅的女眷们在一起,就感到莫名的害怕。她怕她们会问她在哪里留学,主修什么专业;她怕她们一高兴就索性用英语或者法语来交谈;她怕她们谈论文学和艺术,然后问她最近组织了什么慈善……
她很怕那样的酒会,总是急急地要去找师父,只有躲在师父身后,她才是安全的。
但她知道,她不可能永远躲下去。也不可能永远找借口不去那些场合。
她要做他白子画的女人,就必须能够走出来,昂首挺胸地走到她们中间,用一种更高贵、更冷傲的声音去回答她们的问题。
不,什么语调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说出的那些话。
可是,她,能说什么?
所以,她一次次努力,明知不可为,也要去做。她不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更想证明,她配得上他。
她,值得他的爱。
这些,白子画都知道。他知道,但他什么都做不了。他看着她默默地努力,去挑战那些以她的心智根本不可能完成的目标,看着她被打击,被挫败,然后说服自己从头再来……
他竟然除了心疼,什么都做不了。甚至连说一些安慰的话,听上去都是那么苍白无力。
但现在,他可以试一试,为了小骨,为了他们两个。
感谢人类科技发展得如此迅速,让他得以有个机会改变过去某个错误的决定。这听上去很疯狂,但,逆天的事,他白子画也不是第一次做了。
------------------------------------------------------------------------------------------------------------------------------
师父最近很反常。
他不是个急性子的人,但最近练功勤得有点让人害怕。好多次,天光大亮,花千骨一觉醒来,身边的位子还是空的。床褥很平整,他根本就没睡。
她到处找他,最后却总是看到他从练功的地方走出来,苍白的脸上带着疲惫。
到底出了什么事,需要这样通宵达旦、不分昼夜地修炼?是长留又遇到了什么劲敌?还是他的旧伤又复发了,在闭关疗伤?
花千骨心中的谜团又开始滚动,不仅如此,她还发现师父常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连几个小时,都不知道在研究什么。
有一次,她趁他去接电话,偷偷溜进去瞄了一眼。那本质感极好的hermes小牛皮笔记本上,写满了各种奇怪的符号和公式。她不认识,却能肯定这绝不是仙界的法咒和道符,倒是有点类似自己学的那些数学公式。
不知道是不是怕被自己发现,白子画全部都是用英文做的笔记,花千骨无从辨识,但更肯定他有事瞒着自己。
她拿出手机,拍了下来。
------------------------------------------------------------------------------------------------------------------------------
方宇青又来信了。
他倒是经常写信过来。有时候,还会随信夹着照片,是那边的山,水,还有他和孩子们。
他瘦了些,更黑了。呵呵,或者说,因为成天脏兮兮的,所以显得黑了。
那里的天空特别蓝,白云好像就在头顶的样子。方宇青一直就兴头很高,每张照片里,他都和孩子们在一起笑,笑得好开心。
他带了一把吉他,教孩子们唱歌。他还带了个足球,和孩子一起踢球。不过踢了几次,球就没气了。他在信里说,bones,有空给我寄个打气筒吧,我好给足球打气。又说,你再给我寄点书来吧,这里的孩子特别喜欢看书,原来那几本早就翻烂了。
最后他说,bones,你来看看我吧,我想你。
花千骨笑笑,把信叠好,放在一个专门的铁皮盒子里,锁好。他说要的那些东西,她都如数寄了过去,但一个字都没有回。
很多话,她不需要说,他应该也能懂。
但方宇青的信仍是如期而来,他也从来不在信里问,为什么你不回信啊之类的问题。就像他自己说的,你可以不喜欢我,但你管不了我喜欢你。你可以不回信,但你管不了我写给你。
花千骨似乎也习惯了每隔一段时间,去信箱收他的信,默默地看好,默默地锁起来。
这天,她打开信箱,看到一枚传音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