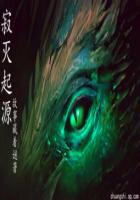沉闷的咯咯声中,两扇巨大的城门缓缓打开,友康穿过阴暗的过道,铸建城楼的坚石巨条横在头顶,受压迫的心底不由感到一股沉重威严的紧张感。
城楼的出口处,一个仆从模样的男子紧扣双手,望着他,默默恭候,友康心内狐疑,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更别谈和他有任何交集,他为何而来?还有城楼上那个举止威严的男人,他是谁?
友康走到他的身旁,伴随巨大的碰撞声响,后方的城门紧紧合在一起,守门的士兵们抱起拦门的横条卧在两边的嵌槽内。
那仆人走过友康,轻轻地抚摸火焰神使长长的马脸,又解开包在火焰神使耳边的布条,仔细地观察它耳朵的伤势,不悦地抱怨道:“看来老爷要不高兴了。”
听见这话,友康心里不禁猜测:他和那个傲慢的清童大概一样,都是郑家的家奴。那之前城楼上伫立的男人又是谁?看他的气势做派,不会是家奴这等人,但一定是郑家的人,地位或许很高,估计是一个主子吧。
那人转过头,以仆人特有的谨慎目光快速地扫了友康一眼,语气谦卑地问道:“敢问阁下尊姓大名?”
“墨兰….友康”友康报上自己的性命。
眼前之人无论仪态、语言都频频有礼,甚合名门大族的家规礼法,不似一般仗势欺人的低等恶奴,以他的身份来看,他在郑家的家奴中应属于贴身伺候的高等奴仆,这样的奴才多与主子的关系不同一般,友康揣测到。
“三爷命小人请墨兰公子到府上一叙”说着,那仆人躬腰伸手,面带笑容,摆出一副尊请贵宾的姿势。在他身后,一辆装饰豪华的马车早已恭候一旁。
这一路友康吃了不少亏,可不敢轻易就上陌生人的车,虽然心中已经猜出事情的轮廓,但还需那人亲口说出,确认自己的猜想。
“你是谁?三爷又是谁?”友康土生土长,没眼前之人高雅的涵养礼教,出口之言自然少不掉乡下少年的土气。
那人笑了一下,知道自己今天碰到个直肠子的乡下土包子,他倒没有看不起这个乡下少年,自己也是从土里爬出来的苦命人,因为幼时长得俊俏又讨人喜欢,家里一贫如洗,被人贩子卖到郑家为奴,不过他的命倒很好。因为机灵聪明从小就成了郑家三公子三爷的书童,一直侍候三爷左右。
“三爷是江南郑家的三公子,我只是他的贴身奴才:秋明。我奉命行事请公子到郑家一叙,有些事还要请公子说明白。”秋明微笑着,不慌不忙,一脸谦和。
“什么事?我听不明白。”友康想问得更清楚,虽然莫忧雨道那些人的死和自己没有瓜葛,但他不想和大人物扯上关系,人家家大业大,轻轻一根小指头毫不费力地能捏死自个。
“什么事?不是我这做奴才能知道的。不过,公子身后的那匹马可是我家老爷的爱驹,现在落到公子的手里,恐怕这要请公子到府上说个明白。”秋明说。
“它不是我的”友康看了火焰神使一眼,问:“三爷名叫郑龙吗?”
秋明吃了一惊,没想到眼前的乡下少年竟敢直呼郑家家主的大名,看他年少无知,也不和他斤斤计较,“他是郑家的家主——老爷的名讳,不是三爷。”说到这,他停顿一下,语气加重道“公子的嘴巴还是小心点好,老爷的名讳不是什么人都能呼来呼去的。”
对他的警告,友康心里不高兴,但还是接着往下说,“我有东西要给他,一个女人托我带给他的。”
“那更好,请。”秋明一摆手,不容友康拒绝。
友康没有办法,把孩子从背上解下来抱在怀中,坐上那辆精美的马车。马车四面皆用美丽丝绸装裹,镶金嵌宝的窗牖被一帘淡蓝色的绉纱遮挡,车内鲜艳夺目,五色毛毯铺底,表面纹路复杂华丽,光是纺织的丝线就不下于十余种,五色的颜色相互交织纵横,华美极了,可是这美丽之物只能被贵人踩在脚下。长形檀木座椅被裹上一层秀丽的锦绣,锦绣内被柔软的蚕丝填充,人卧上去光滑舒适。中间圆形桌几上,一座古玉香炉正飘起渺渺的青烟,吸入鼻腔,身心安宁,旅途的疲乏不觉一扫而尽。抽屉式的桌几内部放有消暑清凉的寒冰。
友康局促地坐在马车内,舒服的有些不自然,看着对面的秋明倒是一副镇静的模样,对一切视若无睹。
马车速度极快,人在里面却不觉颠簸,减震功能做的精巧极了。
车内的友康听见车外越来越热闹,世俗的喧嚣和车内的安静简直如两个世界,车外小贩的叫卖声、女人的叱骂生、孩子的欢笑声和车内香炉飘出的丝丝香甜味、袭人的凉气、柔软的丝绸触感让友康恍惚、迷醉,这里的生活太美好了,车外市井生活与这一比,几乎沉重得可怜,根本不值一提。
马车驶过上都的城门,守门的士兵识得马车上嵌有的郑家架徽,没人敢出来检查。就这样,马车大摇大摆地驶过上都的街道,左转右转后进入城中宁静的小街,从一道偏门进入朱漆红门的府邸宅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