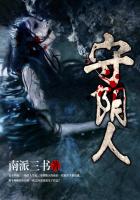当殿天南说到地葬真魔曾经被一头麋鹿搭救,吕永智瞬间回忆起他看过的一幅石图,在那幅石图的画面中,有一头逃跑的鹿,在鹿的背后趴着一个小怪物,人不人鬼不鬼,长相可怖。
起初,吕永智他还以为是狈之类的,现在他明白了,那分明就是塞国峰的墓主人——小时候的地葬真魔。
就连一个将军死了,所葬的陵寝地宫里都要由画师将他生平事迹绘画歌咏,更何况是规模堪比皇陵的地葬真魔,难道他看过的石图,所有的都是关于地葬真魔生平的印记?
这从道理上可以解释的通!
一个怪物,一个由狛和人生下来的异种,就像是几百年间大兴安岭、俄罗斯森林里的真实存在过的狼人、马人等等杂交异种,让人看一眼就会头皮发麻,心生怜悯,这种怪物难道也会有人的情感?甚至比人还要聪明?
吕永智站在石门门口,他怔在当场,在这一刻,他心中不能平静,好像是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综合症,对塞国峰墓主人地葬真魔心生强烈的好奇心和膜拜,他是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一个穷二代,他活了三十载,在这个世界上,对生存两个字感受深切,实在是太艰难。
幸运的是,他是一个人,而并非一个人、畜杂交后的怪物,可如果一个人,他生来就是一个怪物长相,还想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谈何容易?人的出身身不由己,怪物想必它的一生也不愿意看到自己长成这副尊荣吧。
更不要说,在怪物死之后能享受到堪比帝王陵寝规模的待遇了。
殿天南的话打断了吕永智的思绪,他手指着斜前方巨人的肩膀头,惊呼道:
“我靠!永哥,你快看,真神了,这特娘的哪是什么泰坦巨人?分明就是一个死了不知道多少年头的大地植人,一棵小号的梵天宝树,我说怎么它脑袋上、肩膀头上长着黑白邪轮,在我们殿家老寨地下深处也葬着这么一棵,不过个头要比这个大了太多太多。”
“什么?大地植人?”
吕永智对大地植人这四个字异常的敏感,他这一次和殿天南走的近了些,近距离打量这尊泰坦巨人,在那巨人的肩膀头、脑袋上,偶尔会闪现出黑白色的眼球,这眼球像八卦阴阳鱼,又像是写轮眼,给人的感觉非常邪乎。
可这名身高达三米的大地植人身上到底还藏着什么秘密?它真的就像是殿天南所说的那样是人变成的吗?什么人可以长到三米的身高?
种种疑问,吕永智的心都要装不下了,就当他和殿天南绕到大地植人的身后,他的呼吸急促不安,他看到大地植人背后竟然背着一口水晶迷你窖棺。
在窖棺表面布满斑驳的红色血丝,组成了一张血色的大网,一条银色的小蛇顺着血色的网络正在水晶窖棺表面游走。
“空的?”
殿天南看到水晶窖棺里面空空如也,一脸的诧异道。
然而,在吕永智的眼里,当他的目光落在这口迷你窖棺内,他可以透视的眼睛一眼看见在窖棺中竟然葬着一颗死人头,死人头明睁二目,长的像是一个中亚人,眉心处纹着古篆体仙字,一道道血红的丝线从仙字正不停的流出,源源不断流到水晶窖棺的表面,然后被那条小银蛇吞掉。
那银蛇和吕永智之前在万象阵中遇到的明显不同,在银蛇的眉心处竟然有一道道纹络,这无数的纹络扭曲成了一个古篆体‘葬’字!
“嘶!”
小银蛇察觉到了吕永智的目光,它在血线内弓起了蛇身,变成了一道银色光剑,银色的光剑几乎是瞬息之间就到了吕永智的眉心——
“啊!”
吕永智吓的魂飞魄散,失声惊呼。
咔嚓一声,怀中宝珠裂响。
这一声裂响恰是及时雨,让吕永智的意识恢复,大梦方醒,他觉的眉心刺痛,奇痒难忍,用手一摸,什么都没有。
当吕永智第二眼向水晶窖棺看去,那水晶窖棺里哪里有死人头?就连窖棺水晶表面也一样空空如也,并没有什么血丝。
殿天南睁圆了眼,一眼不眨瞅着水晶窖棺:“永哥?我刚才还明明看到棺材上有血线,怎么一眨眼的功夫——没了?”
吕永智没有回答,他觉的脖子上冰凉,有一个凉飕飕的东西缠上了他,那冰凉玉润的触感,那血浓于水的连体感觉,一切都在心中,非亲身,难以言道。
他颤抖着,用手去抚摸脖子上的小东西,冰凉细长的结晶肉体,那是人类又一次对生命等级的崭新的定义,那是一条银色的小蛇,在血塔内守候了千年的岁月,于今时今日,这一刻,这一秒,又一次迎来了新主人。
这种感觉是如此的真实,可吕永智借着大地植人表面的晶莹,他看到倒影出的另一个自己,结果,他惊奇的看到,在他的脖子上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
他心中突然莫名的失落和悲伤,说不清道不明,就好像千年的老朋友又一次离开了自己,是他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结果。
就当吕永智对着大地植人的背影发呆之时,从断龙石方向蓦然传来一声怒笑,就听殿天南激动道:“大哥!你终于来了!”
顺着声音,吕永智侧首看去,他看到一个黑色的虚线勾勒的人影刚刚好从那巨大的断龙石中钻了出来,连同这道黑色的暗影在内,一具全身惨白如纸丢失了右臂的死尸,它闭合着双眼跟随着这道暗影轻而易举的穿透了万斤重断龙石来到了这间禁闭石室之内。
这还没完!
当吕永智看到一个长的貌美如花的绝色美少女,她最后一个穿过了断龙石,出现在他面前,正向他走来,那狡黠得微笑,是如此的熟悉,如此的亲切,吕永智他——惊呆了!
这美少女为何给他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身高就和张勃启差不多,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像梦蝶、像百合花开、像乞力马扎罗山上的冰雪,纯洁的让他窒息,美丽的让他心悸。
“永哥——”
这一声永哥叫到了吕永智心坎里,他忽然觉的一切都值了,人生可以无憾,他笑了,眼眶通红,极力去克制内心真实的情感,是在这数日时间里,一个凡人对地宫世界无限的恐惧之后,遇到了比亲人还要亲的‘自己人’。
他擦掉眼角的泪痕,一骚包的冲美少女挥手,切情感汇成了简简单单的八个字:“勃启兄,你没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