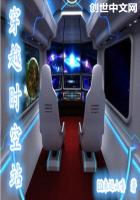“救命,救命!”
当那艘大船离自己不逾百步的时候,老胡终于声嘶力竭的呼喊起来。十七年来,他第一次如此强烈的渴望着被人关注。然而,于那大船而言,他毕竟还是太小,在这浩渺无垠的水面上,如一只微小的蝇蚁,任凭他如何挣扎,终究无济于事。滚滚波涛,淹没了他的呼喊,而茫茫水雾,又隐去了他的身影。
但是,老胡并没有放弃。
“救命,救命!”
他再次呼喊起来,那是一种歇斯底里般的呼喊,这一刻,他仿佛拼尽了周身之力,仿佛面前行驶着的,并非什么大船,而是在这浩荡如海的水面上,他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最后,当那艘大船终于微微转向,慢慢朝自己驶来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成功了。
那是一艘白色的船,如雪一般白,水雾迷濛中,远远望去,浑似一朵盛开在水面之上的圣洁之花。而一张张巨大的船帆,又使它,像极了一只翱翔于九天之上的天鹅。大船更近了,近到老胡能清晰的看到,微风中,如雕塑般屹立在船首的那个中年男人。只听他远远的向自己喊到:
“老人家,莫急,莫急!我们这就救你上来!”语气中,竟透着股暖人心肠的关切。轻柔,而不失浑厚;焦切,却又不乏镇定。一霎时,老胡觉得那简直就是举世间,最美妙的乐音。
大船终于驶到了老胡栖身的江礁之侧。两个男人从船上放下缆绳,顺着缆绳,老胡艰难的爬上了船。直到上船后,他才发现,这艘船,竟比之前载着自己的那艘主祭船还要大。在船上,老胡看到了马,至少数十匹,还有上百名甲胄在身的兵士,他们有的相互之间比划着刀枪,有的悠闲的骑着马,而更多的,则是分列船身两侧,面色凝重的极目眺望着远方。原来,把自己救上来的,竟是一艘战船。
校正好航向之后,大船又一次缓缓起航了。不多时,那块江礁,便已消隐在茫茫水雾之中。望着滚滚波涛,老胡不禁心生感慨,那些人千般算计,到头来,还是没能杀死自己,他这样想着,心底突然涌动着一股胜利者的喜悦。然而,没多久,那喜悦便愈发的浅了,最后又转而化作一抹淡淡的悲凉,那是一种每个离乡背井的游子,都会不时泛滥于胸的悲凉,他不明白自己为何也会心生这般情怀,毕竟于自己而言,赤岩那鬼地方,着实是生无可恋。是啊,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小男孩来说,一个满城充斥着针对自己冷眼、谩骂甚至是谋杀的地方,那实在是和地狱没什么分别。但直到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养父母,想起了那只灰鹞,想起了那个叫拔力乌的小姑娘;才发现,原来赤岩城,于自己,也并非一无是处。慢慢的,那悲凉,竟愈发的浓了。
“要好好活着!”
老胡又想起了养母临死时的那句话,老人家此刻应当可以瞑目了,因为目前为止,老胡似乎已经将死神给远远的甩在了身后。虽然为此着实费了一番周折,吃了一些苦头,但现在看来,这些付出终究还是值得的。
在老胡凝神惘思之际,刚才站在船首冲他喊话的那个中年男人走了过来,望着一身狼狈的老胡,他突然开口道:
“作为一个像您这般年岁的人,实在不应该再出没于这江涛之间!”他的声音依旧那么浑厚有力,如两块碰在一处的金石。
经此一问,老胡这才回过神来,他打量了一眼面前的这个男人,一张瘦削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风霜,而两只眼睛,则炯炯如炬,无时无刻不焕发着夺人的光彩,此人高的出奇,老胡望着他,如望着一颗风雪中拔然的劲松。
那男人见老胡没有反应,便又问了一次,而老胡却浑似没听见,只呆呆的立在原地,冲着那男人露出一抹傻傻的笑。
“您一定饿了吧?我让他们给您准备些饭食。”那男人并未放弃,再一次关切的问道。
老胡依旧未答话,他的笑似乎僵硬在了脸上。
“您莫不是怕我们吧?呵呵,您且宽心,我们可不是坏人。”那男人觉得老胡应该是受了惊吓,故而缄口不言。所以再说这些话时,他的语气变的极尽轻柔,竟又似两块碰在一处的碧玉。而老胡,却憨笑如常。
“依我看,他这里肯定有问题!”从那男人身后闪出一个少年,他简直就是前者的简缩版,从五官到头发都是那样的相像,唯一的不同则是眉宇间那股傲然之气,前者充盈,而后者了无。只此一点,就让前者看起来更像是原版,而后者,则属于那种有心无力的临摹之作。少年说着指了指自己的耳朵,他顿了顿,又继续说道:
“要么就是这里!”少年又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你……你们是要去……去打仗么?”老胡终于颤微微的开了口,他尽量使自己说的每一个字听起来都是那么别扭,以此来故意彰显出自己的蠢笨。在对船上之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装疯卖傻,似乎成了他现在唯一的盾牌。
“哈哈,哈哈哈!看来是这里!”少年再次指了指自己的脑袋,经他这么一指,船上众人顿时笑作一团。老胡却也不觉羞,亦随着众人笑了起来,笑的那样肤浅,笑的那样没心没肺。
“咳!”见势,那男人轻咳了一声,但只此一声,船上便立时噤若寒蝉。唯老胡不明就里,依旧憨笑如常,过了好久,才不情愿的收回了他那突兀至极的笑。
“我们可不是去打仗,我们是要回家。”男人淡淡的说着。
“回……回家?能……能捎上我么?”老胡依旧吞吞吐吐,显得极尽呆傻。
“可我们甚至都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是啊,你叫什么?”一旁的少年忙附和道。
“我——”老胡刚一开口,旋即又停了下来,他暗自思忖着,既然已经离开了赤岩,索性就把昔日种种忘个干净,这样也好重头来过,无论如何,“老胡”这个名字决计不能再用。过了好久,他终于冲着那个男人和少年,淡淡的说出了三个字:
“胡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