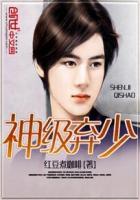苏溪眼光扫过一旁侍立的仆从,斩钉截铁道:“家父是儒将,那又如何?”
自苏居羽接任漓州节度使的第一日,文臣的出身便令他饱受诟病。朝野之中,处心积虑之人不胜枚举,而就在半月前,第三次针对漓州节度使的弹劾奏章已经抵达洛陵。
苏溪极为清楚,若非楚魏当日将那濮阳刺史的奏章压下,那么父亲苏居羽可能已承受滔天的罪责了。
她不甚清楚父亲的所作所为,只是那些蛛丝马迹在告诉她,冷同湾这个人,似乎已经与漓州苏府有了莫名的关联。
冷同湾,太子门生,或者说,太子诸多门客中,他是罕见的富甲一方之人。
在衡帝病势最沉那月,冷氏一族染指崂州一带盐运,并非空穴来风。
此事震动朝野,但最终,却也只草草了之。冷氏一族仍然无恙,冷同湾也毫发未损,就如同衡朝一直以来的暗机一般,替罪羊入狱,承担罪责。
但是苏居羽与冷同湾的书信交往,却是有据可查的。弹劾奏章由濮阳刺史发出,但那书信却不在他手中。此事说大便大,若说小,便也不是没道理。
楚魏得知此事时,仿佛丝毫未有在意。连他私自将如此机要的奏章压下时,也并未向苏溪多说些什么。苏溪之所以听闻,一半是从兄长口中,一半则是近来洛陵的风言风语了。
“崔将军,妄议你职责之外的事,是什么规矩?”苏溪见崔弩半晌不言,轻声道。
她本意也绝非与崔弩纠缠,只是想让他认清自己身份,不要再如此无礼。且如今话已说开,就此作罢到底是不再可能了。
“夫人,卑职知道自己的身份,这点不用您来提醒我!”崔弩如今年过三十,较雍杰还要年长几岁,而他看着眼前的苏溪,只觉如同稚子一般,加之他身为武将,不擅掩饰,此刻他眼中的不屑尽数被苏溪看出,心中冷冷。
“话说得不错,我正是提醒你认清自己的身份,既然清楚,我的目的便达到。”苏溪平素最不喜旁人以这般不尊重的态度对待自己,此刻怒火已然燃起,但想到楚魏谋划之事正需此人出力,且他一向随在楚魏身边,总归是忠心之人,自己在漓州遇险那日,也亏得他善后。
是故她收敛了脸上倨傲的神情,缓缓道:“崔将军莫怪我多说一句,你的赤胆忠心,从未有人怀疑过。那么既然无人疑你,为什么你要咄咄逼人?”
崔弩黝黑的脸上看不出过多的脸色变化,但他眼中几乎要连织成网的血丝却直接地表达了他的愤怒。他此刻只觉一腔怒火就要迸发,而苏溪却并不知其全情,刚要转身离开,只听得崔弩的声音。
“少夫人,卑职有话,不得不说!”
苏溪本不想回身看他,但那声音中蕴藏的怒意太过明显,她听在耳中,竟是从头到脚的不痛快,回身瞧他时,只见崔弩用力拱了拱手,也未俯身,只道:“古来便有妖女祸乱宫闱,蛊惑人心,成大不赦之事。”
苏溪冷眼看着他,心中错愕不能用言语来形容。
“你是……什么意思?”她只觉自己无法再听下去,脱口便问出。
崔弩也顾不得一旁侍从在畔,只再次拱了拱手,眼睛也不抬,只沉声道:“侯爷为令尊苏大人将那奏章硬性压下,此事虽然隐秘,但朝中从来也无隐匿之事。”他说着,眼中怒意好似更加,直直瞧着苏溪道:“节度使大人是何故受了冷同湾的拉拢,卑职是不知道,但是侯爷几次三番为漓州,为少夫人你的娘家做这些事,你就听之任之么?”
他的话说得坚决无比,也坚定无比。是,他确是忠心护主之人,多年未变。再说他对苏溪的敌意,却不仅仅只是由这件事而起。
“官盐营运,家父插手,只能有一个原因。”苏溪心中沉沉,却硬生生地用鄙夷的目光看着崔弩,扬手笑道:“冷同湾是太子门生,我长姐苏氏是圣上钦点的太子侧妃,适才崔将军你提到我的娘家,那么你说,我的娘家与太子府什么关系?”
她收起扬起的手,微侧着身子,笑道:“说句不应当的,家父与太子,本属翁婿之谊,而少侯爷同是我父亲的女婿,且不计你的话是真是假,即便是真,楚魏尽自己之力,为他的岳父泰山做些什么,瞒些什么,又算得了什么?”
她一向不屑与凝妆相提并论,但此刻,仅仅为了这莫名的颜面,她竟道出如此多违心之语,不禁如此,她还要在说完这些之后,重新以平常的倨傲神态看着眼前充满敌意的崔弩。
只听得几声饱含忧戚之感的冷笑声,崔弩缓缓后退两步,怒视着苏溪,恨恨道:“少侯爷迎你这苏家小姐入府,日后岂有宁日?”
苏溪在漓州的事,楚魏知道几分,那么崔弩便也知晓几分。
苏溪听他说出‘苏家小姐’这几字时,便已然对那份敌意有了认识,她揣测着,只听崔弩续道:“今日之事,或许转了身夫人你便将卑职如何不敬如何无礼告知了侯爷,但有些话,如果我崔弩不当着你的面说了出来,便不是我崔弩了!”他说得斩钉截铁,半分的迟疑也没有,而这番话毕,只见他紧绷着嘴角,对一旁的仆从斥道:“下去!”
那侍立在侧的仆从立时朝苏溪看去,目色惊惶而不解。
苏溪眼光瞥过那几名侍从,轻叹了口气,只道:“先退下罢!”
待仆从退去,她登时问道:“有什么想说的,直说便是,你既然将话说了出来,那么我倒当真要听一听了!”
只听得崔弩一声冷哼,继而低下头颅,沉声道:“谢夫人。”
苏溪转了身坐在书房离门最近的那乌木椅上,咄咄逼视着他。
“卑职想问,少夫人是什么人?”崔弩似笑非笑地看着地面,也未抬头,只是用脚上皂靴摩挲着地面上的石子,朗然道,“卑职不是要您回答,而是想说自己的看法。”
“但说无妨!”苏溪侧目看着他,面如冰霜。
“官家小姐,您自然是官家小姐,”崔弩恨恨道,“卑职职位低下,不敢说对您有何评价,只不过,堂堂漓州节度使之女,竟然公然出入青楼妓馆,公然草菅人命,公然殴打朝廷命官,堂而皇之地在男子房中过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