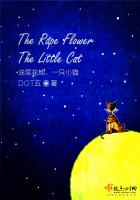八月的天,正是如火如炽,长夜漫漫,扰的人心烦,凌一剑躺在床上,脑子里反反复复的总是那句颤音,凌公子……
一睁眼,柴小妖娇羞的模样仿佛还萦绕在眼前,可一伸手,空无一物。
夜不成寐,唯有披衣起来,借着寥寥的月光,“嚯嚯嚯”的舞起了长剑,风到之处,玉碎瓦残。
“这大半夜的,谁啊?那么吵!”
柴小妖睡得犹如一头死猪,捂着耳朵,踢着被子。
旁边的惊鸿,对着她的睡相吐了吐舌头,心道:谁能比你吵啊?打呼噜、磨牙、流口水、踢被,小姐,您可是无一不精啊!
柴小妖对这话似有所悟,翻了个身,半梦着睡去。
凌一剑却是越练越烦,越烦越练,终于,他忍不住,三更半夜,骑着马去了渡口余老头家。
话说余老头正搂着他媳妇行周公之礼,你侬我侬,正行了一半,忽然,被一阵敲门声打断很是恼火,“吱呀”一声开了门,看着一脸铁青的凌一剑,气不打一处来,:“我说凌公子,天未塌,地未陷,你十万火急的跑来是为哪般啊?”
凌一剑语出惊人:“给我一包打胎药。”
余老头的气愤霎时无影无踪,凝着他:“当真?”
凌一剑还没应声,余老头已经迫不及待的拉着他进了旁边的药材铺,琳琅满目的药材规整的放在一排排货架上。
味道有些呛鼻,凌一剑微皱了眉。
余老头又开始滔滔不绝:凌公子,不是我吹啊,整个长安城,谁也没有我这儿的药材齐全,尊夫人打胎找我就对了,保证药到胎除,绝不影响二次生育,您看,这是三两的、五两的、十两的,下面是十五两的、二十两的、三十两的……”
“停!”凌一剑闭着眼,揉了揉发痛的太阳穴,“随便给我一包。”
余老头叹了口气,难得日行一善,苦口婆心:凌公子,你这就不对了,尊夫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怎好说随便……
“哐!”
余老头后颈上挨了一下,张着嘴昏倒在地上,凌一剑从身上摸出张银票扔在他身上,随便从货架上捞起一包药揣到怀里,一转身,大摇大摆的走掉了。
打马回到翠竹园,天际已经隐隐发白。
“公子,你这一夜都去哪儿了?”
在井边打水的蹁跹,往围裙上擦了一把手,迎了上来。难怪她问,凌一剑面容憔悴,眼圈发黑,像是刚从外面梦游回来。
凌一剑下了马,背着光站着,神情不明,伸手从怀里掏出那包药塞到蹁跹手中,语气异常的冷硬,“把药煎好,我亲自去端。”
蹁跹一应,跑去了柴房生火。
凌一剑却沉着脸,回了屋里,默默的坐着,手指来回的摩擦着手里的玉箫,心中波涛汹涌:紫萱,但愿你不要恨我,千万不要恨我,我只是不甘心,太不甘心了而已。
“这是什么?”
柴小妖刚一起床,就被惊鸿叫过来,看着书房里一大摞的旧书。
“这是女子出嫁前都要看过的书。”惊鸿往那封皮上一吹,撒了一地的灰,“公子虽然是江湖人,但交往的朋友都不能免俗,你以后和士家的小姐夫人们交往,总不能也像昨天那样。”
“《女戒》?”柴小妖随意拾起一本,怎么猪八戒也有女的么?
草草翻开几页,通篇繁体字,“……!”她勉强读来,“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
“这书好没道理!我不读!”她把书扔在一旁。
“怎么了?谁又惹你了?”凌一剑端着药,进了书房。
柴小妖感到有些意外,他怎会突然如此热络?难道是因为肚子里孩子的缘故?想到这里,她不禁伸手抚上了小腹。
一笑,“这本书荼毒三观!夫既可二娶,妇便可二嫁,这才公平!”
惊鸿一震,“你们聊,我去烧水。”
可能是受不了她惊世骇俗的言论,连连寻了个由头跑了。
“紫萱……”凌一剑端着药的手一滞,避过了那双清澈见底的眼,“你当真觉得,女子不必以夫为天,可以二嫁么?”
柴小妖脱口而出,“天经地义的嘛!”
凌一剑星眸一沉,“你真的失忆了么?”
柴小妖摇摇头,双手挽上他的胳膊,“失忆了又何妨,只要你还在我身边。”
凌一剑心里“咯噔”一撞,黯淡的眸子里闪过一丝色彩,久久的落在了药碗上,“药凉了,我去热一热!”
她却浑然不知,欢欢喜喜的夺过了药碗,抵上唇边,“不用了,天太热,凉的也好。”
他望着她葱白的手指,心痛的一紧,猛地打掉了药碗。
“嘭!”
跌破的药碗,染着黑汁,碎了一地。
太阳穴上青筋暴跳,怒目而视,“我说凉了!你没听见吗?”
柴小妖:“……!”他又生的什么气?
赶着声进来的惊鸿,瞅了瞅各人,缓和的笑了笑,“碎碎平安!碎碎平安!我来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