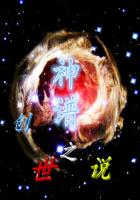宜城县尊褚豫亮今日真是喜出望外,那名叫做楚敦煌的前途无量的洛城尚武堂学子竟然主动找自己喝酒!这让县尊大人好生欢喜,忙不迭的从自家私藏的酒窖中搬出几坛子好酒,又让人从招逢楼定了一桌上好的席面,带着几位学子便朝自家私宅而去。
这私宅是他用来养如夫人的地方,平日里倒是不常来,只因为孙文德到了宜城之后占了他的县衙,而褚豫亮又不想同那个不苟言笑的将军住在同一屋檐,于是便搬了出来,只求一痛快。孙文德看在眼里,也懒得去管,于是褚豫亮便几乎将整个县衙都搬到了这个私宅,连平常办公都只在这里办。可以说除了公堂之外,这里已经是另一个宜城县衙了。
褚豫亮年近不惑,当了多年的县令,早就把升迁当做了天方夜谭。而今的他倒也不求别的,只求日后能够安安稳稳的致仕还乡做个富家之翁。但此次江南邪教之祸,却让他如坐针毡,再加上宜城又抓到了邪教,他这个守牧一方的官员,免不了追责殃及。褚豫亮原本的想法是和孙文德打好关系,以寻找靠山保自己无虞,可惜接触之后他才知道这位水师将领竟是个无缝的蛋,至少他褚豫亮是叮不透。失望之余,却偶然碰见了这几个试炼江南的尚武堂学子,当真是瞌睡来了枕头,天随人愿。
褚豫亮不是清官,但脑子好使,他知道尚武堂凡是试炼学员,基本是就是板上钉钉的甲科学子了。登榜甲科,日后的官运何止亨通二字,看看孙文德就知道了。再说尚武堂学子家世大多不凡,势力交错可谓盘根错节,只要随随便便抱上一根大腿,自己的后半生便有了保障。褚豫亮每每想到此处,便忍不住要笑出声来。自那日招逢楼接风宴后,褚豫亮早晚都在想如何能接近这些少年,却未曾想到自己还没下手,他们竟然先找上门来。这等美事,简直是要咧开了嘴。
褚豫亮的私宅并不大,胜在清幽淡雅。他的如夫人是个原先名动元州的戏子,二八年华出道,长就一双媚眼,知道自己命贱下流,便千方百计投入了褚豫亮的怀抱。褚豫亮对她倒也不错,虽不能给予名分,但至少衣食无虞,也算得人上人了。这女子心灵通透,知道疼人,而今虽已二十五六,但美艳不减当年,仍旧勾魂夺魄。她心中了然自家男人的心思,便亲自调制羹汤,又请了科班戏子助阵,把一个酒宴整治的像模像样,只求尽心竭力侍奉好几个看似并不更事的少年儿郎。
酒是好酒,菜是好菜,曲是好曲,人是美人。灯火阑珊之间其乐融融,那褚豫亮同楚敦煌又拼起了酒,当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喝的酒香四溢,就差称兄道弟了。酒至半酣,楚敦煌才提起要紧的事,含糊道:“褚大人,咱们两个虽年纪不同,但志趣相投,也算是忘年之交了吧?”
褚豫亮忙点头,道:“此话不错,往年之交往年之交,楚兄弟本就是江南人,此番尚武堂试炼,更是前途无量。我褚豫亮能和兄弟你有此缘分,当真是打着灯笼都招不来的。”
“那小弟,呃......小弟可有一事相求。”楚敦煌打着酒嗝,朝褚豫亮拱了拱手。
褚豫亮笑道:“兄弟但讲无妨,只要是老哥我做得到的,定然全力以赴。”
“倒也不是什么要紧事,只是有点难以启齿。”楚敦煌嘿嘿笑了两声,声音放低,道:“老哥也知道,我们兄弟几人从洛城而来,一路下江南。这个这个......啊,这个少年心性,手脚不免大方,如今到了宜城,腰里的盘缠......嘿嘿嘿,有点囊中羞涩。”
话说到这,褚豫亮登时恍然,拍着胸脯道:“这算什么事,有什么难以启齿。你我既是兄弟,便有通财之义,你但凡开口,我这里有多少,你拿多少去便是。”说完这话,他扭头朝身旁的管家道:“老刘,你去账房,先支出一千两银子,马上送到弗园。”
“老哥万万不可!”楚敦煌忙道:“老哥如此做,可正是陷兄弟于不义了!”
“哦?此话怎讲?”
“难道老哥忘了而今正住在县衙里的那位?”楚敦煌指了指县衙的方向,朝褚豫亮投去了一个颇有深意的眼神。
褚豫亮登时明白过来,点头道:“对对对,有那个铁面将军在,这......着实要谨慎小心。”顿了顿,褚豫亮朝楚敦煌又道:“那兄弟你说,老哥能做些什么。”
楚敦煌笑道:“倒也没什么,老哥知道,我尚武堂有相应规矩,凡学子路上所花费之银钱,皆可至各处报销。而今我们兄弟的帐,该由孙师兄报销,可你也看见了,我孙师兄的性格太过刚正,若是让他知道我们兄弟四人一路上花了这么多银子,免不得要骂我们一句不知节俭,奢靡行事了。所以......嘿嘿。”
褚豫亮恍然,道:“如此,我就明白了。兄弟是想走咱们县衙的账,先把银子报了?”
“正是如此。”楚敦煌笑了笑,道:“求别人不如求自己人,老哥能否先行将银钱报账,等年末天工院冲销账册时再领了不就行了。”
“这算什么事情。”褚豫亮笑道:“我个人都能给诸位报了,哪里用得着这般麻烦。”
“不麻烦不麻烦。”楚敦煌摆了摆手,倒杯酒冲褚豫亮说道:“一应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若是没有报账的记录,回头堂里查到了,嘿,老哥你想,我们免不得要摊上一个受贿贪墨的名头。老哥只需把从今年七月到十一月的账册带去弗园,让小弟一观便可,无需劳烦老哥。”
褚豫亮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心中又不禁高看了楚敦煌一眼。心说这家伙小小年纪,但却人情练达,处事圆润,假以时日,前途当真不可限量。又忽的想起洛城的同年好友说过的关于南宫郡主的一些逸闻,心中咯噔一跳,再看楚敦煌的眼神便充满了唏嘘。一手尚武堂,一手贵皇亲,这个少年人的未来,简直是金光闪闪啊。
想到此处,褚豫亮干脆的吩咐道:“老六,让曹主薄去一趟县衙,把账册领出来,直接送到弗园。”
原本对账只需要楚敦煌报一个数,然后直接由县衙小吏办事便可。但褚豫亮是何等人也,岂会如此迂腐?这把账册交给楚敦煌,其中看似画蛇添足,但其中夹杂了一点小心思。账册给你,任由你报帐,是报一百两还是一千两,其中多寡便随你来了。之间可操纵的余地可是真的不少。
楚敦煌眯起眼睛,对褚豫亮举杯道:“那我这里,先行谢过老哥了。”
“客气客气。”褚豫亮回了一句。
“我有两个朋友,正是崇文院的新贵,如今虽官职不高,但家世着实不凡。日后有机会,定向大人引见。”楚敦煌看似无意的添了一句话。
褚豫亮心中一跳,见得对方如此上道,不由得喜上眉梢,客气两句,一饮而尽。
与此同时,县尊私宅里的管家刘通已经找到了县衙主管账册的曹大金主薄,曹大金连夜将账册取出,同刘通一起送往了弗园。
而弗园湖心阁上的两人,早已恭候多时。
楚敦煌去和褚豫亮喝酒,敏达带着阿布,偏执的在暗处保护他。徐秀海和王自成守在湖心阁,等候账册到来。眼见得县尊官家和县衙主薄将今年七到十一月的二十四本账册送来,心中才松了一口气。看来他们这个剑走偏锋的计划,并未被孙文德知晓,至少孙文德不曾在这里设下重重障碍。
得了账册,两人将其藏入二楼,王自成从床底下拉出来另外的厚厚一摞账本,上面的题注同县衙账本一模一样,甚至封皮薄厚都等同。王自成嘿然一笑,对徐秀海道:“明日还给他们的时候,就拿这个。”
徐秀海点点头,回首望着那二十四本账册,眉头一痛,不禁问道:“你懂查账吗?”
“呃......”王自成尴尬的挠了挠头,道:“咱们两个都在北关做猎狐手,你问问你自己不就知道了。”
“我不懂。”徐秀海回答的很干脆,这让王自成翻了个白眼,叹道:“我也不懂。”
“敦煌他呢?”徐秀问道。
“估计够呛,一般不是商务或官宦之家,谁看账册?”王自成道。
“那敏达......好吧,他更不会,他连字都不认识几个。”徐秀海干脆的把敏达排除在外,直勾勾的看着王自成,“那现在怎么办?”
“没关系,虽然咱们不懂做账,但从中查出军需应该不是难事。”王自成的两只手互相捶了一下,道:“账目总会有记载,咱们不需要查账,只需要看账!”
......
......
等楚敦煌和敏达回来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最近他们总是睡的很晚,弗园的下人们倒也没谁觉得奇怪。只是楚敦煌身上的酒味太过浓重,熏的阿布都别着头,一脸嫌弃的样子。
到了湖心阁,敏达去找了点烧过的木炭,弄了杯炭水给他灌下去。木炭水催吐,楚敦煌吐了几下出过了酒,人登时清醒的差不多了,只是脸色还有些红,身上酒味和酸味浓重。等他再喝过了几口醒酒茶,几个人才笑眯眯的看着账册,脸上皆有得意。
但是趁着夜色大致的翻看了一遍之后,几人才变了脸色,楚敦煌打了个酒嗝,喃喃道:“这一点没问题啊!”
王自成眉头紧皱:“不可能啊,咱们的推断不会有错,宜城也应该有调配的记录,怎么......”
徐秀海捏着一本账册,前后全翻过来,仍旧未曾见到任何军需物资的标注,当即眉头皱起,沉默不语。
敏达不认识南朝字,也帮不上什么忙,听到他们说没什么问题,便向楚敦煌问道:“敦煌?”
楚敦煌脑袋有点晕,他干脆坐在地上,扒拉着椅子腿,扬了扬手里的账册,喃喃道:“没有军事标注,整个七到十一月没有任何的军需调动,干净的像一张白纸!”
敏达的眉头也皱了起来。
“不合常理。”王自成捏了捏拳头,语气严肃的道:“六个月,二十四本账册,分为农务、差务、工务和商务四项,每项六本,详细记录了这六个月里所有的明细。可这竟然连一本有军事标志的进出项都没有,实在不合常理。”
“虽说宜城并非军事戍卫城池,但如今城防所用的,都已经换成了水师官兵,这说明水师已经经过了调动。”徐秀海接道:“仅凭这一项,便能看得出,这些账册,都已经被人动过手脚了。”
“你是说有人做假账!”楚敦煌一愣。
“没错。”徐秀海道:“如果不是这样,根本解释不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楚敦煌深吸一口气,道:“会不会是褚豫亮!”
“应该不是。”王自成很快接道:“他还没这个本事,也不敢有这样的胆子,每年年末天工院都会对天下府县的账册进行对冲,这样的账本,足够他全家下大狱了!”
“那只有可能是孙师兄了。”楚敦煌皱起了眉头。
徐秀海捶了一下桌子,淡淡道:“好一个滴水不露,他们已经走到了我们前面。”
王自成无力的把账册扔在了地上,道:“又一条线索断了,咱们现在是束手无策,果然尚武堂不该干刑理院的事,跨界着实不容易。”
似乎是王自成的丧气脸让阿布感到好笑,只见到蹲在门口的阿布打了个哈欠,一溜小跑到王自成身前,冲他耀武扬威似的呲了呲牙。然后阿布便小碎步的跑到了敏达面前,先是把嘴巴放在敏达肩头,然后用爪子拍了拍敏达的肩膀。
敏达的脸有些红了。
楚敦煌冲着阿布笑道:“阿布,你和他嚼什么耳朵呢?”
阿布得意的冲楚敦煌扬了扬头,用抓子挠了他一下,然后转身便走,重新卧在门口,巨大的影子几乎要把一半的门给遮住。
楚敦煌向敏达问道:“阿布跟你讲什么了。”
敏达忽然有些吞吞吐吐了,半天也没说出来一句话。这让楚敦煌好生奇怪,便冲他问道:“嘿,你没事儿吧?”
好半晌,敏达才深吸一口气,道:“铁寒郎!”
三个字让整个屋子陷入了沉默。
铁寒郎,那个直属于禁卫府的铁寒郎?敏达怎么会突然提到这个衙门!铁寒郎可不是吃素的主,成立至今,近一甲子以来专事刺杀、渗透、谍探和情报工作,总之干的大多都不是阳光下的明面事。这个衙门栉风沐雨多少年来,给国朝的印象就只有六个字:“狠辣”、“阴私”、“神秘”!
还是楚敦煌最先反应过来,击掌道:“对啊,我们可以请铁寒郎帮忙!”
徐秀海叹道:“铁寒郎只服务于皇家。”
王自成也反应了过来,颇有深意的看了一眼敏达,对楚敦煌道:“我记得你好像跟我讲过某月某日,在千羽楼发生过的某事!”
“而这某事吗,说明咱们还是请得动铁寒郎的!”楚敦煌顺势答道。
徐秀海听的一脸糊涂,便保持沉默。
敏达脸色微红,不过只是刹那,他的弯刀便弹了出来,刀光雪亮,横在当中。
这种狠辣干脆的作风让贼兮兮的楚敦煌和贱兮兮的王自成瞬间噤若寒蝉,背着手指指点点头望屋顶道:“写信,写信写信!”
敏达低着头,缓缓收刀,脑海中忽然浮现出南宫的影子。
温柔又泼辣,干脆又明朗,灿烂又清澈。
她是他草原上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