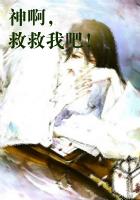我装作没听见,动作幅度更加夸张了,追上几步向前一扑,正好拽住了她的两只脚,就卯足了劲地向后拖,想把她拖到那水塘子里。水风轻双脚像溺水似的乱踢乱蹬,把我胸口及脸上都踹了几脚。突然一个趔趄,我就滚翻在地,双手也从她脚上脱了开来。我顺势往地上一摸,摸到一块石头,抓起来又继续扑上去。她见我手中有石,反抗更加剧烈。我摸爬滚打着几经折腾,终于把她按在地上,右手扬起石头,向着她脑袋就要砸将下去。她早被吓得魂飞魄散,赶忙将双手弯了起来,用肘部护住了头。眼见这石头就快要落下了,突然感觉手上被什么东西一拽,身子向后一仰,石块飞出,我也摔了个四仰八叉。虽然身上伤口被挣得生疼,但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一骨碌爬起来又向水风轻扑了上去。刚要抓到她,又觉脸上被一股强劲之力抽了过来,也没听到“啪”的一声响,脸上的肉就疼得像刀割一样,接着我整个人也一个踉跄摔倒在地。又挣扎着爬起来,凶神恶煞地朝水风轻走去,只不过摔了两次,已不再像疯牛那般势不可挡。眼看着又要挨上她,脸上又照例挨了一记打。我又是一个趔趄,四脚朝天地倒在那草地上。只不过这次倒下我就再也没爬起来,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用手揉着脸上被打过的地方。
就这样躺在地上过了一会,水风轻见我恢复平静了,就慢慢走过来,用登山杖指着我作防备,试探性地叫我:“傻大帽。”
“我刚才怎么了?”我一脸茫然地问。
“你刚才想杀本姑娘。”
“啊!”我大惊失色。
“我怎么可能会杀你呢,我怎么可能会舍得杀你呢?”我继续装着傻,说着又面目狰狞了一下。
“你不要乱动,乱动本姑娘就用登山杖把你脑袋敲碎。”
“我真的不可能杀你,我刚才被那鬼玩意附体了。”此话一出,脸上又被抽了一下,他奶奶个熊的,看来这鬼玩意不能乱得罪。
“你怎么了?”水风轻见我脸上疼得抽起来,但又听不到任何声响,瞪大眼睛问。
“我刚才被那鬼玩意打了好几下,真他娘的疼。……走吧,这下能够肯定,咱们可以走右边了。”
听我这么一说,水风轻马上恍然大悟。“你刚才这么装疯卖傻,是试探那玩意是否对咱们安一颗好心?”
“可不是咋地,在那青铜古城中的时候,被那大黑鬼的表象所迷,指引了咱们两三次,我还以为真的是想拯救咱们于危难呢,没想到那王八蛋竟把咱们引到了万劫不复之地。现在这鬼玩意,又给咱们画了一个大箭头,谁也保不准她就是安的好心。”说着我嘿嘿笑起,脸上尽显自豪之意,“怎么样,我刚才这一通表演,可不可以入围年度最佳男主角?”
“可以,回去我就给你颁个小金人,取名叫做年度最佳傻蛋奖。……起来吧,不妨走进去看看,希望走过去就能看到我爸。”
她拉了我一把,我就从地上爬起来,整理了一下乱七八糟的装束,和水风轻一起望右边那条道走去。
“傻大帽,跟我说说,你刚才这一通表演,心里面到底是怎样打着你的小算盘。”
“我说水姑娘,你脑瓜子比我还要好用,不可能不明白这道理啊。”
“我就是不知道,你赶紧跟我说。”
我看她说话那表情,觉得这丫头是想满足一下女性固有的虚荣心,就跟她娓娓道来:“我这么卖力地装疯卖傻,肯定是想试探下那‘鬼玩意’是否真是安好心,毕竟走到这节骨眼上,更是需要小心谨慎。但是那‘鬼玩意’跟透明的一样,咱们根本看不到,完全无从辨别、完全无从判断。我就想,这一路上它三番五次地摸你,要么就是耍咱们,要么就是对你更加上心一些。……话说那‘鬼玩意’,没有摸你身上其他部位吧?”说着我就一顿。
“没有。你看我这脸不红心不跳的神情,就肯定没有。”
“那倒确实。”我继续补充刚才的话,“我就心想,既然那鬼玩意三番五次摸你,不摸我,有可能是对你感兴趣。还有刚才那一大团水凑到你脸上的时候,我以为那‘鬼玩意’是想对你怎么地,就把你推开,把我的脸凑上去顶着,谁知它不买我的帐,硬是想凑到你脸上。后来那‘鬼玩意’在地上画了一个大箭头,我才知道那‘鬼玩意’三番五次把水凑到你脸上,就是想让你看它画箭头,未必是想让我看。这个时候,咱们又被那‘鬼玩意’整得踌躇不定,不知道左边右边哪条道才是正确的路。在这个节骨眼上,那‘鬼玩意’突然跑出来用水画了一个大箭头,想必有很大的蹊跷在里面,要不然这一路上跟着咱们,其他时候不指引,偏偏这个时候来指引。既然它作了指引,不管安的是好心还是坏心,起码能说明这左右两边的路是分开的,不太可能汇合到一起,要是能汇合到一起,那它跟着咱走,接着摸你就完了,何必用这种方法来向你作提醒。所以对于咱们来说,走左还是走右,失败的几率各是百分之五十,如果失败了,很可能又会踏入另外一重世界。于是思考再三,我就打算试探一下那‘鬼玩意’。如何试探呢?我也没有好办法,只是觉得它是有意指引你,既然是有意指引你,那就有可能是关心你的。既然如此,那我就假装伤害你一下,那‘鬼玩意’不是可以把我砍刀弄飞吗,不是可以把我手脚缚起来吗,想必也能阻止我伤害你。只要它有意阻止我伤害你,那就应该是关心你的,如果无意阻止我伤害你,那应该就是居心叵测的。没想到害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被你踹了几脚,直至到了用石头砸你的时候,那‘鬼玩意’才真的出手了,直接把我放翻在地。不过我还是不怎么肯定,又接着试了两次,那‘鬼玩意’都把我这张脸抽得生疼。三次试探过后,我心里自然也就拿下主意了,那‘鬼玩意’是真关心你,知道吧,是真关心你,一点都不关心我,他娘的。”说这最后一句话时,我把声音都拔高一大节,好让水风轻满足一下虚荣心,“并且经过此番试探,我觉得这‘鬼玩意’极有可能跟你汤叔叔是同一路,并且八成是个男的化身。”
“如何见得?”水风轻只顾抿着嘴笑。
“在青铜古城中时,你汤叔叔给了你一卷地图,在这地方,那‘鬼玩意’又给你画了个箭头,二者的心思都是如出一辙,所以我认为,这‘鬼玩意’即便不跟你汤叔叔是同一家,也肯定是同一路。”
“这点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你为什么觉得那玩意八成是男的化身。”
“从那溪涧中走来,这‘鬼玩意’三番五次摸你,根本没摸我一下。还有,刚才我假装伤害你的时候,它抽我的力道非常猛。”
“好吧,继意淫幻灭综合症之后,你的吃醋抑郁综合症又犯了,然而你的这个说法未必就是真命题。”
说话间,我们已经走进了那谷体之内,小道宽两米左右,两边都是由石灰岩巨石构成的壁体,高度很高,目测有四五十米,越往上越狭窄,有的地方左右两边崖体搭在一起,把天空都遮得只剩下一条缝。地上布满了荆棘蔓藤,长势颇为茂盛,腐败的枝叶软绵绵地堆叠着,真的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一路走过去,道中并未碰到任何惊险,只有几个山鸮、野鸦之流拍翅惊空,陡增几分恐惧之意。约莫走得三四十分钟,还真的从另外一边出来了。出来之后,眼前情景跟里面大不相通,里面古旷之意甚为浓厚,而外面则满布生机勃勃之景。古木参天自也在所难免,但地上植被更多的是野草、蕨类、灌木之流。
走过一片由蕨类植物覆盖的平地,又下了一个陡坡,突然又见到有溪流自林间流了出来,想必就是我们一直在跟踪的那条不假。顺着小溪向下而行,野草稠茂可及膝盖,有的地方烂泥堆积,一脚下去直接没至足踝,当真是举步维艰、步步吃力。如此跋涉了十来分钟,水风轻猛的把我拽住,打了一个嘘声手势,叫我不要出声。接着她就把手拢在耳朵上,凝神屏息、静静倾听。听得两下,欢天喜地地叫道:“娃娃鱼……傻大帽……是昨天早上咱们围起来的那几条娃娃鱼。”
我心下一喜,也学她这样听了一小会,果然是有娃娃鱼的叫声隐隐传来。可能是叫得久了,已经呈现出油尽灯枯、声嘶力竭之态。“他娘的,终于要走出来了,看来那‘鬼玩意’果然是待你不薄。”我高兴地说。
“是啊,娃娃鱼还在,很可能我老爸还没来过,如果来了,那几条娃娃鱼有可能就会被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人收走。但愿如此,这鬼地方一进去就会被困住,希望我那英明神武的老爸千万不要冒冒失失地跑进去。”
这么一说,脚上就更有劲了,一时间倒也感觉不出困乏来,只顾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越往前走,那娃娃的叫声就越听得明显,溪内的地势也逐渐趋于平坦,水草烂泥渐少、糙沙粗石渐多,水流也越来越深。等地势逐步变得狭窄了,我们才找个豁口从左边溪岸爬上去,一爬上去,果然是好熟悉的情景,古木掩映、浓荫遮天、藤曼牵缠、蕨类遍地。正是昨天刚入林时的情景。心想我们昨天从这一片区域走过,马老头是拎着砍刀在前面开路的,路上应该会有草木被割或被折的痕迹,就小心翼翼地边走边找,然而竟是一处鲜明的痕迹都找不到。只是看到有的地方矮木被砍断,早已干枯老死,有的地方蕨类被割平,也早已是枯萎将腐烂,找到的所有痕迹,都是老旧痕迹,没有一处是新鲜的。看着眼前的情景,我这心里又不自禁地发起毛来,这绝对不是我们昨天割倒的草木,就一天多的时间,绝对不可能枯萎成这个样子。难道这鬼地方早就有人来过?哦,对了,我昨天早上追赶水风轻,从大河上那钢索上滑过来的时候,发现那钢索在古木上勒出来的痕迹也不是新鲜的,那索道架起来已有一些时日了。看来这鬼地方,早就有人跑进来过了,马老头还口口声声说无人问津。
话说就在我这么想着的时候,猛的觉得脑袋上被敲了一下,接着脖子上又是被吹了一口气。此时我攥着水风轻,她跟在我后边走,我就问她:“你刚才敲我脑袋了吗?”
“没有啊。”她一本正经地答道。
“你向我脖子吹气了?”
“没有啊。”
“难道……是那‘鬼玩意’还跟着咱?”
一时之间,我俩的神经又绷了起来,虽然从表面看来,这‘鬼玩意’好像并无伤害我俩之意,但老是这么冷不丁地在你身上凿两下,还是会让你冒出一身鸡皮疙瘩的。也不管这地上莫名其妙的老旧痕迹了,只管向着平地,循着娃娃鱼的叫声往前走。
走着走着,我脑袋又被敲了一下,比上次敲得还要重些,脖子上又被吹了一口冷气。我这心里就有点不乐意了,难道那‘鬼玩意’是个红孩儿?托塔天王没把你看管好,老是这么调皮捣蛋,伤又不伤我,就这样没来由地跟我耍着玩。
“那‘鬼玩意’摸你了吗?”我回头问水风轻。
“没摸啊,从画那箭头之后,就一直没摸过啊。……难道现在摸你了?”
“他娘的,不是摸,是打,再打再打,我这脑袋要被打出一个洞来了。”我叹了一口气,“现在看来,那‘鬼玩意’真的是个男的化身,要是女的化身,像我这样帅得一塌糊涂的人,怎么可能连摸都不摸一下,而一个劲地打。你说你摸两下会怎的,反正别人又看不到,就天知地知你知。”说着我就笑了起来,被那玩意戏弄得久了,心里居然一点害怕的意思都没有。
“你不要臭美了,老说这种下辈子才能跟你沾边的话。”水风轻白了我一眼。
我就继续往前走,如果没有走到另外一重世界中,估计前边就是出口不假。不料脑袋上又被狠狠地凿了一下,这下打得非常重,差点疼得中枢神经系统都颤抖起来。我就赶紧扬起攥着登山杖的右手,摩擦生电似的在脑袋上摩。按理来说我应该非常生气才对,但那‘鬼玩意’无非就是一缕空气,要是吃力不讨好地跟它生气,跟前一阵拎着砍刀在空气中乱捅有什么两样。
我就把登山杖交到水风轻手中,双手抱拳作了个拜托的架势,口中念念有词道:“大仙,我知道你眷顾水风轻,非常讨厌我,但是你也不能老是这么打我,我这脑袋本来就被那大金雕差不多给弄残了,你再这样打来打去,非得打成痴呆不可。咱俩走到这里,应该是离出口不远了,这一路上非常感谢您的指引,但你也不能一直跟着咱。正所谓鱼在水里、土在地下,每一样物质都该有它自己的存在环境,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我看不如咱们就此别过吧。我们会一直记住你的好,回去会给你烧多多的纸钱。”
我也不知道那‘鬼玩意’能不能听得懂,反正就只管这么乱七八糟地说,说着说着连水风轻都想笑了。我话刚说完,脖子上又被吹了一通冷气,也是比先前要猛烈得多,在阳光照射下都感觉冷得打寒颤。就忍不住回过头去看,这一看,我这灵魂当真是如烟囱冒烟那般从七窍中忽忽飙了出去。声嘶力竭地大叫一声:“我****姥姥的啊!……”。
水风轻也被我这魂不守舍的表情给吓呆了,赶忙回头去看,也是灵魂出窍一般大叫了一声,几乎把天上的云彩都震得颤抖起来。
紧接着,我这脑袋就真真正正地彻底断线了,身子一软就晕倒在了地上,朦胧目光中,水风轻也是身子一软,就压在了我身上。
那‘鬼玩意’就这样近在咫尺,几乎是贴着水风轻的脊背而站立。
那‘鬼玩意’原来不是绝对的无形,也可以看得见,通体俱黑,身形比我俩都要高。
那‘鬼玩意’长发飘飘、风姿妖娆,正是我在瀑布上喝水时看到的那个人影。
那‘鬼玩意’脑袋左后方的天空上,此时一轮太阳褪去燥热,正在泛出淡淡红光。
那‘鬼玩意’身着一件黑色的大披风,胸口及袖子上都缀有鲜红的蟒蛇纹。
那‘鬼玩意’,正是大山洞壁画上的那个九幽玄女。在她的右手边,正站着一只伞盖般大小的大乌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