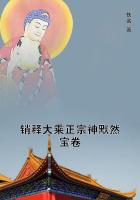不料就在转身之间,一个身影突然毫无征兆地站在她前面,大喝一声“愚蠢至极”,吓得她踉跄连退数步。她定眼仔细一看,那人赫然就是之前阴魂不散一样的老妇人。她害怕得手脚都麻痹了,腿一软便即坐倒在地。“怎么……怎么又是你?”
老妇人歪起脖子看着她,脚跟一抬,像鬼一样缓缓飘到她跟前。“你好愚昧!我好不容易才把你带离那个鬼地方,你怎么又要自投罗网?”年沐盈想跑,但四肢就如注了铅一样,连手指也抬不起半根。“到了这种时候,你还顾虑着什么仁义道德?咱们都已是泥菩萨过河,亏你还有这心思!”
“我要做的事,啥时候轮到你来管?”年沐盈强作镇定,其实内心怕得要命。老妇人瞪着一双阴森愤怒的眼睛,撅起半边嘴唇,“现在已由不得你作主了!你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向你传送危险的信号,而你却置若罔闻。我不会由着你的愚昧,害咱们坠入水深火热之中!”
“是生是死我乐意,你有什么权利干涉?”年沐盈一面说,一面专心致志让自己站起来。她试图夺回肢体的触觉,然而每投放一分力量,却总是无缘无故地消失,就像中风患者一样。“难道你还没有发现,你的身体已不听你的指挥了吗?”老妇人已洞察她的想法,“那是因为,连你的身体也觉得,你不配当它的主人!”她话音刚落,年沐盈便发现身体能活动了。可是——
自己的一举一动,已完全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
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从地上爬起来,就像之前看着自己杀人却无能为力一样,身体完全不受控制。“看啊!”老妇人说,“你的身体已经接纳我了。它已经认可我是它的新主人。如今唯一在负隅顽抗的,就只有你那冥顽不灵的意志。放弃吧!带着你可笑的想法,永远沉睡,别再醒来了!”
年沐盈只觉得大脑也开始麻痹,连思想亦越发控制不住。她感到眩晕,像酣醉一般,眼前莫名闪过一幕幕儿时的影像。她看见小时候的自己坐在秋千上自言自语,那是她无聊时最喜欢玩的游戏之一,假装有一个朋友在自己身边和自己说话,就像自己跟自己下棋一样。最厉害的时候,还能跟自己吵上一架,甚至陷入冷战。
直到此刻,她才终于明白,自己根本不是碰上什么妖魔鬼怪,而是患了严重的多重人格。她的大脑中产生了另一个意志,而这个意志,如今已强大得能公然跟自己争夺身体的主权。
只是这种觉悟来得太晚了。她的神志是那么虚弱,如病入膏肓般不堪一击。她再也不能对身体下达任何命令,尤如被困在一个坚硬牢固的玻璃箱中,虽能看能听,却已沦为台下观众。她能洞悉“自己”的每一个想法和念头,却无法左右。她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拾起地上的背囊和火把,头也不回地走了。
一路上,她看着“自己”经过了不少地方。她知道“自己”是在往回走,去寻找聂纪朗。她清楚明白“自己”在盘算些什么——找到聂纪朗之后,要想尽办法与他重修旧好,再利用他的人力资源活下去。她为“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感到羞耻,甚至觉得被侮辱了,却无法阻止“自己”实施。她在呐喊,她在抗议,但也不过是妄图用一颗小石子去阻止扑面而来的巨浪。
她的思想只能在大脑某个角落苟延残喘。那是个最不起眼的地方,就连她自己亦甚少问津。这里所承载的,大多是她不愿回首的过去。这是她用来埋藏伤痛的地方,她向来拒绝访问这里每一条能引起她剧痛的神经。然而她不知道,她的意识已被挤压在这里,无处可逃。
她仿佛再次听见无数人朝她谩骂,说她人尽可夫;又仿佛看见血淋淋的婴儿,在向她求救。还有许许多多冷嘲热讽,数不尽的尴尬场面,一道道自尊伤痕和早已放下的心理包袱,在此刻不约而同围着她公转。她不愿去想,却被迫着想,各种念头根本不需经她同意就自出自入,而且还被放大了许多倍。
在孩提时撒的小谎告诉她,她是个诚信全无的无耻小人;在儿时撒的小野告诉她,她是个粗鄙顽劣的人渣败类;考试时作弊,让她感到无地自容;偷用母亲的口红,让她觉得自己淫邪放荡。她有生以来所背负的阴暗,不论大小,全如洪水般泛滥,像雪崩般倾泄,把她可怜的意识冲击得支离破碎,自觉就算五雷轰顶,也罄竹难书。
被无限放大的罪疚感让她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尽管她已然如此。但她仍竭尽所能,以仅余不多的理智让自己保持清醒。她看着“自己”穿过一片树丛,感知到“自己”在盼望着聂纪朗等人尚未离去。她察觉到“自己”的步伐越发急速,甚至还酝酿着哭意,只待一见聂纪朗就扑上去痛哭,以换取同情。
可是,“自己”的如意算盘散了。那儿再也没有一个人,就连那个火堆,也让人用一层厚泥盖了。
“自己”呆立在那里环顾四周,年沐盈知道,她在寻找什么蛛丝马迹,以判断聂纪朗众人离去的方向。年沐盈不禁有点窃喜,这亦稍稍冲淡了她的罪疚感。正当她以为“自己”无计可施的时候,“自己”却忽然弯下身去伏在地上,掏出手电四处探照。一个念头如闪电般闯进年沐盈的意识中——“自己”在寻找他们的脚印。
年沐盈不断在祈求,“自己”什么也找不到。她甚至希望突然飞来一场杀身横祸,让她与主宰着自己身体的老妇人同归于尽。过了片刻,“自己”从地上站了起来,似乎并未发现什么——起码年沐盈感知不到“自己”有什么头绪。可是,她却感觉到一股强烈的嘲意。
“从来就只见过人们祈福,”
“自己”站在那儿自言自语。
“却没想到,这世上竟然有人祈祸。”
年沐盈大吃一惊!原来,不光自己能感知到老妇人的想法,就连老妇人,也明明白白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自己”再也不说一句话,只闲庭信步地在树丛中穿梭,举着手电四处寻找线索。但年沐盈清楚感知到,“自己”在想什么。
别再负隅顽抗了——“自己”在心里想着——你就只剩下那丁点可怜的意识,连冷热痛痒都感知不到,于我而言,你就像一只在我耳边拼命扇动翅膀的垂死的苍蝇,对我一点儿威胁都没有。你还是死了那条心吧。
年沐盈这才察觉,“自己”是在透过思想来和自己交流。当她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段信息又转瞬而至。
沉睡吧。这世界、这身体已经跟你毫无关系。我说过,把一切交给我,你就能脱离苦海,回归平静。
这时,“自己”忽然止住脚步,灯光送处,是一片草坪,有几株小草泛着它本不该有的黄光。找到了——年沐盈和“自己”几乎是同一时间里意识到同一件事,但彼此心境却南辕北辙。
她抹下小草上的黄光,闻了闻,不觉扬起笑容。年沐盈虽然闻不着任何气味——因为她的鼻子早就不再属于她——但她仍能透过“自己”的思想得知那是何物。
汽油。准确地说,是聂纪朗用来制造火把的汽油。
她看着“自己”举起手电往较远处照,只见草坪上,隔三差五就会看见点点黄光。那兴许是聂纪朗用来盛汽油的罐子漏了,也可能是他故意留下的痕迹,以便自己改变主意的时候,能循着痕迹找到他们。
“看啊!连老天爷都在帮我。”年沐盈感受得到“自己”的欣喜,她却郁结得心乱如麻。尽管她本来就打算回到聂纪朗的身边,尽管“自己”也有此想法,亦尽管事情正朝着这想法发展,可她却丝毫没有为此而高兴。因为一切都变了,自己变得不是自己,她再也没有任何资格称呼自己为“我”了,“她”已经取而代之。虽然以第三人称称呼自己是一件极其怪诞,不可思议的事,可这就是事实。
如果身体也算是财富的一种,那天底下最为匪夷所思的抢劫,恐怕莫过于此。
两个截然不同的意识,共处在一个体积不足半立方米的身躯里,有着各自的想法,却又为对方所洞察。谁又能说得清,他们彼此到底是什么关系。年沐盈忽然意识到,如果傀儡是一种强行将一个意识嫁接到另一个身体的过程,那如今自己这个状态,会不会就是被傀儡后的状态?
不料这个假设连“自己”也认同了。年沐盈能清楚感觉到,虽然“自己”对此并无太多想法,但那种打心底里的认同,是如此强烈地传递到她的意识中。这也是自老妇人出现以来,她们头一次想到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