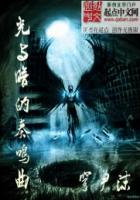另外两名男子见情况不对,忙说:“您请息怒,我们马上去办。”话没说完,两人已推着推床去了。为严黄包扎的女子知道自己说错了话,手都抖了起来。严黄捏住她的下巴,眼中的阴冷不见了,却仿佛有团即便抛到大海里也无法熄灭的欲火。“你还是人类吧?看上去蛮漂亮的。”
那两名男子在过道上找了好一会儿,方找到严黄口中所说的身体。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沉得像灌了铅一样的海婴搬上推床。其中一人轻声揶揄着,“这些家伙真是走过地磅也要交费。”另一人则提醒他小心祸从口出。随后,两人推着推床径回HC317。但当HC317大门打开的那一刻,他们都傻眼了。
严黄正趴在那为他包扎的女子的身上,快活得大汗淋漓。他手上的伤甚至还没包扎妥当,只一边埋头猛干,一边把手放在身下女子的面前,让她继续包扎。而另一名女子就只能傻傻地站在旁边耸拉着脑袋,连看都不敢看一眼。
被严黄压在身下的女子泪如泉涌,却不得不继续为他包扎伤口。两名男子只能装作什么也没看见,手忙脚乱地把推床上的海婴抬了下来,安放到另一张椅子上,又接上检测仪器,心不在焉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语无伦次地说着自己该说的话。
“这个……那个……已经好了。”
“好了就……就那个吧。”
听着严黄的喘息和女子不知是出于悲哀还是快慰的呻吟,他们不由自主地咽着口沫,还悄悄扭头偷看那幅活春宫,生理早就有了反应,只恨自己没有参与的资格。两人正偷看间,与另一名女子对上了眼神,一轮六目交投之后,都不好意思地避开了彼此的目光。他们无不口干舌燥,心中都百般煎熬。其实说白了不是他们不想,而是他们不敢,因为蜂巢内明令禁止人类之间的一切性行为,即便是其中一方已被海婴窃脑。但是相比之下,这种规定对于后者却是宽松得多,简直形同虚设。而倘若双方都是未被窃脑的人类,且又被发现,就只能乖乖地等着死神来点名。
作为旁观者的两男一女,就像被点了穴一样兀立在一旁,等待着严黄完事。他们也不知等了多久,只知道严黄打了个冷战,然后提起裤子,斜眼睃着自己。忽然大门打开,一人冲了进来,气喘嘘嘘地看着这一室五人。
“哈葛托你在干什么?”来者正是罗建明。他扶起被严黄侵犯过的女子,见她的潜水服竟被人从腰间撕开,下身已然一丝不挂,忙脱下自己的衬衣,为其遮羞。罗建明强忍着怒气,尽量用缓和的语气跟严黄说:“你不是答应过我,不会对我的组员做出任何侮辱性行为的吗?”
“谁说我侮辱她了?”严黄挑起眉毛,侧眼瞪着罗建明反问,“你都不知道她有多渴求,我为了不让她一时冲动与别人交配,害她丢了性命,才义不容辞地救她于水深火热之中。这能算是侮辱吗?”罗建明从来没见过严黄如此轻佻,如此强词夺理,顿时觉得不妥,“你……你不是哈葛托?”
严黄冷冷一笑,倏然出手掐住罗建明的咽喉,连推带撞将他压在墙上。“是谁赋予你说话如此放肆的权利?是他吗?”严黄伸出手指,指着其中一个安坐在一旁的海婴。罗建明才顿时察觉,原来那儿坐着两具海婴的身躯。“看来哈葛托真把你给宠坏了,不给你点教训,你还真是目中无人。”说罢,就从身旁提起一个潜水用的氧气瓶,举起就往罗建明头上砸!
在场的人见他下手如此凶狠,都吓得惊叫。罗建明本能地缩起脖子、闭目咬牙。他不能去挡,也不能避开,除了硬生生接下这一击,他毫无选择。只因他一旦让海婴不高兴,死的不一定会是他——毕竟他还有很大的利用价值——但他的组员,就必定会成为海婴泄愤的牺牲品。这种事情在罗建明四年前的日记中几乎就是主要剧情。
然而他等了半天,预期的一击却并没有发生。他缓缓睁开眼睛,看见严黄举着氧气瓶的手停在半空,仿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挥不动那个氧气瓶。双方僵持良久,严黄终是万般无奈地放下氧气瓶,愤怒间挤出一丝阴险的笑容,“行了行了,打狗还得看主人,我不打就是了。”说着,连掐住罗建明脖子的手也松开。
“姓罗的,”严黄一面说一面从控制台上拿起早就准备好的木马仪,安坐在两具海婴身躯正前方,“我奉劝你一句,作为一条狗,就该好好想一下,狗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接过旁人递过来的口腔扩张器戴上——那是用以预防海婴归脑后,人类咬舌自杀的工具——随即又戴上窃灵镜,四条中空钛合金属线刺进他眼眶皮肤的时候,他还痛得吸了一口气。最后,椅子弹出金属扣,将他四肢和颈项都牢牢固定。
众人见他准备就绪,无不闭目以避。待一阵青黄难辨的强光闪过,那两具海婴身躯中的一具,已从椅子上缓缓站起。“记住我说的话,否则你主人都保不了你。”他丢下这句震得人牙齿发酸的话,便离开了HC317。过不多时,木马仪又再强光乍闪,接着另一名海婴亦都活动起来。
他看着比方才的海婴壮硕不少,肌肉更为发达,线条更为硬朗,颊毛更为浓密,宛如一头精钢铸造的狮子——除了那像乌鸦一样的面孔。他从椅子上一站起来,罗建明只仅仅到他腹部。而他就是严黄一直以来的扮演者,海婴听涛氏族的民族英雄,疾游氏族酋长的乘龙快婿,立宪派忠诚的拥护者——哈葛托!
“好久没从这么高的角度去看你了。”他的声音仿佛像竖琴的低音弦被弹拔一样颤鸣,浓密厚实的颊毛颤动得如泛起涟漪一般好看,但依然震得人耳膜发痛、牙齿发酸。只是罗建明亦无可否认,这是他听过最为悦耳的海婴的声音。
“怎么了?”罗建明捂住耳朵,打趣地说,“仰视我让你很难堪吗?”
哈葛托那双像太阳一样火红火红的眼睛突然间柔和了许多,仿佛站在他跟前的并非是一个人类,而是他暌违多时的故友。他伸出左手,三根如钢锥般的手指拨弄着罗建明的头发,“你的头发好像又白了许多。”
“这不恰好证明了我为了海婴族的大业是多么鞠躬尽瘁吗?”罗建明笑着说。
哈葛托脸上没有笑容——准确地说是谁都别指望海婴那张呆板的乌鸦脸能展示出什么笑容。然而海婴却有自己一套表示高兴的方法,那就是颤动颊毛。
据罗建明所知,颊毛在海婴族的社会里,有着非凡的意义,几可视为海婴的第二张脸。从审美角度出发,颊毛的地位相当于人类的头发,其光泽和色泽,都是至关重要的审美标准之一。除此之外,颊毛还代表着海婴的威严,其意义类似于人类的胡子却又远远超过胡子。在社会地位相近的海婴社交中,颊毛越浓密厚实者,往往拥有更高的话语权,从而引申到长幼尊卑的观念中,发展出一套凭颊毛排辈分的文化共识。迷信的海婴甚至认为颊毛越旺盛,其将来之成就则越高。
除了遵从上述文化共识之外,海婴还会讲求颊毛的个性化。他们会编织或剪裁出不同形状、不同纹路的颊毛,雄性藉此展示魅力,而雌性则展示自己如何美艳动人、心灵手巧。在一些重要的社交场合,海婴若不精心修理过自己的颊毛,除了不美观之外,还会被视为对别人的不敬。
以人类的审美观来看,海婴大多体态修长健美,而个性化颊毛是否与身体线条相互辉映,就是其中最大的学问。加之海婴氏族繁多,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流行文化——颊毛的形状是海婴赖以判断彼此氏族和血统的标准之一——继而发展出不亚于人类发型文化的种族特色。如果海婴也会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个性化颊毛恐怕是第一个登上名录的项目。
然而,颊毛之所以如此倍受海婴的重视,除了外观原因,更重要的是那同时是他们表达情绪的工具。
站在人类的角度,情绪可以透过神情、语气和肢体动作来表达。与人类一样,语气和肢体动作也能体现海婴的情绪,唯独神情是他们那张十分抱歉的脸所不具备的。因此,颊毛就成为他们用来告诉别人“老子很生气”或者“奴家很悲伤”的重要工具。而颊毛的个性化,则使海婴更能如己所愿和传神地表现出各种情绪。
就像哈葛托一样,他把颊毛修剪得层次分明,待自己高兴时,颊毛就会随着鳃颚喷涌的气流,荡漾着如平湖投石般的涟漪,叫人看着舒服。反之在生气时,就会如惊涛骇浪般翻涌,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愤怒。
据闻,海婴的颊毛若配合尾巴的挥舞,能表达出丰富细腻程度不亚于人类诗歌的情感。但这对于罗建明,或者任何一个人类来说,都只能算是对牛弹琴。人类能解读出基本的喜怒哀乐就已经相当不错,就别指望他们能从一撮毛中读出什么白居易、莎士比亚。
罗建明收起笑容,目光落在刚才被强暴的女子身上,她正瑟缩在一张椅子上抽泣。他猜想另外三人中的两个男人心里必定会暗骂:明明压抑了那么久的性X欲得以宣泄,明明在整个过程中享受得大汗淋漓,偏偏还要装出一副受了奇耻大辱的模样,还要博得别人道德上的同情,吃了大餐还想赚人安慰,算什么东西。
当另一名女子上前安慰她的时候,两个男人脸上鄙夷的神色更浓,就好像在说:惺惺作态,你恨不得刚才被胖子趴在身上的就是自己。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严黄——自海婴意识离去后就一直昏迷不醒,只有偶尔强烈的抽搐说明他本人的意识在逐渐恢复。
“为什么会这样?”他神情严肃地看着哈葛托,并指着昏迷不醒的严黄问,“为什么纳查瓦会在他身上?他不是一直在酋长身边做事吗?怎么会突然来这里?”纳查瓦就是之前的海婴的名字。
可能对于罗建明来说,纳查瓦作为酋长的参谋,不好好待在酋长身边出谋划策,反而纡尊降贵,枉顾这个他们认为“充斥着人类恶臭”的地方,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而让罗建明更倍感不安的,是这名海婴还是立宪派内的右翼保守份子——那可是一群主张不可善待人类的家伙。
与哈葛托一样,纳查瓦也来自听涛氏族,并效命于立宪派。然而作为右翼的他,在对人类和对宗氏派的立场上,却与左翼的哈葛托有着严重的分歧:
右翼认为,人类可以用之弃之杀之,唯独不可信之。因为人类是一群阴险狡诈的生物,“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正是这群生物总结出来的座右铭。右翼时常提醒族人,只要读一下人类的历史,看看他们的殖民者是如何对待被殖民者,就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对待人类只能像人类对待人类那样,并且要比之更甚,才免于重蹈人类的覆辙。而对待宗氏派,右翼则认为双方都必需要有求同存异的共识。毕竟彼此是同类,内斗不但会使亲痛仇快,还会让苟延残喘的人类得以喘息之机,埋下隐患。至于两派在理念上的分歧,只要彼此努力寻求,就必然会找到比内斗更好的处理方法。倘若冥顽不灵,海婴的明天,就将会是人类的今天。
在对人类“阴险狡诈”的解读上,左翼基本与右翼见解一致。然而左翼却认为,即便人类狡猾得连一根头发也不可信,他们身上却有样东西但信无妨,那就是他们的特质。左翼深信,只要找对方法,没有人类是不可利用的。比如某人贪生怕死,可以死恫吓之;比如某人见利忘义,可以重利诱之;比如某人重情重义,可以情义困之。再不济,海婴还可以窃入他们的大脑,取而代之。所以归根结底,人类不过一件活工具。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建立圈养区,一方面提供立宪派人类资源,一方面将人类对海婴的仇恨引向宗氏派。
与之相反,左翼觉得真正值得怀疑的,是右翼对立宪派的忠诚。因为右翼时常以“彼此是同类”为由,与宗氏派一直保持着暧昧不清的关系。左翼甚至认为,潜伏在派内的奸细以及历来的叛徒,都是出自右翼势力。这一主张时常导致派内关系紧张。而对于宗氏派,左翼的态度可谓十分强硬和激进。他们认为,宗氏派是顽固的极权独裁者的结合物,不可能被改变,只能被推翻,并且要尽可能地利用人类的人力和科技,抢占陆地资源,才有可能将宗氏派从权力的宝座上赶下来。
如此种种分歧,自然而然地迫使纳查瓦和哈葛托走向对立。然而,这对政敌却是同父同母的胞兄弟——纳查瓦是哈葛托的兄长。
罗建明盯着哈葛托,等着他回答自己的疑问。哈葛托两眼的红光褪去,回忆着方才纳查瓦窃入严黄的大脑时,处于同一身躯的自己曾大致读取了他的记忆。原来,纳查瓦此次是受到听涛酉长的直接委任,前来上任巢监。巢监是蜂巢最高长官的职位,负责管理蜂巢内一切事务,如日常维护、职能分配、任务指派、人员调动、委卸职务等,只要是隶属蜂巢编制的,无论或人或事或物,都由他统领管辖。这自然包括了作为圈养区联队队长的哈葛托。
此外,巢监更是酋长直辖官,日常只向酋长一人汇报。他在蜂巢内所行使的一切职务权力,均可以视为酋长亲行,违抗巢监无异于违抗酋长。而与重权相对应,巢监必须承担蜂巢内一切责任。
对此,罗建明不禁萌生出另一层忧虑。据说听涛酋长为了听取最客观的建议,刻意安排让左右二翼各占他的参谋半席。然而,酋长此次委以重任于纳查瓦——一个派内右翼的活跃人物——这不正正说明,酋长的立场已逐渐右倾吗?哈葛托接下来的话,再次证实了罗建明的猜测。
首先,是酋长开始对派内左翼的亲猿者——即指与人类过于亲密的海婴——感到不满。其原因不言自明,又是右翼在酋长耳边煽风点火。故酋长此次委派纳查瓦出任巢监的首要任务,就是监控蜂巢内的亲猿者,力图消削亲猿气氛,并代表立宪派主席——而非听涛酋长——重申和强调人类在海婴内部的工具地位,以劝诫一众海婴族不可混淆身份。而首当其冲要受到纳查瓦“劝诫”的,恐怕就是他的胞弟,亲猿者的代表人物哈葛托。
其次,是哈葛托在圈养区中名声过盛。只因他是疾游酋长的女婿,而外派到圈养区的海婴又多是疾游氏族者,这帮疾游海婴不但对他十分恭敬,并且以他马首是瞻。这直接导致蜂巢对立宪派在上海地区的数百个圈养区的领导地位被削弱,而哈葛托却一言九鼎。这不管是对于听涛酋长还是立宪派主席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因此,纳查瓦空降巢监的另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加强蜂巢对圈养区的领导力,并提醒那些疾游海婴们,圈养区是立宪派的战略单位,而不是他们疾游氏族的领地。此外,作为兄长的纳查瓦也要提醒弟弟,他只是娶了疾游酋长的女儿,并不是成为了疾游氏族的海婴,要注意与疾游氏族之间的距离。
最后,就是与罗建明等以人类身份为海婴效力者息息相关的问题。由于哈葛托与罗建明关系亲密,且罗建明的团队又确实屡有贡献,这导致在蜂巢内的人类过着些与这时代极不相符的优质生活。他们日不愁食,夜不愁眠,夏不愁暑,冬不愁寒,比之外派的海婴,有如贵族一般,其权利已经严重超越了作为一个工具身份所应该拥有的,久而久之,这帮工具极有可能会忘记了自己的角色。而纳查瓦就是来提醒他们的。至于是如何提醒,纳查瓦刚才便已向罗建明言明——
“作为一条狗,就该好好想一下,狗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听完哈葛托的话,罗建明早已忘了自己的耳膜被他的声音震得嗡嗡作响。他捋起半黑半白的头发,看着身旁的两男两女,而他们亦惴惴不安地看着自己。这些人都是他团队的一分子,有几个甚至是他在事变后亲自救下的。他们跟着自己,原本好歹混得个衣食无忧,但如今好日子只怕到头了,往后若能保得住小命,已是天大的造化。
所以他心中暗暗盘算着——有些人和事,似乎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