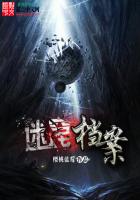我几乎有一种错觉,我好像在那一瞬间看到了之前那个女鬼姐姐的影子在媋姝的脸上浮现出来。但是媋姝只是用手捏着符,稍微往上提了一提,便放下了。但即便是这样,我得心还是提到了嗓子眼。
“你这符揭不下来。”媋姝扭头看看我,接着说:“我在家的时候就试过,现在上面的字都快没有了,但是还是揭不下来。”
我赶忙把杏放在一边,然后跑过去检查那个坛子上面的符,果然没有丝毫损坏的痕迹。
“这符本身应该也被下了很厉害的咒术,我师父以前在山上摆大阵的时候画的符最厉害的都是水火不侵的,像这种揭不下来的,不是很稀奇,但是不知道是下咒了揭不下来,还是用的浆糊比较好。”
我说完,就从我身上把信封拿了出来,从里面掏出那张黄灿灿的符,贴到了坛子上。
“你现在再揭揭看。”我贴好符,然后对媋姝说。
果然。媋姝用手轻轻一拽,原先的那张符就被她揭了下来。一旁的杏看的兴起,执意要我把这张被接下来的符送给她作纪念。我很不耐烦的把符给了她,问她之前没用光的符都让她拿去玩了,这次还要,要那么多回去当女道士么。她的回答让我很无奈,说这是用过的,纪念意义不一样。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看来以后的日子可能不会像以前那么悠闲了。正坐着寻思师傅给我这坛子的用意,腚哥就来电话,让回店里上工。
其实事情没有我想的那么复杂,等到我下一次再收到信,已经是三个月以后了。
寄信人依旧是那个名字,陆放。信封里装着的东西一模一样,就连白字条上写的字都一样,甚至我觉得这上面的字可能都是复印上去的。这次大家已经没有太大的反应,只是我一个人回到宿舍把坛子拿出来,换上符。
这段时间关于这个坛子我想了很多,有时候甚至想出一趟远门,去那个信寄出的地方找到那个叫陆放的人,然后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看着上面那个地址,实在太远了,甚至远的我都没有概念在哪,要做多久的车,要走多远的路。眼前的未知经常能够很轻易地就把我阻挡住,就像师父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说的。
“小娃娃,你不适合当道士啊。”
每次想起这句话,我都能想起师傅那个总是在留,但是却一直都留不长的胡子。师傅说,因为他的胡子不长,所以耽误他少赚了很多的香油钱。
把坛子放回衣柜里,就下楼准备回一定来。
一出门发现,下雪了。
感叹一声,要过年了,今年应该是不能跟腚哥一起在这边过年了,要跟着媋姝一起回村里看看,我也好久都没回去了。
临近年关,店里没有什么人,像凤宁这种小地方年过的都比较长,虽然法定假日只有七天,但是基本从腊月二十三往后就没有什么人还在干活了,然后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才算过完年,有些偏远的农村甚至要过完正月人们才开始出来干活。
腚哥一般这个时候就开始安排店里的人回家过年。
虽然我们在一定来干活赚的不是很多,但是也绝对不少,而且腚哥待我们都像自家人一样,尤其是年底,回家的路费和过年的红包是一定不会少的。不过今年似乎有点不一样。
我见腚哥发完了手里的红包,就打发孔老二还有锅巴和小四条收拾东西回家过年,然后又给了杏一个红包,说杏他妈肺不好,这钱是给他妈买水果的。杏接过了红包,给腚哥鞠了一躬,也走了。
我正准备招呼媋姝收拾收拾东西的时候,腚哥拍了拍我,跟我说:“殷天,过年你家方便么?我今年过年想跟你走,去你老家看看。”
我一开始没反应过来,愣了一下,然后一乐,说:“行啊,怎么不行,没什么不方便的。我们村里过年才不像这地方自己家过自己家的,我们都是好几家甚至整个村子聚在一起过,多你一个人就是多双筷子。”我又想了想,然后接着说:“不过你不都是跟你父母过年么,而且奶奶走了,你不留着陪你爸妈?”
“我爸妈去海南旅游过年去了,我不爱去。你方便就好,那我就跟你走了。”说完腚哥就走出了店门,然后给我做了个电话联系的手势,一拐弯就不见了。
我转身进厨房,把腚哥要跟我们回去过年的事告诉媋姝,媋姝正在检查水电煤气,听我说完之后也挺开心,说跟家里打电话说在这里跟我找了个好老板,家里还不太相信,这下好了,正好带回去给村里人看看。
我回到前面看了看自己的行李,早就被媋姝井井有条的整理好了,一个箱子,一个背包。其实我自己的东西没有多少,只是媋姝前几天带着我逛了好几天的市场,买了好多东西让我带回去。说虽然村里人带给我的东西都让她在客运站给卖了,我没吃到,但是我还是得带东西回去给那些七大姑八大姨,我也没注意她都买了些什么,反正最后是满满塞了一大箱子外加一背包。我考虑了很久要不要把坛子带走,最后还是留在了宿舍,不过柜子上面我多加了一把锁。
不一会媋姝从里面出来,自己也背了一个大包,就招呼我往外走。
快过年了,我们俩要出去吃一顿。
等再在客运站见到腚哥已经是两个小时以后了,腚哥比我们先到,倚着售票大厅的栏杆等着我们。腚哥的东西很简单,只有一个拉杆箱。
一直到上车的过程基本都很顺利,春运还没有开始,人也不是特别的多,但是我很机智的拉着媋姝绕过了那个当初要没收她“非法所得”的保安,不然我怕媋姝这次会闹出更大的事情来。
坐在回家的车上,我们三个很开心的说说笑笑,我们俩给腚哥介绍我们村里各种风土人情和趣闻轶事,这时候我才发现,媋姝说的很多地方,很多人,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在我上山学艺和外出闯荡的这几年,那个所谓的“家”已经和我印象里的不太一样了。
我望了望窗外,心里不免产生了一丝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