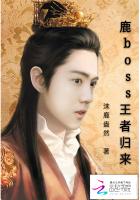翠翠压抑的低泣声就在耳边盘旋,时断时续,听上去那样绝望无助。曲烟烟紧闭着干涩而空洞的眼睛,只觉得胸腔中那颗心已如外面这具皮囊一般麻木僵硬,失去了最后一丝温度。
半个时辰后,冯豹拎着裤子站了起来,开了门,心满意足地哼着小曲,回东屋继续挺尸去了。
翠翠蓬头乱发地坐了起来,表情呆滞,双眼无神。她的衣服散乱地堆在身上,浑身象发疟疾一样抖个不停。
曲烟烟轻轻地叫她:“翠翠?”,连叫几声,没有反应。
她便将那灵牌从身下的柴草中摸了出来,隔空递了过去,柔声道:“令尊泉下有知,看见你这幅样子,也会心痛的……你才劝过我的——日子再艰难,也总要想法子活下去!你自己倒忘了么?”
翠翠缓缓抬头,看到父亲灵牌的一刹那,她整个人顿时撑不住了,扑过来死死抱住曲烟烟,借着滂沱的雨声,痛哭失声。
曲烟烟将灵牌轻轻交到她手上,叹了口气,轻声道:“想不到你竟也是官家小姐出身……”
翠翠用手狠狠捂住嘴,哭得哽咽难抬。“先父原是宝江县令……一场飞来横祸,他莫名其妙牵扯进一桩谋逆的案子,被问了斩……我母亲和姐姐籍没入宫为奴;我几经易手,被拖到人肉市上卖了……”
翠翠瘦骨伶丁的身子不住地发着抖,心中悲苦又不敢放声大哭的样子看上去说不出的凄凉无助。
曲烟烟惊异地抬眼看她。
“你父亲区区一个县令而已……谋逆?!”她双眉一挑,脸上神色不觉端凝了几分。
“不,不不!”翠翠猛烈地摇头,眼中泪如泉涌,“先父一生清正廉洁,效忠朝廷,爱民如子,公务之余只喜养花种菜,他怎么会谋反?谋反作什么?!先父是冤枉的,他是屈死的……”
冤枉,屈死……曲烟烟没吭声。每一个死囚都觉得自己冤枉。不过小小的一介县令,他就算要谋反也没这个实力,想来也许是和哪个心怀不轨的封疆大吏有些关联,因此吃了挂落吧。是和谁呢?曲烟烟凝神想了一会,茫然不知。前世严守宫妃不得干政的训诫,两耳不闻朝堂事,对这些闻所未闻。明渊也从来没有提起过。
即使是现在,她对这些也毫无兴趣。
那包药粉在鞋子里微微地硌着脚。曲烟烟侧耳听了听外面那一阵紧似一阵的风雨声,扭过脸去看着翠翠,一字一顿地问道:
“如果有机会逃走,你可愿意离开你那个畜牲丈夫,离开这冯家?”
“逃走,离开……”翠翠坐在地上,茫然地瞅着曲烟烟,喃喃道:“可是我已经家破人亡,举目无亲,我能到哪儿去呢……”
“远远地离开此地,就算去知书识礼的人家作个粗使丫环,也比在这儿被那些恶徒作践凌辱强百倍吧”。门外雨急风骤,漫天的大雨倾盆而下,曲烟烟凝神听了听院中的动静,低声道:“你既是官家的小姐,想来也通文墨,会女红,挣口饭吃总不至于太难。”
“可是我……我……”翠翠无力地张了张嘴,后面的话却没有说下去。恐惧,茫然和羞惭让这个十四岁的小姑娘最终深深地低下了头,呆愣愣地瞅着自己的脚尖,两手抱膝,瑟缩成一团。
曲烟烟注视着她那张瘦成一条的没有血色的小脸儿,以及她眼中那凄恻惶恐的目光,微微蹙了下眉头,亦把下面的话咽回了肚子里。
原本的打算是:翠翠在冯家比自己要自由一些,若她决意和自己一同出逃,就让她趁外出的机会,想法子偷偷雇辆车在村口接应——如果没有坐骑,仅凭一双肉腿想要成功脱逃,那基本上等同于痴人说梦。
可眼下瞧这小姑娘的样子……只怕她没有这个胆量啊。
既是这样,倒不宜跟她透露太多了,以免言多语失。只能另外再想法子。
曲烟烟拿定了主意要伺机逃脱,她很清楚自己只有一次机会,必须一击而中。如果不幸被冯家人捉住,她的下场一定是不堪设想的。真到了那一步,她唯有咬舌自尽一条路了。
而且要快。有冯虎那畜生在,多耽搁一天都是凶险。
昏蒙的灯影里,她隔着鞋子又将那包蒙汗药粉暗暗地捏了一捏。
既打定了主意,曲烟烟心里反倒平静了下来,躺在黑暗闷热的柴房中,只管一心一意地静养身体。她闭了双目,缓缓吐纳调息,排除杂念,居然安稳地睡了一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