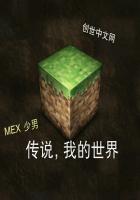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初一,帝都北京城内彤云密布,阴雨靡靡,将至晌午天色愈加阴霾,像被欠了半年租子的地主婆的脸,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京城最繁华的正阳门大街也少了几分平日里的鼎沸与喧闹,只有街道两边装饰考究的店铺名号辐条依旧在风雨中飘荡,稀稀落落的行人,撑着油布伞快步走过空旷的大街上,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平淡祥和,直到──直到一个人的出现打破了这片难得的静溢。
透过雾蒙蒙的细雨,一个落魄的中年人正沿着街边的青石路阶踉踉跄跄的走来,他约莫四十上下年纪,身上穿一件破麻布宽衫,头上戴着儒巾,端的一秀才打扮,他一步三晃,边走边捶足顿胸,脸上满是悲愤,他没有打伞,全身上下早已湿透,空洞的眼神带着些许麻木,冰冷的雨水击打在身上,浑然不顾,嘴里兀自唠唠叨叨,不知说些什么……
对于这一切,即便是京城的人们也早已见怪不怪了,自当今圣上登基以来,内忧外患不断,社会持续动荡,连年灾荒,特别是崇祯十五年,十六年,连续两年河南湖北等中原地区遭遇千年不遇的洪涝灾害,庄稼颗粒无收,百姓卖儿卖女,命悬一线,大批难以活命的饥民揭竿而起,加入流贼大军。
近日坊间更有甚言说,贼寇李逆已于西安建立伪政权,年初即举十万精兵东进,一路势如破竹,现已入山西陷太原,直逼京师。
乱世飘零,国将不国,作为读书人最底层的秀才亦难逃厄运,很多人被迫背井离乡,甚至流浪乞讨,曾经受人尊敬的功名,如今却不如一块面团更能满足肚子的需求。
让开,让开,让开!伴随着车夫由远及近的呵斥声,三辆车身豪华,装饰考究的马车风驰电掣般从内城方向快速驶来,粗大的车轮溅起路边的泥水足有丈余,街道两旁的行人惊恐之余,纷纷躲避。
也许是行人的怯意助长了车夫们的豪情,他们快马加鞭,任其狂奔不羁。
找死呀──吱──突如其来的斥骂夹杂着马车刹车声让原本宁静的街道陡然充满了急促,紧接着──砰──的一声闷响,一个人从马车右前辕径直飞出,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在空中划过一条弧线,跌落在了七八米外的路边排水沟旁。
──吱──吱──
瞬息过后,又是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刚才紧随其后的另外两辆疾奔的马车也在不远处戛然而止。
一个手持马鞭,车夫打扮的矮个胖子从最先停下来的那辆车上侧身跳下,大踏步奔到被撞飞的那个人的身边,你这个穷酸儒,竟敢在皇门正街撒野,冲撞国丈大人车队,该当何罪!
胖子作为达官显贵的车夫,平日里多耳须目染其言行,对付草民百姓显然深喑其道,一出口就上纲上线,先给扣了个大帽子。
被撞得正是刚才那个秀才打扮的中年人,此刻满脸都被混杂着泥水的鲜血覆盖,整个人身子抽搐着蜷作一团趴在路边的泥水洼里,两条腿僵直的错位成了外八字,显然是断了。
眼见“肇事者”只是眉头紧锁,咬紧牙关,趴在地上瑟瑟发抖,并无诚惶诚恐的认罪态度,原本趾高气昂的胖车夫显得有些恼怒,顺手扬起手中的马鞭,斜向中年秀才裹去,鞭梢划过他被雨水打湿的破烂衣衫,瘦骨伶仃的背上登时出现了一条血淋淋的口子。
中年秀才猛地颤栗了一下,并没有出声,只是咬着牙用一只手撑着地艰难的侧过身来,冷冷的看了胖车夫一眼,又径直躺在了地上。
这时候街边已有路过的行人驻足观望,有大胆的甚至开始指指点点,面上亦有不平之色。
胖车夫恼羞成怒,再次抡起了手中的马鞭,劈头甩落,这时一个白色的身影猛地扑了过来,横抱住了中年秀才上半身,挡下了嗞嗞带声的落鞭。
爹爹,爹爹,
一个身着粗麻布白裙的小女孩伏在中年秀才身上大声痛哭,稚嫩的背上被马鞭抽出一道深深地血痕,血水夹杂着雨水漫延开来,顷刻间染红了小女孩单薄的衣衫。
胖车夫稍稍愣了一下,随即怒骂道:哪来的贱蹄子,敢在此扰乱公差,信不信将你一起绑了送官!”
小女孩并没有理会胖车夫的谩骂,只是冷冷的回头看了他一眼,双臂紧紧抱着蜷缩在地上的中年秀才,痛哭流涕,泪如雨下。
爹爹,爹爹,
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玉娘,我是玉娘呀……小女孩悲戚的哭声让人心如刀绞,而此时躺在地上的中年秀才面色苍白,两眼紧闭,全身瑟瑟发抖,任凭女孩哭喊,却始终无动于衷。
围观的人群中不时发出阵阵叹息声,不知是为这对惨遭横祸的苦命父女怜惜,还是对这生灵涂炭,豺狼当道的乱世感到悲哀。
数次发威均遭无视,地上的这对父女并未像他预想的那样畏惧求饶,甚至都没有正眼瞧过他,胖车夫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恶向胆边生,扬起手中的马鞭再次向父女俩挥落。鞭梢划过蒙蒙的细雨,带着尖锐的破空声,再次袭向可怜的父女。
这时候马车周围已经聚集了不少的人,几个大胆的更是在那里指指点点,他们显然很同情眼前的父女,只是胖车夫口中的“国丈”让他们感到一种畏惧。
敢在通往皇宫内城的正门正阳门主街纵马狂奔的主,绝非一般的达官贵人,忿忿不平的人们只是面带同情之色远远地看着,并没有谁敢上前施以援手,有胆小的不忍心更是用双手捂住了眼睛。
小女孩咬着牙一动不动,只是紧紧地抱住中年秀才,尽最大可能得用稚嫩的身躯保护他奄奄一息父亲。
──啪──
一声脆响,马鞭已经结结实实的抽在了一个人身上。
——不是小女孩,更不是她的父亲。
一只苍劲有力的手不知什么时候攥住了胖车夫的鞭头,马鞭失去了往下的旋转点,没了准头,伏在地上的父女俩躲过了一劫,但是软韧的鞭梢却顺势掠过那人的右肩,在上面留下一道浅红的印痕。
等到那女孩惊恐万分的回过头,她看到的不是那肆虐的马鞭,而是一顶挡风遮雨的硕大皮伞。
透过皮伞弧檐,一个年轻人修长挺拔的身影正矗立在那里,他二十岁上下年纪,头戴一顶红缨毡帽,身着镶红边的白粗布鸳鸯袄,浓眉大眼,紫铜的脸膛棱角分明,仿佛石雕一般,雕刻出岁月的沧桑,深邃的眼神让人感到遥远却又近在咫尺。
“大胆狂徒,竟敢庇护人犯,对抗官府,你该当何罪?”眼见有人挺身而出,抓住了马鞭,并且看装束好像是军官打扮,胖车夫颇有些意外,不过作为堂堂国丈嘉定伯府的车夫,终究见过些世面,对于一个小小的军官并未放在心上,随即定了定神,大帽子扣出。
庇护人犯,对抗官府,哼哼……哪个人犯,是你吗?
年轻人神情肃穆,愤然道。
胖车夫微微一愣,旋即指着伏在地上的父女俩怒道:“你敢胡说,他们冲撞国丈府车队,惊扰皇胄贵体,才是人犯”,说着两手突然发力,想挣脱年轻人右手中的马鞭,不料马鞭就好像生了根一样,纹丝不动。
胖车夫两次使力都未能成功,反而憋得满脸通红,气喘吁吁,而年轻人一幅波澜不惊的样子,脸上竟然带着淡淡的笑意。
这样僵持了片刻,胖车夫身子后仰,两腿着力,使出了吃奶的劲,猛然一扽,原本想趁其不备,将马鞭夺回,熟料年轻人早已觉察到他的用意,顺势将手一松,在单边重力的作用下,胖车夫登时像一发出膛的炮弹,连人带鞭向后急速坠去。
……扑哧……一声闷响,肥胖的身躯像一个瘪了气的皮球四脚朝天、结结实实的墩在在路边凹起的一块青石板上。
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围观的人们先是目瞪口呆,继而忍俊不禁、捧腹大笑,刚才令人纠结压抑的气氛也一扫而空,街边商铺的客人、伙计听见哄笑声,也纷纷出来看热闹,在绵绵的细雨中原本显得有些沉寂的大街竟好似恢复了往日的喧哗。
估计是对这套高难度的着地动作缺乏了解,此时胖车夫表情变得极其古怪,眼睛瞪得老大,手指着年轻人,不停地张着嘴,却只是呜呜咽咽,说不出话,一张紧绷的胖脸也变成了诱人的熟猪肝色。
年轻人对胖车夫狼狈的样子并没有多大兴趣,径直回过身来,女孩泪眼朦胧,正一脸茫然的看着他,年轻人没说话,只是将手中的皮伞交给女孩,然后蹲下身来,正准备查探中年秀才伤势,突然身后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远处的人群中不禁发出一阵惊叫声。
后面两辆车的车夫眼见同伴吃了瘪,大为光火,作为国丈府杂役,平日里狐假虎威,飞扬跋扈惯了,今日却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戏弄,均感到颜面大失。两人都抄起马鞭从车上跳下,大步流星的冲了过来。
也许是对刚才胖车夫悲惨的乌龙遭遇有所顾忌,这次两人均未用鞭,而是从左右两路分别出拳袭向年轻人。
此二人身材较还躺在地上哼哼唧唧的胖车夫高大出不少,眼见年轻人并无防备,围观众人不禁心捏了一把汗。
说时迟,那时快,闻得耳边风声起,年轻人脸色微微一变,蓦然回身,侧身前倾,挡在了父女俩身前,同时分出左右手,……啪的……一声响,年轻人脚下生根、身子只是微微一晃,已然握住了近到咫尺的重拳,左右夹击的两个壮汉车夫壮硕的身躯好似被钉在当地,半步动弹不得。
惊魂未定的的女孩半跪在地上,两只胳膊紧紧抱住父亲的头,被雨水浸的湿漉漉的头发软软的敷在脸上,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年轻人,眼神中却满是焦虑与担心。
围观的人们也忍不住叫起好来,有几个义愤填膺的年轻人更是吹起了声援的口哨。
年轻人冷冷一笑,眼神中闪过瞬息的凌厉之色,只见他气沉丹田,两手猛然发力,只听到“咯吱”一声脆响,被年轻人紧握住的两只拳头指关节已然错位,正想奋力挣脱的两个车夫倏地脸色大变,额头上青筋绽出,五官扭曲,片刻之间,豆大的汗珠便已混杂着雨水布满了因痛苦而狰狞变形的脸廓。
两人咬着牙,擎起另一只拳头向对手面门袭去,年轻人头一低俯身闪过,然后迅速垫步上前,马步桩交叉别住他们下盘,同时虚灵顶劲,以四两拨千斤之势,双臂骤然发力推出,两个车夫原本硕大魁梧的身躯却好似被狂风吹散的落叶,向后急速坠去。
──砰砰──
两声闷响过后,胖车夫在“下榻”的青石板上迎来了患难与共的同伴,三个人错落有致,仰面躺成一排,场面倒也颇为壮观。
围观众人早已看得呆了,此刻见三人大起大落,这般狼狈相,再也无所顾忌,皆轰然大笑起来。
年轻人衣袂飘飘,一脸肃穆,缓缓走到胖车夫等三人落脚处,朗声道:尔等肆意妄为,目无法纪;在此天子脚下,皇门正街;纵马狂奔伤人,当真敢藐视天威吗?
年轻人声音浑厚,低沉中透着一丝威严。
此话一出,众人皆倒吸一口冷气,“藐视天威”,这是什么罪过?砍头有木有,要不要?
如果碰巧赶上“大明律“的版权所有者——朱元璋老爷子发脾气,砍下了你的脑袋只是一个噩梦的开始,接下来他还要砍光你全家所有的脑袋,运气好的话还有可能把你三伯四舅七大姑八大姨的也捎带上,这样即便你到了那边,依旧能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不会有一丝寂寞。
至于当今圣上脾气原本倒是不错,只是登基后国家内外交困,社稷危亡,性子早已是大变,这话要是传到他耳朵里,结局估计也好不到哪去。
和刚才胖车夫的上纲上线比起来,这个年轻人扣帽子手法娴熟、游刃有余,政治觉悟明显高出不少。
兀自躺在地上哼哼唧唧的三人此时总算有点清醒了,最先“倒地就寝”的胖车夫摇摇坠坠,挣扎着站了起来,手指着年轻人,怒道:你……你……你血口喷人,
……我……我……我是国丈府的车夫……
也许是对这顶威力惊人的帽子有所畏惧,又或者是刚才表演失传已久的独门绝学“凌空墩坐”岔了气,胖车夫语无伦次,说话也变得有点结结巴巴起来,全没了刚才的嚣张。
大胆狂徒,国丈大人功高德劭,克以奉公,世人皆仰慕其德;尔等天子脚下纵马行凶,鞭笞弱孺,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嫁祸皇亲,辱没国丈英明,该当何罪呀!
年轻人气贯长虹,声音雄壮响彻整个街区,在雨中回旋激荡,回声竟不绝于耳。
众人闻之皆一片哗然,年轻人不仅身手了得,而且心思缜密、机变如神。如果说刚才扣得是顶大帽子,这一番训斥无疑更是个紧箍咒,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让对方骑虎难下,欲罢不能。
就在众人纷纷对年轻人的机敏的应对之策意犹未尽之时,不远处中间那辆马车上珠帘轻启,一个五官瘦削的人探出头来,向外张望。
正垂首立在当地,一脸狼狈状的胖车夫见状,忙挣扎着爬起来,一瘸一拐迎了了上去,从车尾横挡取下马梯,快步放到马车右前辕处,小心翼翼的扶着那人走下阶梯。
众人纷纷侧目,一个身着紫色锦袍、面色阴晦,管家模样的人正缓步向这边走来,胖车夫从车上拿了把伞小心翼翼的撑开,紧紧跟在那人身后为其挡雨。
年轻人此时正蹲下身子,左手三指成弓形,平布按在中年秀才右手掌后寸脉处,中年秀才躺在地上气若游丝、面色苍白。
少顷,年轻人轻轻叹了口气,脸色愈加凝重起来。
女孩跪坐在地上,呆呆的看着年轻人,原本眉清目秀的俏脸早已是泪眼朦胧,让人看了黯然神伤,她俯下身子用力将父亲的头部移到到自己腿上,想尽量减轻一下他的痛苦,地上满是积水,父女俩早已全身浸透,身上再也找不到一丝干松的痕迹。
一阵风袭来,女孩情不自禁打了个寒战,见此,正欲起身的年轻人,顺手解下了身上的斗笠,递给她,女孩没有接,只是怯生生望着他,凄楚的眼神中满是感激,年轻人没说话,只是蹲下身来,将斗笠轻轻的搭在中年秀才身上。
“就是他,包庇人犯,对抗国丈府!”眼见来了主心骨撑腰,胖车夫恢复了刚才的狂妄,指着年轻人,气焰嚣张的大声道。
眼见胖车夫欺下瞒上丑陋的嘴脸,街边围观的众人皆窃窃私语,皆面露鄙夷之色。
……啪……一声脆响,管家模样的锦袍人忽然侧身,猛抽了胖车夫一记耳光。
混账东西,尔等主道纵马、御车伤人,不下车礼罪,反而行不义之举,损国丈仁义威名,当真该诛!
面对这这突入起来的变故,众人皆愕然,年轻人倒是泰然自若,缓缓回过身来,冷冷的看着主仆二人。
胖车夫麻脸通红,正欲辩解,锦袍人反手又是一个耳光,胖车夫倒退两步,愣愣站在当地,再也不敢吭声。
国丈一贯温良恭俭,严于律己,尔等骄横跋扈,横行无忌,以致惹此祸事,回府必受重罚。锦袍人阴着脸斥道。
此言一出,路人更是哗然,原本替年轻人担心的众人,悬着的一颗心也放了下来。
经此大起大落,绵绵细雨带来的隐晦一扫而空,围观众人更是兴致勃勃、议论风生,有的说,年轻人行侠仗义、抑强扶弱,着实让人敬佩,也有的说国丈身居高位却豁达大度、宽以待人,实属难得。在人们此起彼伏的议论声中,对锦袍管家的印象,也由刚才的鄙夷变的赞叹连连。
这位兄台,鄙人乃嘉定伯府总管周通,刚才府中车奴孟浪无礼,有冒犯之处,还请见谅。锦袍人打量了一下年轻人,又看看兀自卧在地上的父女俩,微微拱了拱手,一脸恻然道。
嘉定伯是国丈周奎封爵号,周奎是周皇后父亲,当今圣上岳父,平日里出入宫庭,颇得帝后宠幸,围观众人多是京城人氏,倒也偶有耳闻,当下更是饶有兴趣的看下去。
原来是国丈府周总管,失敬,失敬,在下年轻气盛、行事莽撞,适才多有冲撞,也请总管海涵。
年轻人并不做作,双手抱拳做了个辑,脸上却是依旧肃然。
无妨无妨。
周通回了个礼,接着向前紧走几步,来到父女俩跟前,女孩也轻轻扶了扶父亲的身子,抬起了头,周通猛然一怔,原本阴晦的脸上,变得有些异样,但随即探下身子,缓缓握住中年秀才的手,面露关怀之色,微微叹了口气,起身对年轻人道:看样子着实伤的不轻,小兄弟,我刚才去宫中办事,匆忙间没有准备,这里有十两银票,你先拿着,先找个郎中诊治一下,有什么事明日到府上再细细斟酌,如何?
说着,周通从袖口内衬里取出一张单面盖章的京城宝丰钱庄银票。
这个……
年轻人没有接,只是不动声色的看着身边的女孩。
小女子年幼无知,不谙世事,一切但凭侠士做主。
女孩显然明白的年轻人的顾虑,咬着嘴唇轻轻的说。
刚才父女俩惨遭鞭笞凌辱,年轻人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不仅救下他们,还狠狠惩戒凶手;继而慷慨陈词,迫使对方低头认错……
对于女孩来说,此时这位年轻人俨然成了他们的守护神,是她和父亲唯一的依靠和寄托。
恭敬不如从命,既然这位姑娘没有异议,那就有劳周总管了。
年轻人义形于色,从周通手中接过银票,凛然道。
周通回过身,唤过还在一旁颤立的胖车夫,凑在耳边交代了几句,胖车夫点了点头,小心翼翼将雨伞递给周通,一瘸一拐的向马车跑去。
你们两个混账东西,还嫌丢人不够吗?赶紧给我滚起来!周通用雨伞指着兀自躺在地上呻吟的另外两个车夫,阴着脸骂道。
两人一脸狼狈相,在众人嘲笑声中,相互搀扶着,摇摇摆摆的站了起来。
胖车夫已经奔了回来,手里捧着一个名帖,毕恭毕敬的交给周通。
这是国丈府名帖,你将此父女俩安置好后,可持此贴来府中找我,再商榷后续之事。
周通转过身,从袖口中拿出一张名帖对年轻人说道。
年轻人不置可否,只是伸手接过,淡淡的点了点头。
告辞了。
说着周通又侧目看了一眼地上的父女俩,原本瘦削的脸上多了一丝叵测的光彩。
细雨靡靡,飘落在身上;薄薄的一层,像雾一样。
周通等人早已驾车绝尘而去,年轻人巍然的站在雨中,看着街尽头那金碧辉煌、屋宇重重的皇宫内城,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两边的围观的行人,渐渐散去了,一个个披蓑戴笠的身影,若隐若现的消失在朦朦细雨中。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年轻认黯然神伤,轻轻的念着这两句诗,深邃的目光变得有些迷离……我来自何方,又将去往何处……